(英文原版)How Big Things Get Done 哈希解读
How Big Things Get Done|哈希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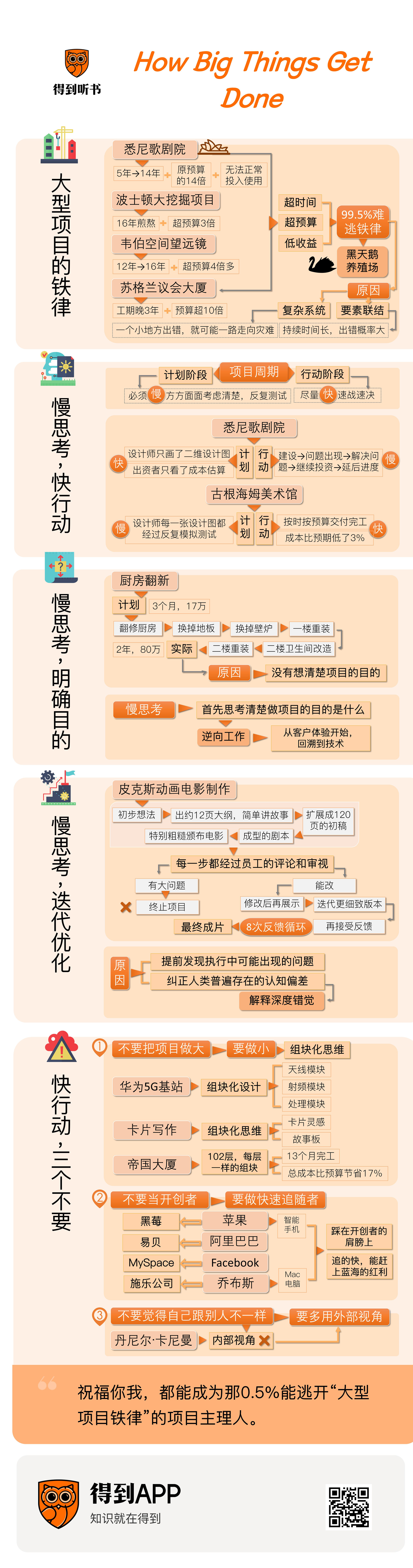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哈希。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一本2023年在美国出版的书。它的名字叫做How Big Things Get Done。我们可以叫它《怎样做成大事》。它的副标题有点长,翻译过来是,“决定每个项目命运的惊人因素,大到太空探索,小到家庭装修”。
这本书的第一作者,是牛津大学教授、丹麦经济学家本特·弗莱布约。他近些年的一个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那些成本上亿的超级项目,比如建造摩天大厦、修建万里铁路、筹办奥运赛事、打造商业大片,等等。他用超过十年的时间,搭建了一个庞大的“超级项目数据库”,覆盖了20多个不同领域,136个国家,16000多个项目。从中,他发现了一些,决定这些项目成败的关键规律,而这些规律,同样可以用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工作当中,比如装修房子、写报告、办活动,等等。总之,只要是你想把一个复杂的计划落地成现实,想让它能保质保量保时间地完成,那么这本书里的内容,就能帮到你。
今天我们从一个悲伤的故事说起吧。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大项目——悉尼歌剧院。你应该见过它的样子,就像一簇即将乘风出海的白色风帆,每一页风帆又像贝壳,像云朵,像鸟儿的翅膀,洁白,优美,飘逸。即使从它落成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了,但咱们今天看这个设计也一点都不会觉得过时。
那么,这么杰出、天才的建筑设计,是出自谁手呢?这位设计师的名字叫约恩·乌松。当年,澳大利亚政府发起了悉尼歌剧院的设计竞赛,收到了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两百多个设计方案。乌松的方案从里面脱颖而出,一下子就把评委们给震住了——因为它实在是太美了。
这就是悉尼歌剧院故事的开端——天才的设计,年轻的设计师,一夜成名的比赛。像梦一样美好。但是,故事的走向却没有延续这种美好。后来悉尼歌剧院的建造,可以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为什么呢?首先,它的时间严重超期,原本计划的建设时间是五年,结果花了14年;而且,预算也严重超支,最终的建造费用是开始预算的14倍;即使是这样,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1973年它落成的时候,也就只是外表上搭建好了,里面还有很多缺陷,甚至都没法在里面演歌剧,因为那个声场环境是不合格的,后来才在很多年的时间里一点点给完善好了。
好,到这里,我们先暂停一下,稍后再来讲导致这个项目失败的原因。现在,我们先用这个例子,来介绍这本书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发现。那就是,绝大多数的“超级项目”,也就是预算超过10亿美元的项目,它们的建设过程都会出现跟悉尼歌剧院类似的问题,那就是:超预算,超时间,低收益。用书里的话说就是:Over budget, over time, under benefits.
作者把这个叫做“超级项目的铁律”(Iron Law of Megaprojects)。不管是像博物馆、音乐厅和摩天大楼这些建筑项目,还是像桥梁、隧道、高速公路和铁路这些交通项目,还是核电站、水电站建设,或者奥运会等大型赛事,或者现在百亿千亿的IT系统项目,都很难逃开这个铁律。
在我们开头提到的,作者那个覆盖了16000多个项目的数据库里,只有0.5%的项目逃脱了这个铁律。而剩下99.5%的项目,要么是超预算,要么是超时间,要么是效益不行。而且往往还不是只占一个,而是占了两个,甚至三个全占了。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假设你现在要领导一个大型项目,比如一个大型建筑,或者一个大公司的IT系统,那么你可千万别太乐观,觉得肯定没问题,因为大数据告诉我们的现实其实很可怕,那就是你有99.5%的可能,没法保质保量保时间地完成任务。
好吧,那既然是这样,我们设立一个缓冲区间怎么样?比如,我要建造一个大型建筑,我设好时间、预算以后,再多打出20%的富余量,这应该能行了吧?
但是,作者告诉我们,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数据显示,一个大型建筑项目的实际成本平均会超支62%。而且,这个数据的概率分布还不是正态分布,而是肥尾分布,也就是说,出现极端情况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很多人们熟悉的大项目,都属于是这个“肥尾”中的一分子。比如,美国波士顿的“大挖掘”项目,用隧道取代高架公路,经历了16年的煎熬,花费超了预算的三倍。美国宇航局的韦伯空间望远镜,计划要12年,结果花了19年,而且超出原本预算4倍多。还有苏格兰的议会大厦,工期晚了3年,预算超了10倍。
我们都听过“黑天鹅”这个词,指的是那种概率低,后果严重的风险事件。而大型项目领域,简直就是一个黑天鹅养殖场,到处都是黑天鹅在横冲直撞。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在于,每个大型项目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里面每一个要素都是相互联结的,所以,但凡一个小地方出了岔子,就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路走向灾难。而大型项目持续时间又很长,中间总是难免会有哪个地方出问题,所以多米诺骨牌就很容易被碰倒。
所以,一个能显著地降低项目出问题的概率的思路就是,尽量缩短项目建设的时间。打个比方,就像你住在黑天鹅养殖场旁边,那你每天开窗时间越长,黑天鹅就越有可能飞进屋里,所以一个解决思路就是,尽量缩短开窗时间。
但是,这个思路是不是有点太简单粗暴了?我们看有多少仓促推进的项目,最后都成了烂摊子、无底洞。所以才有那句话,“欲速则不达”呀。
确实是这样。那么,有没有一种,既能干得快,又能干得好的方法呢?作者给我们提供的建议,叫,慢思考,快行动(think slow,act fast)。
也就是说,他把整个项目周期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计划阶段,也可以叫思考阶段;然后第二个是行动阶段。那我们前面说的,“尽量缩短开窗时间”,指的是让行动阶段尽量短,速战速决。但是在思考阶段,必须要慢,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清楚了,反复测试了,再去行动。
听起来好像是很明显的道理,但是作者调研发现,在现实中,大型项目最常见的做法,恰恰是反过来的。他们在思考阶段推进得很快,着急开工,结果开工以后才发现有各种问题,只能一拖再拖,结果就是超预算、超时间、低效益。我们前面提到的悉尼歌剧院的例子,正是这样的一个负面典型。
刚才讲到的,设计师乌松的那个天才的设计,后来大家发现它真的就是一个飘在天上的设计。乌松画图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过,这张二维图要是变成三维的,该用什么样的内部结构,该用什么材料,怎么去搭建。这些问题他都没考虑过。
那,设计师没考虑过,给歌剧院项目出钱的人也不考虑吗?巧了,他们也没仔细研究。当时,歌剧院项目背后的关键力量,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卡希尔,他已经在位很多年了,还得了癌症,就想赶紧留下一些政治遗产。他觉得光有自己推行过的那些公共政策是不够的,必须得有一座宏伟的建筑。所以他只看了粗略的成本估算,就决定赶紧开工了,而且开工之后还一直催进度。
但是,随着建设的推进,问题就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了。为了解决问题,他们只好不断地往里面砸钱,延后进度。甚至中间一度,要把已经干完的工程炸掉,重新换一种思路来做。
虽然,设计师乌松在这个过程中也一直努力在解决问题,但是他捅出的篓子太大了,消耗的代价也太大了。所以,1966年,项目进行到一半,乌松就被换掉了。他跟家人秘密离开了澳大利亚。为了躲媒体,他们在飞机关舱门前几分钟才溜上飞机,然后再也没回来。他的事业也这么毁掉了,没人再敢找他设计大项目。他直到2008年去世的时候,也没亲眼见过自己设计的悉尼歌剧院。
这就是悉尼歌剧院的故事,这是一个“快思考”导致了“慢行动”的悲剧故事。真的像一部让人唏嘘的歌剧。
我们再来讲一个关于大型项目的故事。这一次的主角是位于西班牙北部的古根海姆美术馆。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一”。在很多顶尖建筑师看来,它的地位一点不亚于悉尼歌剧院。
但是,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故事,跟悉尼歌剧院的故事,完全是相反的。它不仅是按时按预算交付完工的,而且耗费的成本还比预期低了3%,产生的效益比预期还要多。也就是说,它属于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只有0.5%的,非常罕见的,逃开了“大型项目铁律”的“完美项目”。
为什么古根海姆美术馆能逃开“大型项目铁律”呢?这也要说到它的设计师。这位设计师叫弗兰克·盖里。他的做事风格跟乌松完全不一样。他在交每一张设计图纸之前,都必须经过反复的模拟测试。最早的时候他是用各种木头积木来搭模型,还会加入很多折纸,他把这些东西摆来摆去,模拟各种变化。去找那种不仅好看,而且性价比高,结构稳固的设计方案。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方案,就是在这样的,不断推倒、迭代的漫长思考过程中孕育出来的。
后来有了CATIA这类能做数字模拟的软件之后,盖里又开始用软件来尝试各种各样的设计形状,甚至会做上千次迭代。可以说,盖里的每一个设计在正式出炉之前,其实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微缩版“孪生体”。所以他的设计往往到了后面的建造阶段,会推进得飞快,能给建造方省钱省时间。这就让他成了被很多大项目争抢的设计师,职业生涯非常长寿。
作者在调研中发现,那些最成功的项目,那些属于0.5%的逃开了“大型项目铁律”的项目,它们几乎都有跟古根海姆美术馆类似的经历。那就是,慢思考,快行动。这就是成功项目的秘诀。
这个秘诀,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直接。但是当你在实践中去执行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下面我们就分别展开来说说,怎么做好慢思考,怎么做好快行动。
先来说怎么做好“慢思考”。我们还是从一个真实的故事说起。这次讲的不是那种上亿的大型项目了,而是一个家庭项目——厨房翻新。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把自己家的厨房翻修一遍,其实也算是日常生活里的一项大工程了,也同样是适用这本书给出的那些建议的。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夫妇,大卫和黛博拉,住在美国纽约。他们开始翻修厨房的时候,预算是17万美元,预计要花3个月。但结果呢,他们最后是耗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花了80万美元左右。比计划的翻了好几倍。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虽然一开始只是想翻修一下厨房,但后来又感觉地板又旧又丑,也该换掉,然后又感觉,客厅里的那个砖砌壁炉,跟新厨房新地板风格不匹配,也该换掉。换掉壁炉之后,又发现化妆间在壁炉附近也显得格格不入了。结果就这样一步一步扩展,直到把整个一楼都掏空、重新修了一遍。这还没完,他们的母亲说,你们既然都已经这么大动干戈了,干吗不干脆把二楼的卫生间一起也改造了呢,我早就看它不顺眼了。结果,再一次地,这一个变化又导致了另一个,直到最后,整个二楼也全部翻修了。这就导致了,这项工程消耗的成本、时间都翻了好几倍。
那么,大卫和黛博拉的问题出在哪呢?有的朋友现在应该想到了我们前面说的,要“慢思考,快行动”。那他俩的问题是出在,没有做好“慢思考”,开工之前没好好筹划吗?
还真不是。他俩的思考阶段还真挺长的。他们提前不止一年就开始考虑怎么翻新厨房了,后来还雇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建筑师,花了几个月来定设计图纸,然后才开工的。
所以,他俩的问题,不是出在思考不够慢上。那是出在哪里呢?是出在,没有想清楚,项目的目的,也就是翻新厨房是为了什么。其实在后来的扩大改造的过程中,他们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翻修房子是想更好地招待客人,所以才会看越来越多的布置都不顺眼。但如果他们能一开始就明确这个目的,就能意识到光改造厨房是不够的,应该去做一个房屋的整体改造。这样,建筑师就会根据这个需求,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来帮他们做整体的规划了。
所以,要做好“慢思考”,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思考清楚,你做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你后面的思考才不会迷路,不会脱轨。比如设计一座建筑,你首先要考虑这个建筑要发挥的最首要的作用或者功能是什么,然后把这个功能放在第一位来做设计。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设计师盖里,他就是这么干的。他每次在跟潜在客户会面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做长时间的交谈,去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建筑项目。
从“为什么”开始,这一条原则适用几乎所有的项目。不管你是建大楼、办比赛、写书、做产品,还是给家里改造厨房,都要从“为什么”开始。
乔布斯就经常强调一句话: “你必须从客户体验开始,然后回溯到技术。”你不能反过来,先研发技术,然后再想怎么卖。他这个理念被叫做“逆向工作”,后来在硅谷流传很广,成了很多公司的准则。
我还想起曾经看过的一个美国纪录片,叫《富豪谷底求翻身》,讲的是一个亿万富豪接受了一个挑战,隐姓埋名到一个小镇,身上只带一百美元,三个月要赚到一百万。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这个富豪不管是之前做大生意,还是到了小镇从零开始去淘废品,都是一定先看准买家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根据买家的需求去反推我要做什么。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慢思考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从“为什么”开始;再来说第二个关键点,就是不断迭代优化。
书里讲到皮克斯的例子。这是一家专门制作电脑动画的公司,做出过很多特别受欢迎的动画电影,比如很多人熟悉的《飞屋环游记》《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头脑特工队》等等,都是他们制作的。
作者跟皮克斯的高管详细了解过他们的创作过程。一开始作者以为,他们的创作是“悉尼歌剧院”式的,特别依赖一个天才的点子,有了点子之后抓紧推进就行了。但后来作者才发现,原来他们的创作过程,是“古根海姆美术馆”模式的。就是不断地做一版又一版的模型,去迭代优化。
他们一开始可能只是有一个很初步的想法,比如“一只法国老鼠喜欢烹饪”或者“在一个女孩的脑袋里发生的事儿”。然后他们会出一个大约12页的大纲,简单讲一遍故事。然后扩展成120页的初稿。再然后是成型的剧本。再然后是把剧本变成一个特别粗糙版本的电影,只有一些画面加上员工阅读的对话。
而在这每一步里,他们都要经历一群皮克斯员工的评论和审视,这些人会质疑人物、质疑情节、质疑创意。然后创作团队就拿着这些批评回去研究,要是发现真是有大问题,就终止项目。要是觉得能改,就改了再展示,大家觉得可以了,再往下迭代一个更细致的版本,然后再接受大家的反馈。通常来说,一部皮克斯电影,从有了创意到最终成片,要经历8次这种反馈的循环。而我们最终看到的片子,已经是至少第9个版本了。
为什么作者很推崇这种不断迭代优化的做法呢?最基本的,当然是它能提前发现很多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能帮我们纠正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认知偏差,心理学家把它叫做“解释深度错觉”。意思很简单,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想明白了,懂了,实际上并没有。
比如,你知道自行车是怎么工作的吗?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知道。但是如果真的让他们去把这个原理完整写出来,或者在图纸上画出来,他们就突然发现,不知道该怎么下笔了。也像学习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已经把一个定理搞懂了,但是真的让我用它来解释一个现实现象,就发现,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没搞懂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慢思考”的阶段,我们不要只停留在想法层面,而是要动手去实践一下、测试一下,至少跟别人完整地讲一遍。在这个过程中,那个“解释深度错觉”就消失了,你会发现自己哪里是对的,哪里确实没想明白。每一步都这样做,就完成了不断的迭代优化。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怎么做好“慢思考”。下面再来说说,怎么做好“快行动”。从这本书里,我们能提取出来三个“不要”。
第一个是,不要把项目“做大”,而要把它“做小”。意思就是,要把一个大项目拆成很多个小项目来做,也就是你可能听过的,“组块化”思维。我们在《效率脑科学》那本书里重点讲过这个思维,它尤其适用于那种比较复杂,或者信息量很大的项目,不管是一个大型工程,还是你自己要写的一个很头疼的报告,都是适用的。
比如,举个书以外的例子,华为的5G基站用的就是“组块化”设计。他们把基站分解成很多个组块,比如天线模块、射频模块和处理模块,然后根据不同的需求来做拼装部署,效率就很高了。
还有,再说个小一点的场景,个人写作。我们听书为你解读过的那本《卡片笔记写作法》,其实本质上也是组块化思维。很多我们熟悉的大作家,都很喜欢用卡片来写作。比如纳博科夫,二十世纪著名的俄裔美籍作家,记者问他怎么写作时,他说自己写小说不会从开头一直往后写,而是像拼图一样,脑子里先有个大致的架构,一块块内容就像是一张张卡片,对哪块有灵感就写哪块,然后再把它们拼进去。还有,编剧们也会采用类似的方法。他们会用很多块“故事板”组成整体的故事,每块故事板上都只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剧情;当要调整情节的时候,只要移动故事板,或者调整某块板子里面的内容就行了,不用拿出整个剧本,钻进去修改,这样效率就会高很多。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不要”——不要把项目“做大”,而要把它“做小”,拆成小的组块来做。再来说第二个“不要”——不要当“开创者”,要做“快速追随者”。
这个听起来好像跟人们一贯推崇的,要“创新”,要“找蓝海”,要“抓住先发优势”,是冲突的。很多人都觉得,我做这个项目,最好之前没有人想到,我第一个做,那才了不起,那才能赚大钱。
但是,数据告诉我们,最容易成功的,不是那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是那些快速跟上的人。研究人员收集了来自50个产品类别的500个品牌的数据,结果发现,那些开创者的幸存率只有一半,而快速跟随者的幸存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而且他们后来占的市场份额也是更高的。
其实,很多人们以为的“开创者”,都是“快速追随者”。比如,苹果是追随黑莓做的智能手机,阿里巴巴是追随的易贝,Facebook是追随了MySpace,乔布斯的Mac电脑是模仿了施乐公司帕克研究中心的成果。
快速追随者之所以容易成功,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能踩在开创者的肩膀上,直接把他们的经验、教训拿过来用;另一方面又因为追得快,能赶上蓝海的红利。
从快速追随者容易成功这一点上,作者希望给我们的一条忠告是,千万要重视成熟的经验。不管在干什么事的时候,都先想一想,有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助,不要急着自己去开垦荒田。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的大项目,就是没有先例呀,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要和我们前面说的,组块化的思路结合起来了。整体来看,可能这个项目没有现成的经验,但是当你拆成组块之后,就会发现,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没人做过。而只要某一个组块上有成熟经验可以用,那么就尽量拿来用。我想起,之前我们讲过的《小而美》那本书里,有个建议是,在创业阶段,只要能外包的环节,就外包出去。这其实也不只是为了精简员工、省钱,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组块的维度上,充分借助成熟经验,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
书里还举了一个把“组块化”和“借助成熟经验”结合起来的非常传奇的例子,就是纽约的帝国大厦。
帝国大厦有四百多米,总共102层。它的外形就像一根铅笔,纤细,笔直,高耸入云。在1931年落成之后的40年里,它一直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那么,这么高的一栋楼,是花了多久建造出来的呢?答案是,只有13个月。比我们前面提到的,大卫和黛博拉修自家房子的时间还短。最快的时候10天就盖了14层半。而且,他们最后的总成本比预算节省了17%。
他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造的其实不是一栋102层的建筑,而是102栋一层的建筑。什么意思?就是每一层都是一模一样的组块,经验是非常成熟的。而且,这个思路本身也来自另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帝国大厦的设计师兰姆早前给美国雷诺烟草公司设计的总部大厦,那个大厦的形状跟后来的帝国大厦非常像。可以说,帝国大厦其实就是一个加高加大版的雷诺大厦。
所以,就这样,通过把成熟经验的作用给最大化,他们根本没承担多大风险,就完成了一个开创性的巨型项目,实现了当时人们梦寐以求的“世界最高建筑”。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在项目进行过程中要重视成熟经验的作用。其实,在项目开始前,在你估算时间和成本的时候,也要多向外看,多参考别人的经验。
为什么书里要特意嘱咐这一点呢?因为我们人类有一个普遍的心理现象,就是总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我这次跟他们以前的不一样。比如看别人做一个项目做了一年,等到自己要做了,心里就会觉得,我跟他不一样,我用不了一年那么久的。行为经济学把这个叫“内部视角”。但现实是,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用的时间和成本,最有可能会落在这类项目的平均值上。也就是说,其实你跟别人没那么不一样。
提出这个“内部视角”的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但他自己也掉进过这个陷阱里。他在编一本教科书的时候,问了一位资深的同事,这类项目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同事说一般都不少于7年。卡尼曼就震惊了,他觉得自己肯定最多两年就完成了。但最后,他是用了8年才写完的。
而如果不想落入内部视角的陷阱,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外部视角。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尽量准确地估计一个项目要耗费的时间和金钱,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找一些别人做的可参考的项目,然后取一个平均值。而不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其实我们在最开始说的,那个“超时间、超预算、低效益”的大型项目铁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很多项目在刚开始的时候都觉得“我这次不一样”,所以就低估了时间和成本。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快行动”部分要跟你说的最后一个“不要”了:不要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最后你会发现,你们没有那么不一样。
看这本书的时候,不知怎的,我的脑海里经常会响起陆铭在《大国大城》那本书一开篇讲的一句话: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我越是相信,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
而放在大型项目上,好像也是这样的。每一个大型项目,表面上看起来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有的是高耸入云的建筑,有的是直通万里的铁路,有的是精雕细琢的著作,有的是运载庞大的系统。但是,如果你把成千上万个它们放在一起,却会发现,那些成功项目走过的轨迹,竟然逐渐重叠在了一起。它们用总计上万年的光阴,上万亿的真金白银,帮我们锤炼出来了这些可以复用的规律。而如果你也要开启一个属于自己的复杂项目,那么我想不出,还有哪种外部视角,比今天这本书里讲的,更值得重视了。
那么,也祝福你我,都能成为那0.5%能逃开“大型项目铁律”的项目主理人。
我相信这能实现。毕竟,现在听过这本书的人,远远不到0.5%呢。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超级项目的铁律:超预算,超时间,低收益(Over budget, over time, under benefits)。
2、如何逃离超级项目铁律:慢思考,快行动
3、如何做好慢思考:从“为什么”开始;不断迭代优化。
4、如何做好快行动:不要把项目“做大”,而要把它“做小”,拆成小的组块来做;不要当“开创者”,要做“快速追随者”;不要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最后你会发现,你们没有那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