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 朱步冲解读
《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 朱步冲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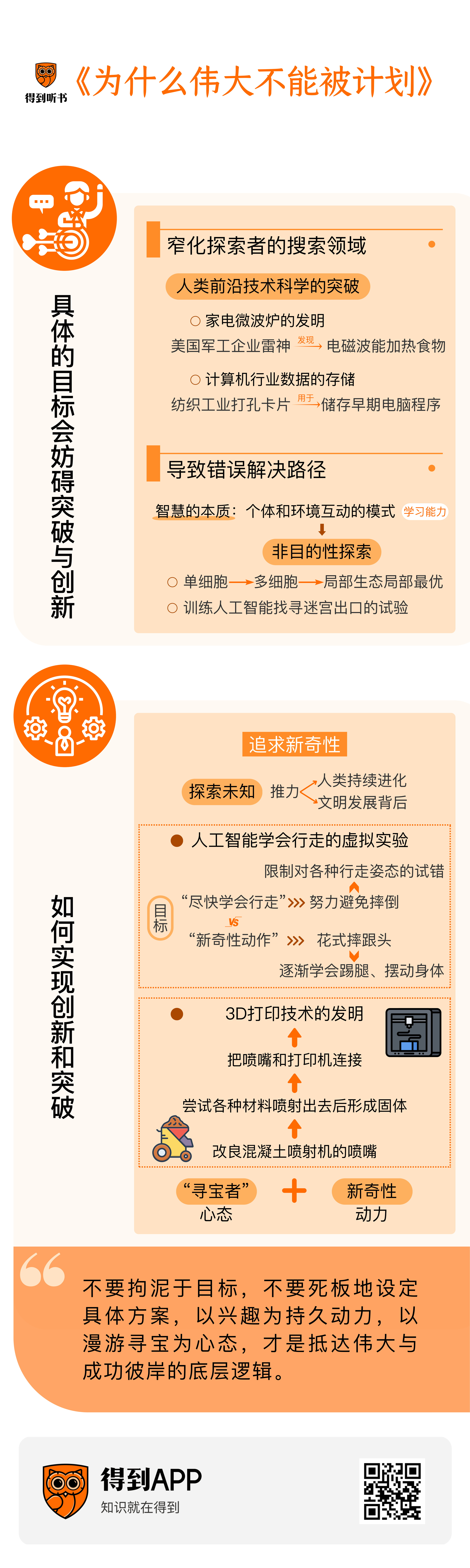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肯尼斯·斯坦利与乔尔·雷曼撰写的《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副标题是:“对创意、创新和创造的自由探索”。
光听这两位作者,斯坦利和雷曼的名字,你可能会感到陌生,但是如果说到他们所在的公司,那么你可能就会感到肃然起敬。他们两个,都是OpenAI的研究员。大家都知道,2022年11月,OpenAI推出了大名鼎鼎的人工智能语言训练模型ChatGPT,能够以流畅自然,近乎人类水平的语言来完成问题回答、文本翻译、信息总结,甚至文稿写作等高难度任务,而斯坦利和雷曼,就是ChatGPT研发团队的核心科学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可以被看作是雷曼和斯坦利,对自己技术探索和创新方法论的总结与升华。不过,雷曼和斯坦利想要谈的,并不是自己在研发ChatGPT时的经验之道,甚至也不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之道,而是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如何实现创新与突破的底层逻辑,非常具有颠覆与前瞻性。所以我们今天,特地把它推荐给你。
在我们的常识里,科学技术的创新研究,遵循着这样一种线性逻辑:科研人员首先设定一个目标,然后通过理论假设与试验,一步步地排除谬误,向目标挺进,最终排除万难,攀上胜利的高峰。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出乎意料的是,两位作者在本书一开头就告诉你,这个观点,是错的,而且是大错特错。
斯坦利和雷曼说,自己在常年从事人工智能算法优化研究中,领悟到了一个真理:在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真正伟大的突破,都不是事先精心计划的结果。例如,迄今为止,最新一个由顶层设计,目标先行,且最终获得成功的大型科技创新项目,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主导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此后再无类似的案例。 换句话说,任何创新和突破,都不像登山,也就是按照既定路线,向着一个清晰可见的目标挺进;而是如同在一片迷雾重重的沼泽地里寻宝——目标未知,路线不定,寻宝者的任务,是在寻找一个个的踏脚石立足点,努力探索尽量大的区域,再看看探索过的区域里,都有哪些价值连城的小玩意。
当然,在科学创新的领域里,所谓“价值连城”并不总是意味着能够立刻能转化成经济效益。斯坦利和雷曼解释说,在科学探索中,任何理论、解决方案,乃至材料或者技术的价值,往往是和它的“新奇性”挂钩的,所谓“新奇才是王道”。
被誉为“硅谷教父”的天才程序员,风险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就说,在高科技领域,优秀的研究,不一定是好的,但一定是新的;而优秀的产品设计,不一定是新的,但必须是好的。只有使用全新的创意和理论,才会涌现革命性的产品,解决那些前人无法解决的难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新奇性意味着,我们认知边界的拓展,更多的新信息,让我们原有的认知结构得以升级、复杂化。最终,在这种看似漫无目的的科研“探宝”中,必然衍生出突破人类原有水平,具备碾压迭代性的技术或者解决方案。
说到这里,我相信你已经对本书的内容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和期待,那么接下来,我就分两个部分,为你讲述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在科技前沿领域,详尽的目标和过分具体的计划,反而会妨碍突破与创新。其次,我们再沿着斯坦利和雷曼的思路,来看看,在技术飞速发展、跨领域研究蔚然成风的今天,怎样才能实现突破与创新。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作者斯坦利和雷曼说,在高科技的探索中,设立明确的目标,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反而会窄化探索者的搜索领域,提供错误的思路和前进方向。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我们不断被告知,有了目标,我们才会有动力和使命感。所谓“谋定而后动”,通过设定和拆分最终目标,我们才能制定出细化而精确的行动与学习方案,日拱一卒,不断提高和升级自我。不仅如此,大家也都相信,小到企业、各种组织机构,大到社会、国家,乃至整个生物界与自然环境,它们的存在与发展,也是为了某种设定好的终极目标,比如生存,与升级进化;而一旦失去目标,无论作为个体的人或者生物,或者作为整体集合的社会,或者自然,就会陷入停滞、混乱与迷茫。
当然啦,斯坦利和雷曼说,这种目标本位主义,从常规来说,是合理有效的。但是,在进展飞速,充斥着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科学、技术创新,甚至艺术领域,“目标本位主义”里的很多法则,就失效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斯坦利和雷曼说,那些高大上的目标,由于非常复杂,涉及的信息变量太多,而现有的技术和理论又由于水平所限,无法立刻拿出一套可行的实现与解决方案,所以那种想象中,明确的行动路线图,是没办法画出来的。斯坦利和雷曼说,实际上,人类前沿技术科学的突破,倒像是某种探宝行动:我们要在一个巨大、黑暗,结构复杂,放满了物件的房间,或者沼泽地里慢慢探索。而我们渴望的那个成果或者奖励,很可能就隐藏在某个角落里,和一堆看似和它无关的东西放在一起:比如,有一堆,是火的使用、轮子、弓箭等等,是人类早期进入农业定居文明所必需的技术,而远处,则是个人电脑、光纤等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所必需的技术,诸如此类。我们必须在黑暗中慢慢摸索前进,做出标记,得知哪些地方是探索过的已知空间,而哪些区域尚未探索。如果是沼泽地,我们还要找到那些帮助我们继续前进的踏脚石,以便达到更远的地方;甚至,在这些星罗棋布,分散在各处的宝藏物件里,很多物件之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你只有发现了A,才会得到宝贵的线索,了解B或者C在哪里。
在这种情况下,你越是设定一个详细明确的目标,制定周密精确的方案,反而越无法达到目的。回顾人类技术发明史,就会发现太多“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案例:比如,日常使用的家电微波炉。我们一定会觉得,肯定有一家消费电子企业,或者某个发明家,想制造出一台方便快捷的食品加热器,然后就致力于发明一种耗能少,又安全的加热技术,最终选中了电磁波。但实际上,人类使用电磁波装置的历史,要比我们使用微波炉的历史长得多: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能够持续稳定发射电磁波的磁控管就被制造出来,用于雷达探测装置,并在二战中被不断改良,直到1946年,美国军工企业雷神的一位工程师斯宾塞,在雷达测试中,无意中发现自己兜里的巧克力,因为靠近设备太近而被熔化,这才意识到,电磁波还能有加热食物的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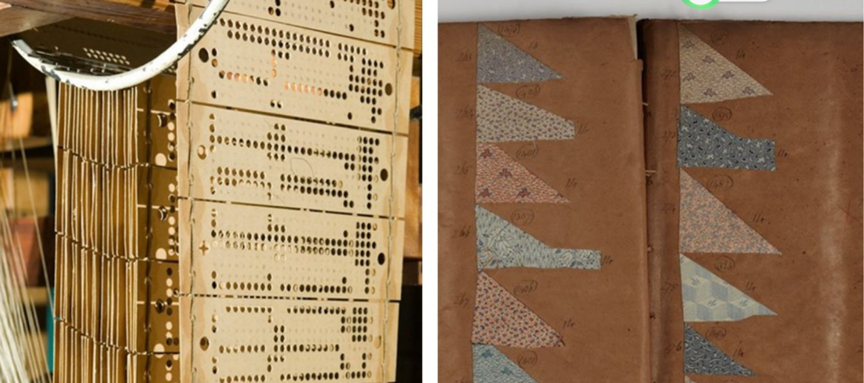
再比如,数据的存储,对于计算机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但实际上,最早发明,并把数据存储技术投入应用的,却是纺织工业。早在18世纪,有个法国机械师和发明家,叫沃康松,他就构思了一种能让提花机快速编织出图案复杂布料的发明:打孔卡片。由于布料上的图案,是由不同颜色纱线彼此叠压形成的,所以在此之前,要想让提花机编织出图案复杂的布料,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绘图员,在机器旁边盯着,根据图案,手动控制不同颜色纱线叠压的方式,非常辛苦,效率还不高,所以图案复杂的布料产量低,价格昂贵。而打孔卡片的作用,就相当于原始的计算机控制程序。具体方案就是,一沓子打孔卡片,被放在提花机底板上,编织针运行时,遇到卡片上的小孔,就从孔洞里穿过去,挑起纱线,让垂直方向的其他纱线从下面穿过。所以,一组分别在不同位置打了孔的卡片,就能精确控制各个特定位置的编织针何时抬起,从而快速编织出图案复杂的布料。到了19世纪,“打孔卡片”引起了英国数学家巴贝奇的注意,他认为,打孔卡片既然能够“储存”布料的打印图案,肯定也能够记载复杂的数字计算模式,应用到早期的机械计算机上,让计算机按照程序进行复杂的数字运算。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早期电子计算机问世之后,科学家又发现,可以把早期的电脑程序,翻译为一组二进制数字密码,再通过打孔卡片储存,运行时先让电脑读取,然后再运行。
所以你看,如果进行复盘的话,很多通向重大技术进步或者创新的所谓踏脚石,都是人类在其他看似无关领域进行探索时发现的。这些踏脚石诞生时的原初应用场景,也和最终那个高大上的目标毫无关系。斯坦利和雷曼甚至还提出了一个假设,经常读网络文学的人肯定听到之后不会感觉陌生:那就是,假如几个现代IT工程师和科学家集体穿越到古代,还能够召集一群当时最聪明的人,那么,他们是否能用“目标导向”模式,组建一个项目团队,造出一台计算机?答案肯定是不行的。表面上,项目组遇到的瓶颈是,建造计算机的基础设施和原材料,从电力、工业机床到纯净的硅,在远古时代压根无法得到,但深层理由是,古代人无法想象,制造这样一台机器,到底目的何在。很明显,只有当人类的经济和科学研究活动复杂到一定量级时,这些建造计算机相关的技术材料,才会出现;同时,人类也会意识到,需要一种具备超级计算和信息处理能力的机器。
不仅如此,过于具体但遥远的目标,还会具有极大的误导性,让我们走上一条错误的探索或者研究路径。在书中,斯坦利和雷曼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设你现在变成了一个造物主,手里有一颗环境和地球一模一样的星球,这里已经有了一些简单的单细胞生物,请问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进化繁育策略,才能让这颗星球上诞生像人一样的高度智慧生物?
斯坦利和雷曼说,如果按照我们习惯的“目标本位”策略,那么我们的策略就应该是,坚持给所有的单细胞生物测智商,然后选择那些智商最高的进行配对繁衍。当然,听到这个逻辑正确,但实际荒诞的答案,所有人肯定会哈哈大笑。如果我们从生物神经科学角度拆解一下智慧的本质,和生物演化的过程,就会发现,高度智慧生物的诞生,压根不是自然演化的目标,充其量只是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首先,让我们来看下,智慧的本质是什么呢?生物学家、科普作家王立铭曾说,智慧,就是个体和环境互动的模式:通过捕捉信息、积累经验,再通过总结规律,改善应对的策略和技巧。说白了,智慧就是一种学习能力。从神经生物学角度讲,学习,就是生物体内的神经细胞之间,通过信号传递,产生了连接与共鸣。
那么对于地球早期生物来说,怎么提升学习效率呢?最便捷的方法就是,身体内有足够多的神经细胞开工,同时连接、提升单位时间内信息交流的总量。所以,多细胞组成的复杂生物,就要比单细胞生物具备碾压性的优势。不过,从单细胞演化为多细胞,背后的首要推力并不是要发展高级智慧,而是生存;这里面的理由很简单,在当时生物种类稀少、形态相似的情况下,谁的个头越大,被吃掉的风险也就越低,还可以成为位于食物链条顶端的捕食者。
同时,成为多细胞生物还有一个好处,体内各个细胞可以按照各自的专长分工,让自己所属的这个集体,同时可以处理很多任务,从运动、生殖到制造能量等等。
英国理论物理学家杰佛里·特纳,曾经写了一本《规模》,里面提出一个克莱伯定律,生物自身的体积和结构复杂程度越大,维持自身运转的能耗反而越小,具体来说,规模每扩大一倍,就会产生25%的节余, 所以说,生物为了更好地生存,就要提升自身结构的复杂度,实现规模效应;而随之诞生的高智慧生物,比如人类,只是这场沼泽探索中,意外找到的宝藏盲盒。用作者斯坦利和雷曼的话说,就是,自然演化中的竞争,并不是全方位的,每一种生物并不需要达到整体最优,完全可以在自己所处的局部生态中达到局部最优即可,甚至还可以通过偶然的突变,产生出属于自己的生态位。 所以,所有生物都具备了生存和繁衍这两个基本能力后,演化就变成了一场典型的“非目的性探索”。换句话说,当生物的演化,诞生出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这样的复杂形态的时候,各类生物之间的竞争,开始让它们各自在各自的生态位上开展局部竞争。跑不快又力气不大的人类,就演化出了复杂的大脑结构,来对抗其他动物。所以说,自然之所以能在演化过程中,创造出人类这样高度智慧的“另类”生物,恰恰是由于,它没有把“诞生人类级别大脑”,作为自己的目标。
同样的情况,在科学家训练人工智能的场景下也经常出现,诞生出无数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况。
斯坦利和雷曼就举了一个自己进行人工智能训练的小案例:先设置一个平面迷宫,然后训练机器人顺利走出迷宫,到达出口。出乎意料的是,如果算法被设定成尽快到达出口,机器人反而进步迟缓,因为它总是遵循目标第一的原则,想规划一条最便捷的路线直达门口;而我们人类理解中的合理路线,都会被机器人判定为,在某些时刻远离了门口,背离了目标,所以是不正确的。这就导致机器人永远是一出发,就朝着出口方向猛冲,撞上迷宫中的墙壁。你看,通过这个小小的计算机试验,“目标至上,导致错误解决路径”这个道理,就被演示得清清楚楚。
那么如何实现创新和突破呢?斯坦利和雷曼说,首先要给自己的探索或者研究设置一个底层逻辑,那就是,尽量把它当做一种对有趣和新奇的探索;把我们的目光,从所谓的伟大、遥远的目标上暂时挪开,而转向我们身边可见范围内,可能埋藏的宝藏,和通向陌生区域的踏脚石。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要问了,追求新奇性,听起来既漫无目的,又很难把控,由这种原则来指导科学研究或者技术创新,真的靠谱吗?斯坦利和雷曼就说,别担心,首先,探索未知,是人类持续进化、文明发展背后的最基础推力,即使最终失败,我们追求新理论和解决方案的努力,也会比循规蹈矩地沿着既定方案进行探索,更能获得宝贵的经验与数据。
为了证明这一点,斯坦利和雷曼就在书中讲述了一个他们做过的人工智能虚拟实验,实验的目的是让一个拥有人类一样双腿的机器人,最终学会行走。这两位程序员为机器人编写的算法中,优先目标并不是尽快能够双腿行走,而是尽可能让机器人用自己的双腿做出一些新奇的动作。出乎意料的是,当设定的算法是鼓励机器人做出新奇性行为时,它学会走路所用的时间,远远少于目标被设置为尽快学会行走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如果机器人被设置为“尽快学会行走”,那么在算法逻辑里,摔倒就是一件坏事,机器人会努力避免摔倒,但同时也限制了它对各种行走姿态的试错;但如果是以新奇性动作为优先目标,那么机器人一开始会以各种姿势花式摔跟头,但在这个过程中,它逐渐学会了踢腿、摆动身体,而这两个动作,正是实现双腿行走的基础。
甚至有时候,科研人员纯粹出于找乐的“玩闹”行为,也能促成意想不到的技术变革:比如,号称将引领下一次工业革命的3D打印技术。1995年,还在麻省理工学院当研究生的吉姆·布莱特和自己的朋友安德森,被导师拉进课题组,研究如何改良一款混凝土喷射机的喷嘴。但是,布莱特发现,喷嘴总是堵塞,估计是混凝土配方有问题,可这事儿又不归自己管,那为什么不用喷嘴来搞点有趣的东西呢?于是,他和安德森从杂货店搞来了各种材料,从糖霜、蛋糕粉到奶酪碎,然后把这些材料喷射出去,形成固体,然后他们又灵机一动,把喷嘴和打印机连起来,就能“打印”出各种各样的立体字母。最终,这个革命性的发明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利和7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
甚至,在一个创意或者革新还不能确定具体应用场景,甚至功能还不完全的时候,那些有敏锐眼光的探索者,也会从直觉中感受到,这是一块意义重大的踏脚石,将把自己的认知边界大大推进。比如,我们刚才提到过的硅谷教父格雷厄姆,他曾经主持过世界上第一个互联网应用程序Viaweb的开发。格雷厄姆说,对于一个天才程序员,或者黑客来说,哪怕写出来的程序只有一部分能够跑起来,那就说明它还有希望,值得继续投入精力改进。实际上,在程序编写中,很多灵感是在边写边构思中产生的,如果你执着于做一个完美的方案和计划,而不着手开工,那么你将和许多本来可以诞生的妙点子失之交臂。当Viaweb刚刚诞生的时候,那些上门的风险投资人总是问格雷厄姆,你们未来半年的计划是什么?格雷厄姆的回答往往都是,没有具体计划,但我们会对程序做出任何能够想到的最佳改进。
在斯坦利和雷曼看来,在今天这个技术飞速进步,各个科技领域交叉融合,综合创新的年代里,最有可能做出重大发现,出成绩的,是那些兴趣广泛、嗅觉灵敏,始终对新事物、新理论抱有开放心态的“寻宝者”。他们往往一专多能,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中不断探索未知,持续漫游,为自己和后来者构建了一块又一块踏脚石,留下自己“到此一游”的标记,最终在意想不到的技术或者时间节点做出了重大突破。 格雷厄姆,就是一个典型的“寻宝者”,尽管他更愿意以“海盗”自称。格雷厄姆在康奈尔大学学的是哲学,但深刻感觉自己应该从事和技术相关,直接改变世界的东西。于是,它就在研究生时代去了哈佛大学计算机系,可当他真正开始学习编程和人工智能理论的时候,心有旁骛的格雷厄姆又迷上了视觉艺术,利用假期,开始在著名的罗德岛艺术学院学习绘画。格雷厄姆总结说,自己同时涉猎多个领域,带来的好处是一种融会贯通的“大局观”。比如绘画和编程,其实在底层逻辑上是相通的:都需要有洞察力、精确性,从用户需求出发,具有美感,但同时又具备开放性,可以随时修改优化。
不过,斯坦利和雷曼在书里提醒我们:那些科学史上看似“灵光一现”“神来之笔”的创新突破,从来不是偶然性的,只是因为当事人在漫长艰辛的探索中,已经发现了无数块踏脚石,在不知不觉之中,距离这个神秘宝藏只有一步之遥。例如,即使牛顿与苹果的故事真的存在,那也只能说明,苹果落地,是引领牛顿创造万有引力定律的最后一块踏脚石。在此之前,牛顿已经在数学与天体物理领域进行了多年的潜心研究。苹果落地这个现象,无数人目睹过,但只有牛顿能够把它与天体之间的引力作用联系起来;归根结底,这是源于牛顿在长年研究中形成的敏锐观察力和开放心态。
好了,这本《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的大致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两位作者,斯坦利和雷曼,可以说是大道至简,没有使用太多人工智能专业术语,甚至没有摆任何一个数学公式,而是用风趣而平实的语言,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截然不同的技术创新图景与方法论:不要拘泥于目标,不要死板地设定具体方案,以兴趣为持久动力,以漫游寻宝为心态,才是抵达伟大与成功彼岸的底层逻辑。
在本书中,斯坦利和雷曼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和许多科学创新史上的真实案例,来证明,在高技术领域,“唯目标主义”会带来视野狭窄、方法路径错误等种种弊端。过度强调“目标导向”,在两位作者深耕的人工智能技术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究竟存在不存在一种通用普适性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在理解人类语言时,是让人工智能发挥现有算法的优势,利用越来越庞大的数据库进行深度学习?还是走截然相反的路子,尝试人工智能像人类那样思考,理解各种语言概念背后的逻辑关系?似乎在肉眼可见的未来,这些问题暂时还不会有明确的答案。
同时,斯坦利和雷曼还对今天美国高科技企业创新体制中的一些弊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对于“迅速实现某个具体技术创新”,以及尽快盈利的执念,正在让一度充满活力的美国高新技术产业陷入歧途:一方面,是暂时无法产生直接效用,但可能会引发重大突破的“踏脚石”技术,得不到重视和资助;但另一方面,则是许多“看上去很美”,但远未成熟,应用场景不明确的技术,由于资本的助推热炒,迅速泡沫化。虽然斯坦利和雷曼的批判,是着眼于美国,但其中的某些观点,也值得今天发展中的中国借鉴:所谓“只要大量地投入资金,就能可靠地产出特定研究领域的根本突破”,这个策略已经被证明存在严重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反过来说,无特定目标的探索漫游貌似不可取,但却符合科学探索的本质。
所以,斯坦利和雷曼,借助本书,向所有准备探索未知世界,推进技术前沿的人发出呼吁,不要盲目地把目光投向远方,而是要关注你身边,脚下的每一块踏脚石;虽然它们只能暂时导向另一块,但我们要相信,正是由这些踏脚石连接而成的创新链,才是通向伟大的发现之地的正确路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此外,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在科学探索中,任何理论、解决方案,乃至材料或者技术的价值,往往是和它的“新奇性”挂钩的,所谓“新奇才是王道”。
-
不要拘泥于目标,不要死板地设定具体方案,以兴趣为持久动力,以漫游寻宝为心态,才是抵达伟大与成功彼岸的底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