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鲸鱼海豚有文化》 杨以赛解读
《鲸鱼海豚有文化》| 杨以赛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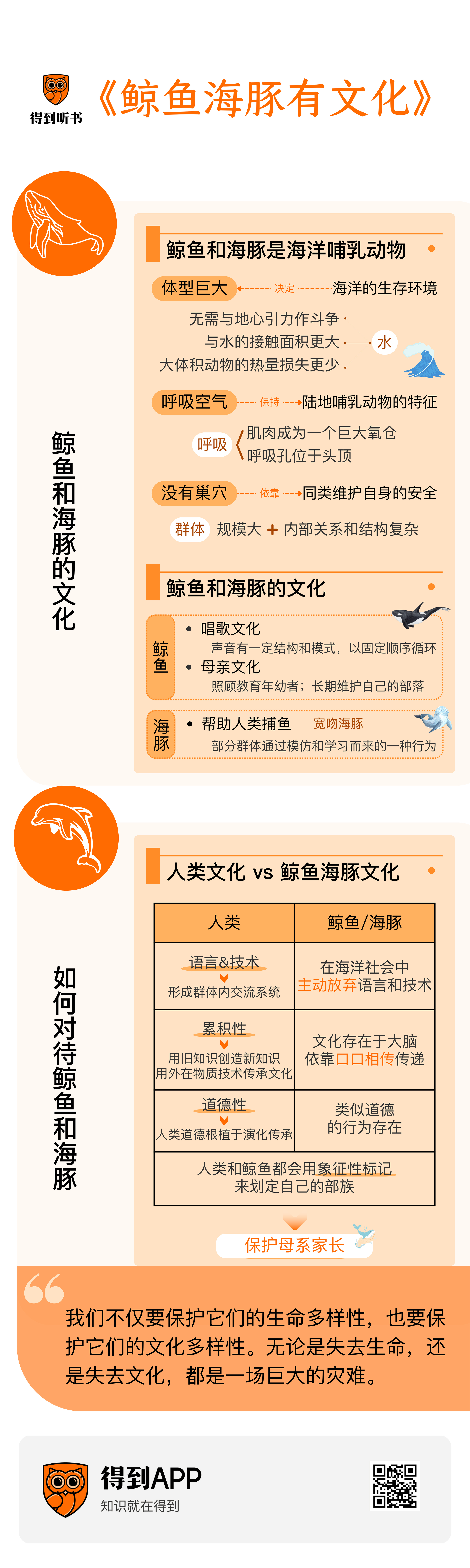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鲸鱼海豚有文化》,副标题是“探索海洋哺乳动物的社会与行为”。这是一本为我们介绍鲸鱼和海豚物种文化的书。
社交网络上时不时便会流传起一些跟鲸鱼和海豚有关的轶事,比如它们的歌声、它们的智商和灵性,以及它们与人类友好互助的关系。这两种动物,似乎一直以来承载着我们对于海洋非人类文明的想象,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对它们的认识只是停留在那些趣闻轶事。它们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动物,它们是否真的发展出了文化呢?今天这本书便回答了这个问题。
书的作者有两位,哈尔·怀特黑德是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生物学系研究教授,出版过《抹香鲸:海洋中的社会进化》《动物社会分析》等书,卢克·伦德尔则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海洋哺乳动物研究中心的生物学讲师。两人长年以来观察和研究鲸鱼和海豚,在这本书中,他们试图定义什么是鲸类动物文化,它对鲸鱼和海豚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以及最终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他们在书的前言中写道:“我们认为一些鲸鱼和海豚有某种文化形式,而这种文化是在一个与人类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演化而来,并持续运作,其和人类文化有惊人的相似性,但也同样有着深刻的差异。我们相信,这种文化是鲸鱼之所以是鲸鱼的一个重要因素。正确地理解这一点,不仅可以让我们更了解鲸鱼,也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人类自身。”
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将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了解鲸鱼和海豚是一种怎样的生物,以及它们究竟有怎样的文化。第二部分,我们来了解,倘若我们将鲸鱼和海豚视作一种有文化的物种,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和对待它们。
我们先来简要了解一下鲸鱼和海豚,它们都属于海洋哺乳动物。早在人类之前,哺乳动物就统治了地球大部分陆地,它们呼吸空气、拥有脊骨、胎生繁殖,这些特征让它们在陆地上有很强的适应性,但海洋是和陆地完全不同的环境,只有极少数的哺乳动物征服了海洋,鲸鱼和海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大部分人一提起鲸鱼,第一印象是大,更准确地说是巨大。鲸鱼为何体型如此巨大,这是由海洋的生存环境决定的。海洋的基本特征是水,水的密度大约是空气的840倍,这意味着海洋生物不需要和地心引力做斗争,体重再重也不构成障碍。另外,水的密度大,摩擦力也大,因此在水中移动要比在空气中移动困难得多,体型越大的生物因为与水的接触面积更大,所以反倒能够移动得更快。一只虎鲸的巡游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10公里,而一只磷虾的巡游速度每小时只有0.2公里。再有,水是所有液体中比热容最大的,所以水是很好的冷却剂。这意味着在水中保持体温是非常困难的,大体积的动物遭受的热量损失比小体积的动物要小很多。
但是海洋哺乳动物也仍然保持了一些陆地哺乳动物的特征,比如说要定期浮出水面呼吸空气,这一点对它们来说是一个麻烦。比如对抹香鲸来说,它常常在水下1公里的地方觅食,离水面那么远,意味着很有可能呼吸不及时。所以海洋哺乳动物必须得更有效地利用氧气,它们肌肉里的保存氧气的肌红蛋白更为活跃,这让它们的肌肉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氧舱。另外,鲸鱼和海豚的呼吸孔不在脸部,而在头顶,这也便利了它们的呼吸。
海洋生物还有一个突出特征是,大部分在海洋的动物并没有巢穴,它们尤其要依靠同类来维护自身安全。研究海豚几十年的生物学家理查德·康纳曾说:“也许没有其他哺乳动物群体,是在这样一个全无庇护之地演化而来。许多鲸类动物,尤其是体型较小的鲸类,它们除了彼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让其藏身其后。”正是因为这一点,鲸鱼和海豚往往成群出现,群体规模很大,群体内部有着复杂的关系和结构,换句话说,它们有它们的一套文化。
大部分人应该都听过“鲸鱼会唱歌”这个说法,这一点并非空穴来风,它最直接地显示了鲸鱼之间存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科学家罗杰·佩恩利用美国海军水听器录下了一头座头鲸的声音。这是一些很响亮的声音,哪怕15公里外的水听器都能接收到。另外这些声音有一定的模式和结构,它们会以一个固定的顺序不停地循环,换一句话说,它有其韵律,这也是为什么会把它称之为歌声的原因。罗杰·佩恩在1970年推出了一张名为《座头鲸之歌》的黑胶唱片,鲸鱼由此在人们印象中不再只是一种可食用的巨型鱼类,而是作为了会唱歌的生物,这一点极大地推动了1982年国际捕鲸委员会宣布暂停商业捕鲸。
20世纪90年代,生物学家迈克尔·诺德在澳大利亚东海岸研究座头鲸的歌声。在基本已经熟悉这一地域座头鲸的歌声后,1996年他突然听到有一头鲸鱼唱着一首全新的、完全不同的歌。到1997年,这首歌变得流行起来,越来越多的鲸鱼唱起这首歌,到了1997年年末,几乎所有经过佩雷吉安海滩的座头鲸都在唱这首歌。这让诺德感到极大的震撼,因为只有一种方法能让数目众多的动物在短时间内唱出同一首歌,不是基因,也不是个体的学习,只能是文化。诺德后来发现鲸鱼所唱的歌并不新,它是一首在西海岸早就流行起来的歌。一个合理的设想,西海岸的一头座头鲸错游到了东岸,给东岸带来了一首颇具诱惑力的全新歌曲。用作者哈尔和卢克的话来说,这就好比1964年2月,披头士乐队穿越大西洋来到美国,之后所有美国的乐队都开始模仿披头士的风格,这一举改变了北美音乐的进程。
那鲸鱼为什么要唱歌呢?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种解释。研究者们发现一般只有雄鲸会唱歌,而且它们往往会在繁殖地或者是迁徙途中唱歌,这些发现强烈提示出,鲸鱼的歌声似乎与求偶相关。但这只是一种假设,无法确证。我们唯一能确证的是,鲸鱼的歌声以相当稳定的速度演变着,偶尔会有革新,这其实和人类艺术的特征是很相似的。作者哈尔和卢克在书中提出说,人类的艺术是其神经生物学和文化压力双重作用下的产物,鲸鱼的歌声背后或许也是如此,有生理和环境的原因,也有其文化演变和发展的原因。举例来说,生物学家马克·麦克唐纳曾在2009年公布过一项发现:过去的30年,全球各地海洋中的蓝鲸之歌的音高逐渐降低了10%,换一句话说,蓝鲸的歌声正在变得越来越深沉。针对这一点有很多种说法,从生理或外在环境的角度来讲,有生物学家提出,这可能由于雌鲸的偏好变化,雄性蓝鲸为了求偶不得做此调整。此外也有人提出海洋声音环境的变化,海洋变得越来越嘈杂,鲸鱼得要调整音高来保证可听性。但我们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一点,作者哈尔和卢克在书中提到一个假说,文化的改变有时候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外部诱因,比如我们人类的服饰潮流常常就很随意,一时新一时旧,所以流行语说“时尚是一个轮回”。或许我们也可以把鲸鱼的歌声越来越深沉,看作是一个潮流趋势,可能这阵潮流过去了,它们的音高就又高起来了。
此外,鲸鱼还很受关注的一点是它们的母亲文化。像虎鲸、抹香鲸、黑鲸还有白鲸等等,它们的群落都有很明显的母系特征,也就是说它们从一出生就是跟着母亲和母亲的姐妹生活,它们围绕母亲搭建“部落”。这有其好处。母系鲸鱼在整个生命都认识彼此,并将一直待在一起,这让它们更容易合作和交流,并借此形成传承、文化。以虎鲸为例,虎鲸的一生都待在一个母系氏族中,它们年复一年地和同样的伙伴移动、社交、打猎,这些伙伴通常就是它们的亲戚。虎鲸也被称为“杀人鲸”,它们是海洋当中的顶级捕食者,它个头大、力量大、速度快,并且有着大型的下颚和牙齿,它的攻击性可能与鲨鱼相当,但它们在捕猎的时候却是极度小心的,很少单独行动,依靠精细的群体合作。作者哈尔和卢克认为,虎鲸的猎捕行动彰显出它们极度保守的文化特征,一套生活方式坚持到底,它们甚至会因为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拒绝与对方交配,由此它们被划分成了不同类型,彼此有彼此的生活方式,互不干扰。
抹香鲸部族也有母系特征。雄性抹香鲸在大约10岁的时候就会离开它的母亲,青春期的雄性抹香鲸会在温带水域与其他雄性抹香鲸组成临时性的群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会向着越来越冷的气候地带移动,并且会变得越来越形单影只。大个的雄性抹香鲸有时会联盟,然后无缘无故地一起在海滩上搁浅自杀。鲸鱼的集体自杀现象存在几千年,甚至几百万年了。早在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就感叹说:“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们会触底搁浅在海岸上,没有任何明显原因。”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按照遗传演化的看法,生物一般会为了适应环境而做明智的事情,但集体搁浅显然是对自身和对部族都无益的一件事情。作者哈尔和卢克认为,这背后或许有文化的作用,有时候文化会驱使我们做出愚蠢的行为,这一点想必不用多说了。鲸鱼的集体自杀现象正提示出,我们有可能从一套文化中受益,但是也有可能成为一套文化的牺牲品。
好,说完鲸鱼,我们再来说一说海豚。很多人对海豚很着迷,一方面由于它们可爱的外形,另一方面由于它们足够友好和聪明,能够迅速掌握必要的技能和知识,并且主动与人类合作。社交网络上流传着很多海豚与人类合作的故事,这些故事激发出了很多对海豚的浪漫想象,但是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巴西、印度、毛里塔尼亚、缅甸还有地中海地区,都有过海豚帮助人类捕鱼的记录,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巴西,在巴西南部的拉古纳附近,当地渔民与宽吻海豚合作捕鱼,已经持续了很多个世代。这个合作先是由渔民把渔网带到水中,然后渔民拍打水面向海豚示意,让海豚知道自己位置。海豚确定之后,会拱起背准备下潜,这个时候渔民把网撒出去,海豚则开始将附近的鱼类驱赶进渔网。像这样的合作是怎么达成的呢?对人类来说,回报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能因此捕到更多的鱼,但对于海豚从中究竟获得了什么就很难说了。更难回答的是,这种合作最初是怎么发生的,是渔民训练了海豚吗,还是无意之中训练的呢?海豚拱背下潜是向渔民有意发出的信号吗,还是只是渔民刻意捕捉到的信号?另外,为什么只有不到一半的本地海豚种群参与到合作中,另外一半不参与的原因又是什么?
有一个例子或许可以拿来与之比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生活着一种小鸟,叫黑喉响蜜䴕,它会用叫声将人类引到蜂群所在地,甚至会向人类指示蜂巢的位置。一旦人类提取了蜂蜜,它们就会进到蜂巢,吃剩下的蜜。但是这种鸟几乎是无差别地发出信号,比如它们也会向狒狒和猫鼬发出这类信号,而且这种行为在这种鸟的各种种群中都有出现,这提示出,它们指引蜂蜜的行为很有可能有遗传基础。相较之下,海豚的合作捕鱼行为更像是一种文化行为,是部分群体通过模仿和学习而来的一种行为。
有很多的实验显示,海豚有惊人的模仿和学习能力。1988年,南澳大利亚的一家商业水族馆救治了一只雌性宽吻海豚,他们给它取名叫比莉。三周的治疗期,比莉一直在水族馆里面和其他海豚住在一起。水族馆里面的海豚学习了各种各样的表演行为,其中一种是“尾巴行走”,也就是拍打尾巴使自己垂直于水面,然后保持这个姿势向后移动。比莉在休养期间没有经过任何训练,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把它放归野外后,比莉也开始用尾巴行走。更令人惊讶的是,没过多久,附近有越来越多的海豚也出现了类似于用尾巴行走的行为。这个行为在野外是没有任何用处的,相反还要消耗很多的能量。它只能被理解为,比莉通过自发的模仿和学习,给它的同类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游戏,并且成了流行。
研究儿童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模仿行为的专家安德鲁·怀滕曾说,海豚甚至可能比类人猿更擅长模仿人类。正是因为这样出奇的模仿和学习能力,海豚曾被征召入伍。美国海军拥有一支现役海洋哺乳动物行动部队,海豚在其中负责提供港口安保,主要是探测水下地雷,它们曾经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一旦注意到海豚在这方面的天赋,那解释海豚在自然环境中的各种复杂性行为就不可能绕开这一点,它们背后有遗传和生态的成分,也有可能有社会性学习的成分,换言之也就是文化的成分。
两位作者在书中分析很多鲸鱼和海豚的行为,并试图从中窥视鲸鱼和海豚的文化,坦白说这只能是一种管中窥豹,现阶段我们很难获悉鲸鱼和海豚文化的全貌,并且眼下的分析也含有大量的假说成分。两位作者甚至在书中承认说,理解人类文化都已经如此困难了,理解和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环境中的鲸鱼和海豚的文化,就更不用说了。但他们一再强调,这一视角是很重要的。文化在人类社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着人类的进化。演化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和埃尔斯·萨瑟马利曾提出一个极具开创性的看法:人类生命的演化有过8次巨大的演变,其中第8次是从灵长类社会到人类社会。这次转变的关键在于信息不再只经由遗传传播,而开始更多经由文化传播。这之后人类的演化就不能再忽视文化了,人类基因可能会为了应对文化压力而演化,这被称作“基因-文化协同演化”。如果我们承认海豚、鲸鱼存在文化,或者说我们承认非人类文化的存在,那这些非人类物种之间是否也存在相类似的协同演化呢?带着这一视角去看待鲸鱼和海豚这样的物种,我们或许能发展出更多的方法和举措来理解、研究和保护这些物种。两位作者甚至在书中说,我们必须带上这一视角,哪怕至今仍然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鲸鱼和海豚已经发展出文化。他们在书中引用了日本著名鲸类科学家粕谷俊夫的一段话,他说:“如果某个鲸类动物的表现提示有文化存在的行为特征,或者如果它具有适宜保存一种文化的生活史和群体结构,那么出于保护的目的,更安全的做法是,假定文化是存在的。”
说到这里,那假使我们不去争论鲸鱼和海豚中是否真的存在文化,我们就把它视为是一种有文化的物种,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生物呢,以及我们又该如何对待这种生物呢?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当我们关注到一种文化,总是难免会将它和人类文化做比较。尽管这种比较有时候看起来是很荒谬的。两位作者在书中说,地球上,人类一直假定自己比鲸鱼和海豚更聪明,因为他们已经在建造城市、制造车辆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鲸鱼和海豚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水中无所事事。但是反过来说,鲸鱼和海豚可能也一直认为它们比人类聪明得多,原因可能完全相同:它们能做到的事,人类并不能做到。像这样比较两种在完全不同环境和物种间产生的文化,是没有结果的,论其优劣也是荒谬的,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尝试关注当中的差异,因为我们有可能从差异中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彼此,并由此决定我们要如何对待彼此。
人类文化有两个关键,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技术。人类掌握了语言,更准确地说,人类掌握了句法,也就是用有限数量的单词,加上一些规则,然后在一个交流系统中表达出无限多的概念。据目前的研究显示,鲸鱼和海豚显然是能够交流的,但并不使用句法,或者只是用很简单的方式使用它。它们在人类的教导下可以学习和使用一些句法,所以它们并不是不会,而是在海洋社会中,它们放弃了这一块。此外,鲸鱼和海豚也显然不使用技术。部分海豚有过自发用海绵来保护鼻子的行为,但是总体上它们对物质性的技术是不感兴趣的。
人类文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的累积性。用进化生物学家彼得·理查森和罗伯特·伯伊德的话来说,似乎没有任何其他物种,对文化的依赖达到像人类那样的程度。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我们懂得用旧知识创造新知识。鲸鱼和海豚的文化有一定积累性,比如它们发声文化的演变,就显然是在一定积累基础上达成的演变。但相对于人类懂得用外在的物质技术来传承文化,比如说书籍还有雕塑,鲸鱼和海豚显然还没有掌握类似的方式,它们的文化存在于它们的大脑,靠口口相传来传递。
人类文化的另一个特质是道德性。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人类的道德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演化传承之中,换而言之,道德感可能是一种本能。“得到听书”此前解读过一本《人性悖论》,讲的便是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可以演化出道德,那非人类物种又何尝不可呢?无论是鲸鱼,还是海豚,都有很多足以显示它们道德感的行为。比如,鲸鱼有帮助海豹逃离捕食者的行为,海豚也有被发现引导抹香鲸游出错综复杂的沙洲。此外还有大量关于海豚救人的记录,它们会帮助人类寻找落水者。而且,海豚似乎拥有关于“对错”的概念。有研究者曾观察到,当浮潜者过分靠近正在带幼崽学游泳的海豚的时候,海豚母亲采取的行为不是直接制止这名浮潜者,它会游向它认识的浮潜领班,提示他来约束浮潜者的行为。我们无法确证,这些行为背后有多少是条件反射,有多少是自发的,但不管怎样,它显示了类似道德的存在。
像这样的比较是很有意义的。两位作者在书中论述道,为什么人类有工具,而鲸鱼和海豚没有工具,人类有了什么鲸鱼没有的东西,让他们发展出了工具呢?人类和鲸鱼都有部族,而且人类和鲸鱼会用一些象征性的标记来划定自己的部族。比如人类会用上旗帜,而鲸鱼会用声音,这一点黑猩猩是不具备的。那黑猩猩又少了什么,使它没有发展出这一点呢?两位作者说:“这样的比较为我们考量人类文化的神秘起源,增添了一扇新的窗。”此外,像前面所说到的,这样的比较也将会影响到我们对待鲸鱼和海豚的举措。
人类花了很多精力保存自己的文化,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其中第一条便是说,“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一样必要”。但我们常常在保护自身文化的同时,却忘记保存其他物种的文化。两位作者在书中说,生态学家总是提及保护生命的多样性,却很少提到保护不同生命的文化。
倘若将文化引入进来,我们的保护举措会有更多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比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在鲸鱼和海豚当中,母系家长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长期承担着照顾和教育年幼者的角色,也长期维护着它们的部落。但当它们被捕,伤害不仅体现在一只鲸鱼的身上,而会体现在整个部落上。最直接的例子是大象,研究显示,对年长母系大象的偷猎,会直接降低其余幸存成员应对威胁的有效性,也会降低它们繁殖的成功率,并且这个影响有可能一代又一代地蔓延和持续下去,最终降低大象种群的适应力。所以,当我们谈论鲸鱼和海豚的保护的时候,我们尤其要重视对其母系家长的保护。而对其母系家长的保护,实际上也就是对其文化的保护。
人类如果失去文化,毫无疑问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对鲸鱼和海豚来说也同样如此。一只没有文化的鲸鱼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全世界的科学家,一直在利用海军水听器监听海洋中鲸鱼的歌声。1989年,有科学家听到了一种不寻常的歌声,频率大约是52赫兹。这么多年来,只有一头鲸鱼在唱着这首歌。科学家们跟踪了这条鲸鱼,它的活动跟其他鲸鱼的活动毫无关联,它就一边唱着歌,一边独自在太平洋移动。它似乎既没有学到歌曲文化,也没有学到迁徙文化,于是它找不到同伴,也没有同伴找到它,它就此被人们称为“52赫兹的幽灵鲸”。这或许提示了丧失文化的后果,没有文化,个体只能沦为幽灵。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作者哈尔·怀特黑德和卢克·伦德尔在这本书中分析了鲸鱼和海豚在自然环境中的种种行为,从中寻找其存在文化的证据。在两位作者看来,鲸鱼的歌声和它的母系特征,以及海豚和其他物种的交流和合作,都充分显示出文化的存在。他们认为,不仅仅只有外在的环境在影响着鲸鱼和海豚的演化,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应该纳入文化的视角,来理解鲸鱼和海豚的种种复杂性行为。
另外,鲸鱼和海豚的文化和人类的文化从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演化而来,有相同之处,比如说都重视部落,并且学会了用象征物标记自己的部落,但是也有不同之处,比如鲸鱼和海豚几乎不使用工具,也不使用有句法的语言。当我们将鲸鱼和海豚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性物种,我们认识、理解和保护它们的方式或许就该有所改变,我们不仅要保护它们的生命多样性,也要保护它们的文化多样性。无论是失去生命,还是失去文化,都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这本书包含了非常多和复杂的生物学和进化学的知识,但是两位作者一直试图用通俗的语言讲述这些知识,他们在书的最后写说:“我们希望我们已经让你意识到海洋中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兴盛的文化,如果有机会的话,尝试登上一艘船去海上看看那些鲸鱼和海豚吧,也许一次注视就能让你跟它们的世界产生连接。”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地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作者哈尔·怀特黑德和卢克·伦德尔在这本书中分析了鲸鱼和海豚在自然环境中的种种行为,从中寻找其存在文化的证据。在他们看来,鲸鱼的歌声和它们母系特征,以及海豚和其他物种的交流和合作,都充分显示出文化的存在。
-
当我们将鲸鱼和海豚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性物种,我们认识、理解和保护它们的方式或许就该有所改变,我们不仅要保护它们的生命多样性,也要保护它们的文化多样性。无论是失去生命,还是失去文化,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