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版)Challenger 刘怡解读
(英文原版)Challenger| 刘怡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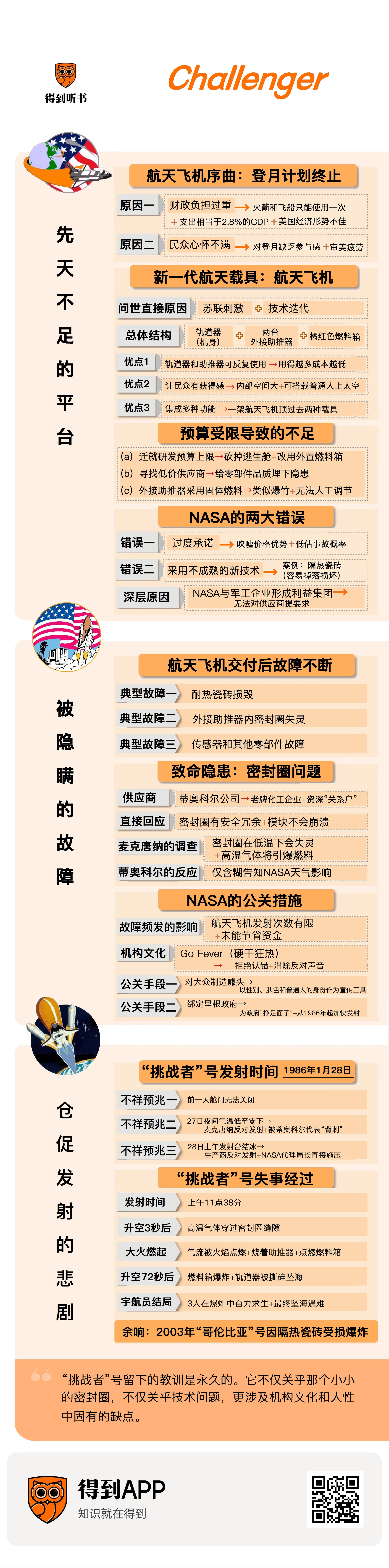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叫做Challenger,直译过来就是“挑战者号”。熟悉航天史的朋友多半猜到了,它的主角是1986年爆炸失事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没错,本书讲述的就是“挑战者”号事故的来龙去脉。原书是2024年5月在美国出版的,它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就冲上了亚马逊航天类书籍榜单的第一位,还入选了《纽约时报》的半年最佳书单。这对一本将近600页厚,充斥着专业术语的书来说,是很难得的。
为什么这本Challenger会这么受关注呢?我想,这多半和当下的“航天热”有关。在2024年的世界上,无论是中国的“嫦娥”探月工程,还是美国SpaceX的“星舰”,在媒体上的出镜率都非常高。这些航天项目的长期目标,是执行载人任务,把宇航员送上月球甚至火星。这是继“冷战”时代的“阿波罗”计划之后,人类航天事业的又一波高潮。不过,面对星辰大海的诱惑,人们忍不住也会想:载人航天除了技术门槛,还有没有其他风险?过往的历史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反复回味?这个时候,许多人,尤其是美国人,立马就会想到“挑战者”号事故。那场灾难不仅葬送了一架价值4亿美元的航天飞机,还牺牲了7位宇航员。其中一位叫麦考利夫,她是一名中学女教师,也是美国第一位接受宇航员培训的普通人。这让许多人感到,自己的“太空梦”也随着“挑战者”号一起破灭了。尤其特殊的是,“挑战者”号发射是有全美直播的。超过1亿人在电视画面里,看着它凌空爆炸;这种感受太刻骨铭心,也太令人震惊了。
不过,“挑战者”号事故毕竟发生在将近40年前,它的直接原因早就水落石出了。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挑战者”号外接助推器里的一个橡胶密封圈。许多管理学教材都会引用这个案例,来阐述“小差错造成大损失”的道理。但是,本书作者希金博特姆,对这个解释还不够满意。他进一步追问:这个密封圈,到底是质量有问题,还是设计存在缺陷?“挑战者”号的生产商和使用方,知不知道这个“坑”?还有,以“挑战者”号为代表的航天飞机,拢共就存在了30年,随后就被放弃了。这是不是说明,整个航天飞机项目都是一个错误?谁又该为此负责?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希金博特姆从2019年开始,花费4年多时间,采访了200多位“挑战者”号事故的当事人。他们中有航天工程师,有资深宇航员,还有“挑战者”号遇难者的家属。希金博特姆以这些访谈为基础,配合解密档案,才写出了这本Challenger。书中得出的结论,可以说触目惊心。它讲,导致“挑战者”号灾难的,是环环相扣的系统崩坏。“省钱至上”的政府、文过饰非的主管部门、隐瞒风险的供应商,每一个环节都存在问题。正是这个失控的系统,研发出了短板严重的航天飞机,一次又一次隐瞒技术故障,还强迫“挑战者”号在不良天气下发射。要是我们真以为,出问题的只是那个小小的密封圈,反而会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忽视更严重的系统问题。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航天爱好者,这本Challenger的内容对你都会有启发。毕竟,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也有相互协作的部门和环节,也涉及预算、调整和纠错。如何避免局部问题形成共振,给整个系统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对每个人都很重要。而Challenger一书复盘的“挑战者”号事故,就是一个经典的反面案例。弄清楚这个案例背后的真相,然后以史为鉴,给自己的“系统”多加几道保险,对个人也是很好的思维训练。
本书作者亚当·希金博特姆,是英国资深调查记者,曾为《每日电讯报》《纽约客》《GQ》等知名报刊撰稿超过20年。他尤其擅长在抽丝剥茧式的追问中,还原复杂事件的真相,因此在转型为非虚构作家后,作品相当受欢迎。希金博特姆的第一本大书《切尔诺贝利的午夜》,2021年已经引入中国,在豆瓣网获得了9.1分的高评分。这本2024年写成的Challenger,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前作,相信它也会让你大有收获。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以“挑战者”号为代表的航天飞机,在研发阶段出现了哪些技术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在第二部分里,我会为你分析,航天飞机在投入使用后,发现了哪些常见故障,它们又是如何蒙混过关的。最后,我再为你总结一下,“挑战者”号最后一次发射,有哪些不祥的先兆,它又是怎样被失控的系统最终葬送掉的。
说到“挑战者”号事故,我们得先从航天飞机聊起。1969年7月,第一批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宣告“阿波罗计划”大获成功。随后的3年里,又有5批宇航员完成登月,让“冷战”时期的美国挣足了面子。但你可能不知道,“阿波罗计划”的结束非常仓促。1972年,尼克松政府干脆利落地宣布:不会再有新的载人登月飞行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其实就是三个字:太烧钱。要知道,“阿波罗计划”从1961年立项开始,持续了整整11年,高峰期有40万人在为它工作。登月用的“土星5号”火箭和月球舱,都是一次性的,每发射一次就要烧掉4亿多美元。据美国国家航天局,也就是NASA,在1973年估算:整个登月项目的成本高达254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570亿,折合当时美国GDP的2.8%。用这笔钱,可以造16艘最大的航空母舰。而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形势并不好,政府正在勒紧裤腰带。总不能削减日常开支,饿着肚子去圆“登月梦”吧?“阿波罗计划”自然就成了牺牲品,被放弃了。
不光政府囊中羞涩,美国民间对登月计划,怨念也越来越重。1969年阿姆斯特朗第一次踏上月球时,全国舆论都把他看成英雄。但随着第二批、第三批宇航员顺利归来,老百姓的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开始质问:美国已经有了越南战争这个烧钱的无底洞,为什么还要在40万公里外一个光秃秃的星球上,“浪费”那么多钱呢?到了后期,每一次“阿波罗”飞船升空,都会有社会活动家在发射场门口抗议,要求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1972年最后一次“阿波罗”飞船发射时,电视传播权居然没卖出去,因为民众已经审美疲劳了。这对花纳税人钱的NASA,也是个坏消息。
问题是,登月可以暂停,载人航天却不能不搞。原因很简单:1971年,苏联开发出了近地轨道空间站。这种平台是有军事用途的,可以搭载重型雷达,这让美国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以美国的技术实力,搞出自己的空间站不成问题。但如果每一次把宇航员送上站,都要动用超大超重的“土星5号”火箭,又会是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更要命的是,负责登月计划的那一代科学家,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面临退休。美国的下一代发射工具,必须另起炉灶。
又要省钱,又要让民众有获得感,还得从头研发新载具:这根本就是“不可能三角”吗!没承想,NASA捣鼓了快10年,还真的把符合要求的载具研发出来了,它就是本书的主角——航天飞机。一架航天飞机的造价,也接近4亿美元,但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每次任务完成后,它可以像滑翔机一样,自主再入大气层并完成降落。而且在10年的设计寿命里,用得越多,单次发射成本越低。NASA给航天飞机起了个绰号,叫“太空卡车”,听上去就很皮实廉价。民众的参与感问题呢,也好解决。因为航天飞机的内部空间非常大,它除了携带27.5吨科研器材,还可以搭载7位宇航员。NASA打算推出一个“普通人上太空”的招募计划,在这7名宇航员里,塞进一位新闻主播或者一名中学老师,让他(她)在太空中开讲。这是一个绝佳的宣传噱头,准能激发美国公众的热情。至于技术问题吗,一架航天飞机的功能,相当于过去的一枚火箭加一艘飞船,所有功能集成在一个平台上,可以放心大胆地实施技术迭代。
不过,新项目也带来了新问题。这里要交代一下航天飞机的结构。我们熟悉的那个外形圆滚滚,很像普通客机的东西,大名叫“轨道器”,是航天飞机的主体,它有3台主发动机和2台变轨用的小发动机。但要把这么一个100多吨重的“铁疙瘩”送上太空,光靠主发动机的推力是不够的。所以,轨道器在升空前,需要像火箭一样直立在发射台旁边,再捆绑上两台外接助推器。轨道器的背部还有一个外形很像热水瓶的橘红色燃料箱,那是主发动机用的。航天飞机发射时,会先点燃外接助推器,由它们推着整个载具冲上45000米高空。随后外接助推器脱落,轨道器点燃自己的主发动机,背着重重的“热水瓶”,继续飞向近地轨道。等“热水瓶”里的燃料耗尽了,它也会自动脱落,这时轨道器已经顺利入轨,可以执行任务了。外接助推器在脱落之后,会掉进大海,可以回收使用。这就又省了一笔开支。
注意了,这里说的“省开支”,指的是未来的运营成本。在研发阶段,该花的钱还是得花。正是在研发预算上,NASA和美国政府拉扯起来了。NASA想给轨道器装上逃生舱,让宇航员在遇到危险时,可以实施自救。他们还想削减“热水瓶”燃料箱的体积,把主发动机的燃料装载在轨道器内部,这样比较安全。但那样一来,轨道器的体积和重量会显著增加,研发预算也得加码,要140亿美元。而美国政府的回答是:就给你55亿美元,多一个子儿都不行。为了迁就这个预算上限,NASA可谓绞尽脑汁。逃生舱太重,那就不要了;内置燃料箱太费钱,还是老老实实背“热水瓶”吧。在给航天飞机的子系统寻找供应商时,NASA也专挑报价低的厂商,不管它们有没有行业经验。著名的登月宇航员谢泼德,对此说过一个金句:“航天飞机的乘员,其实是坐在报价最低的那批厂商,攒出的一台便宜货里。”
预算受限还造成了另一个隐患,那就是外接助推器。从“阿波罗计划”开始,NASA使用的一直是液体燃料的火箭发动机,轨道器安装的也是这种型号。它的优点是点燃后可以反复重启,还能调节推力。但液体发动机的结构非常精密,一旦脱落后掉进海里,就会整个报废。而NASA已经拍胸脯保证说,外接助推器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为了实现这个承诺,它决定向美国空军求助。空军的建议是,用固体燃料发动机嘛!它跟弹道导弹的助推器一模一样,技术成熟,价格便宜,还不怕海水浸泡。问题是,固体发动机有一个先天缺陷:它一旦点燃,就不能熄火,必须把所有燃料耗尽为止。本书作者形容说,固体燃料的外接助推器,就像是两根大爆竹。航天飞机的轨道器,是没法自主控制自己身上捆着的这两根“爆竹”的;因为它们的点火作业,是在地面上完成的。从地面飞行到45000米高空,需要花费122秒钟。在这段时间里,宇航员只能祈祷神明保佑。如果外接助推器在这段时间出现问题,它不仅会烧光自己携带的固体燃料,还有可能引燃“热水瓶”里的液体燃料。到时整个航天飞机会直接爆炸,没有任何逃生的希望。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NASA也太可怜了。在这场“预算战争”中,它完全就是个受气包。但本书作者却说,别以为NASA很无辜,它也犯了两大错误。第一项错误叫过度承诺。为了让航天飞机项目在政府那边顺利“过堂”,NASA雇了一家不靠谱的评估公司,替它“做数据”。这家公司宣称,根据他们的计算,发射一架航天飞机,在最优状态下只需要35万美元,而一艘“阿波罗”飞船是1.85亿美元。这听起来差距确实很大。但数据没说的是,35万美元的价格,不包含燃料和检修费用;而且只有当航天飞机每周发射一次时,才能达到这个所谓的“最优状态”。这在现实中根本就做不到。评估报告还说,航天飞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10万分之一。而美国政府后来复盘“挑战者”号事故时,算出的真实概率是1/100,两者差了整整1000倍。虚报数字,欺下瞒上,这个责任只能由NASA自己负。
NASA的第二项错误,是冒险采用不成熟的新技术。这方面的典型,是轨道器表面覆盖的隔热瓷砖。轨道器本身是用铝合金制造的,它承受不了再入大气层的高温。为此,NASA在它的表面贴上了一层二氧化硅瓷砖。这种瓷砖又轻又薄,却能耐高温,是美国材料科学的新成果。每架航天飞机表面,都覆盖有3万多块这种瓷砖。问题是,瓷砖不能用钉子固定,只能靠胶水粘。而轨道器的轮廓不是直线,不同部位需要的瓷砖厚度还不一样。结果,供应商只能给3万多块瓷砖,每一块都单独开模具,再用人工贴在轨道器表面。就算是这样,轨道器每运输一次,甚至是挪动一次,都会有没粘牢的瓷砖掉下来。如果在发射准备中,任何一个小零件或者冰块,打到了瓷砖,它也会开裂甚至破孔,露出下面的铝合金机身。那轨道器在再入大气层时,就会被这个破洞连累,完全烧毁。而耐热瓷砖掉落损坏的问题,困扰了NASA整整30年,直到航天飞机退役都没解决。但他们对外却声称,一切正常,不必担忧。
听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在隔热瓷砖这件事上,NASA是甲方,产品是由供应商制造安装的。品质不过关,甲方不得提点要求吗?本书作者的结论是:办不到。因为生产和安装瓷砖的,是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它也是NASA的长期合作伙伴。整个航天飞机项目,几乎都被洛马、罗克韦尔这类强势军工企业包场了。它们从“阿波罗计划”开始,就和NASA合作,彼此形成了深度绑定的利益集团。NASA已经在报价上压了乙方一头,当然不好再提其他要求。因此,被寄予厚望的航天飞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平台。更多的麻烦也在前面等着它。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航天飞机在研发阶段,遭遇的一系列技术难题。无论如何,NASA还是凑合着把这个项目搞出来了。只不过,美国政府临到最后,还在预算上砍了一刀,把轨道器的建造数量从6架砍到了5架。去掉一架没有发动机的技术验证机,实际只有4架可用。“挑战者”号是其中第二架,它在1981年完成组装,但直到两年后才进行了第一次发射。照理说,飞机少了,应该用得更勤啊,为什么耽搁了那么久呢?原因只有一个:缺陷暴露了。
1981年4月12日,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进行首次发射。外接助推器在点火时,烧着了机翼的一个零件。几块碎片脱落下来,把轨道器表面的瓷砖砸开了一个小洞。幸运的是,这个洞在底部,不是很深,没有引发严重后果。但随后的第二次飞行又出了新问题。技术人员回收了脱落的外接助推器,打开一看,发现有一个O形橡胶密封圈被高温烧毁了。这个密封圈的功能,是控制固体燃料点火时的内部压力。因为燃料在点火的一刹那,会生成高温高压气体;如果不加控制,它会把整个燃料舱段都点燃,助推器会直接爆炸。安上密封圈,下面再留一个空腔,气体就会被稀释,燃料就会慢慢烧,而不是瞬间引爆。密封圈被烧毁,说明这道安全阀并不保险,需要引起注意。
对这个新的隐患,NASA并没有掉以轻心。他们直接找到生产密封圈的蒂奥科尔公司,要他们排查问题。蒂奥科尔是一家老牌化工企业,也是NASA的资深“关系户”。他们研究了半天,得出了一个非常敷衍的结论:助推器点火时的温度,超过了NASA最初要求的指标。不过这不是问题,因为密封圈有一套两个,上面那个烧毁了,下面那个还能起作用。换句话说,这个模块有安全冗余,没那么容易崩溃。NASA也就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套说辞。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哥伦比亚”号在第五次飞行中,宇航服出了故障,被迫提前返航。新完工的“挑战者”号也是多灾多难:1984年2月它第四次发射时,因为设备故障,差一点就丢掉了两颗价值1.8亿美元的卫星。返航途中,排水阀上脱落的冰块还打穿了3片隔热瓷砖,几乎又酿成一场惨剧。1985年7月,“挑战者”号的第八次发射也是一波几折。因为外接助推器上的传感器故障,地面工作人员紧急关闭了发动机,排查了两个多星期才恢复任务。
听到这里,你应该已经发现了:刚刚交付时的航天飞机,根本就不是一种稳定的载具。从隔热瓷砖、密封圈到宇航服,它的几乎每一个子系统都存在隐患,这沉重打击了NASA吹嘘的所谓“经济性”。按照NASA的承诺,航天飞机需要每年发射55次,才能把运营成本降到理想程度。但从1981年4月到1986年1月,4架航天飞机总共只发射了25次,平均每年刚满5次,其中还有1/4发生事故或者安全隐患。美国的太空计划,压根就没比过去更省钱。
问题是,要想叫NASA服软,承认自己做错了,根本办不到。本书作者发现,NASA在“阿波罗计划”时代,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机构文化,叫Go Fever,直译过来就是“硬干狂热”。它的意思是:项目前期已经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构成了巨大的沉没成本;这个时候要是停下来,一切都会前功尽弃。不如硬着头皮往下干,说不定能成呢?在NASA内部,一切强调安全隐患,主张推迟航天飞机发射的员工,都会被视为异类。长此以往,反对的声音也消失了。
不过,航天飞机发射一再延误,NASA对政府和公众也得有个交代。于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初,NASA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公关和宣传上。我可以给你讲几个案例:1983年,第一位美国女性宇航员搭乘“挑战者”号进入太空。同年,美国第一位黑人宇航员成功升空。1985年,一位沙特王子搭乘“发现”号进入太空。随后还有两位国会议员乘坐航天飞机进行了太空旅行。为“挑战者”号挑选的女教师麦考利夫,更是从11000多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接受了宇航员培训。整个过程几乎成了一场真人秀,一下点燃了美国民间的“太空热”。但其实,那位沙特王子、两位议员和麦考利夫,并不负责操纵航天飞机,或者执行科研任务。他们的头衔叫“有效载荷专家”,约等于乘客,噱头意味大于实际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麦考利夫和之前那几位女宇航员个人能力不够。她们非常专业,也极其勇敢。但把性别、肤色和普通人的身份当作宣传工具,还拒不向宇航员透露航天飞机的技术缺陷,这就是NASA在玩火了。
对美国政府,NASA也有一套手段。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了。他是坚定的“冷战”信徒,也是美国太空事业的支持者。NASA瞅准这个机会,把“普通人上太空”这个点子兜售给里根,很快获得了他的青睐。NASA还承诺,虽然航天飞机前期问题重重,但从1986年开始,他们每个月至少会完成一次发射,保证让里根政府挣足面子。当然,承诺是要兑现的。NASA的策略,是缩短每次任务之后,检修轨道器和助推器的时间,而且还定了一条潜规则:只要轨道器上了发射架,除非出现不可抗的自然灾害或者重大技术故障,否则一定要按期发射。这已经是罔顾风险了。
当然,要说整个美国宇航业都在搞“面子工程”,那也有点夸张。生产密封圈的蒂奥科尔公司,就有一位负责任的工程师,叫艾伦·麦克唐纳。他从1981年开始,一直在研究那个倒霉的密封圈,结果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双层密封圈在高温条件下,的确不会被完全烧毁。但发射航天飞机的卡纳维尔角航天中心,冬季气温特别低;暴露在室外的助推器表面会结冰,内部的密封圈也会因为低温丧失弹性。没了弹性的橡胶圈会自然收缩,露出边缘的缝隙。这时如果突然点火,高温气体就会顺着缝隙,引爆全部燃料,造成重大事故。问题是,假如蒂奥科尔把这个缺陷反馈给NASA,承认自己的产品存在品质缺陷,那他们的声誉就会受损,就有可能拿不到政府的新订单。因此,蒂奥科尔方面只是含含糊糊地告知NASA,低温环境对密封圈的性能“有影响”;多大呢,没说。又一个缺陷蒙混过关了。
好,刚刚我们回顾了航天飞机在投入使用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它们也是葬送“挑战者”号的祸根。不过,“挑战者”号事故本身,其实到最后一天为止,还是可以避免的。那它为什么还是发生了呢?这里我们展开说说。
1986年1月27日清晨,“挑战者”号的轨道器和助推器,在卡纳维尔角中心竖起来了。按照NASA先前的承诺,1986年会是航天飞机发射的“加速之年”。“挑战者”号除了部署两颗卫星,还要观测哈雷彗星在太阳附近的轨迹,这个时间窗只有48小时,所以最晚28日必须升空。原定计划是在27日发射,没承想,轨道器的门直接关不上了,一修就是大半天。27日就这么过去了。巧的是,蒂奥科尔公司的那位工程师麦克唐纳,当时就在发射基地。他满脑子都是密封圈的问题,所以一直盯着天气预报。坏消息很快就来了:27日深夜,卡纳维尔角的气温会下降到零下8度,第二天上午也只有零下3度。而美国此前发射航天飞机,最低的气温是12度。麦克唐纳担心,密封圈在低温下会收缩,造成不可挽回的恶果,所以坚持要求上报情况。27日晚间,他和发射中心管理层、NASA的高官以及蒂奥科尔公司的代表开了一场电话会议,坚决表示:如果气温低于12度,他不能保证密封圈的安全。然而,蒂奥科尔方面却“背刺”了麦克唐纳。他们表示,所谓“低温问题”,纯属个人意见,不代表公司立场。公司是赞成继续发射的。
不过,老天爷却以沉默的方式支持了麦克唐纳。28日天刚亮,检查人员震惊地发现,“挑战者”号的发射台上结了一层冰。这一回,就连生产轨道器的罗克韦尔公司也坐不住了。他们的代表表示:融化的冰块可能打坏隔热瓷砖,或者被吸入发动机,发射必须终止。关键时刻,NASA代理局长格雷厄姆施加了压力。格雷厄姆是里根的亲信,当时刚刚上任一个月。他已经在总统面前夸下海口,说1986年不会出现发射延误事件。更何况,电视台的摄制组已经到了发射基地,全国有1亿多人等着看直播呢。在高层施压下,“挑战者”号只做了简单的除冰作业,还是发射了。
11点38分,“挑战者”号缓缓升空。短短3秒钟之后,3000多度的高温气体就穿过密封圈边缘的缝隙,形成了一股黑色烟雾。这时,助推器的尾部正在向外喷火,火焰顺着气流,先是烧着了助推器,接着点燃了橘红色的“热水瓶”燃料箱。第72秒钟,燃料箱整个爆炸了。轨道器被直接撕成几块,四散着掉进大海。一个多月后,美国海军打捞队在100多米深的海底找到了“挑战者”号的残骸。他们发现,7名宇航员里至少有3个人,在爆炸发生时还是活着的。他们启动了应急氧气包,奋力求生,却随着乘员舱一同坠入海底。世界载人航天史上最大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为了调查“挑战者”号失事的原因,美国政府绕开NASA,组建了“罗杰斯委员会”,邀请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参与调查。那个致命的密封圈问题,至此终于公开。在最后的报告里,费曼写了这样一句话:“对一项成功的技术来说,现实应当比公关来得优先,因为大自然是无法愚弄的。”美国航天飞机的发射,因此中断了两年多。令人扼腕的是,2003年,“哥伦比亚”号也在执行任务时爆炸,罪魁祸首正是另一个技术隐患——隔热瓷砖。美国最终决定放弃航天飞机这种平台。但“挑战者”号的7位牺牲者,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结语:
好了,关于这本Challenger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距离“挑战者”号事故发生,已经过去快40年了。载人航天史最终翻过了航天飞机这一页,进入了新阶段。但“挑战者”号留下的教训却是永久的。它不仅关乎那个小小的密封圈,不仅关乎技术问题,更涉及机构文化和人性中固有的缺点。美国航天系统在这场事故中的拙劣表现,是贪婪和急功近利共同导致的;而它们存在的范围,又远远不限于航天。如何走出“硬干狂热”的思维陷阱,如何在风险面前常怀谨慎,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需要终生修炼的课题。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此外,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导致“挑战者”号灾难的,是环环相扣的系统崩坏。“省钱至上”的政府、文过饰非的主管部门、隐瞒风险的供应商,每一个环节都存在问题。要是我们真以为,出问题的只是那个小小的密封圈,反而会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
2.在航天飞机的研发过程中,预算严重受限的NASA为了争取政府的支持,不仅做出了过度承诺,还冒险采用了多项不成熟的新技术。
3.NASA内部有一种独特的机构文化,叫Go Fever,直译过来就是“硬干狂热”。它是“挑战者”号最终失事的深层原因之一。
4.在“挑战者”号事故调查报告里,著名物理学家费曼写了一句话:“对一项成功的技术来说,现实应当比公关来得优先,因为大自然是无法愚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