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写作之中》 杨以赛解读
《生活在写作之中》|杨以赛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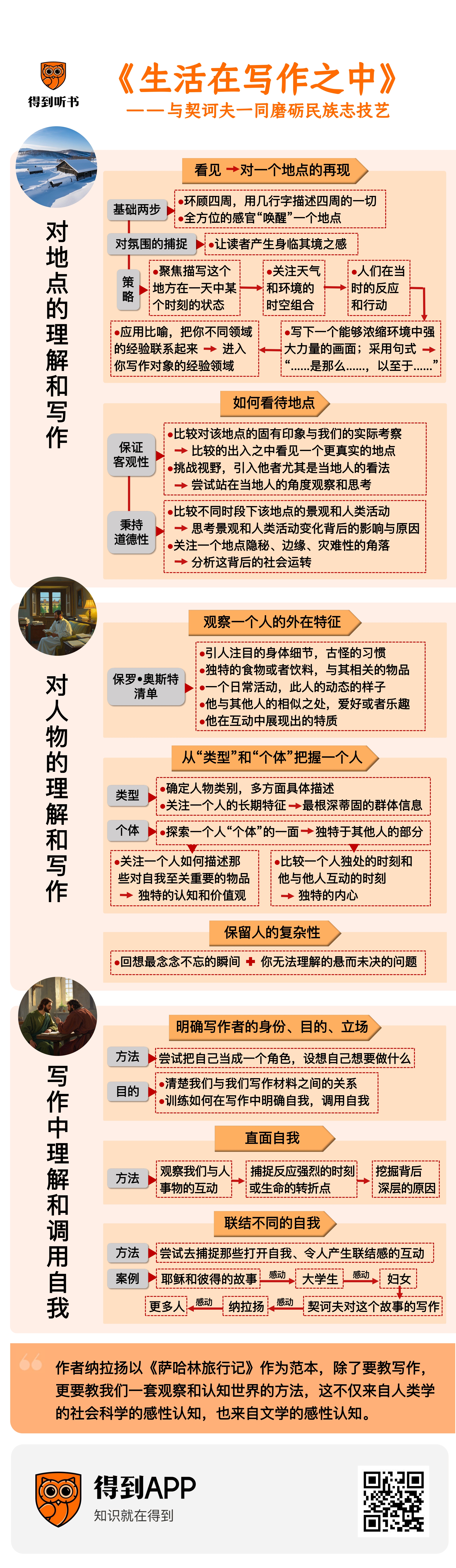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生活在写作之中》,副标题是“与契诃夫一同磨砺民族志技艺”。
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手段,是人类学家在近距离观察和分析世界的各种人群、各种情境后写出来的文本。它听上去局限在一个学科内部,但实际上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种观察、认知和记录事物的技艺,应用范围非常广,任何的非虚构写作,包括描写个人经历的随笔、回忆录、传记、游记、新闻,还有研究和调查报告等,都能从中有所获益。今天的这本书的作者基伦·纳拉扬是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曾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教授。她教授了多年的民族志写作,她说她借由民族志思考的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我们生活当中的经验材料能够由怎样的方式塑造成引人入胜的故事。
在这本书中,纳拉扬给出了一系列实用的方法和练习,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纳拉扬在这本书中引用了很多人类学和文学领域的著作作为她教学的范本,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是她最为核心的范本。1890年,契诃夫从莫斯科来到被俄国用作流放之地的萨哈林岛,了解当地人的生存状况,他做了详细的人口调查、采访,最终写成《萨哈林旅行记》,契诃夫自己形容说,《萨哈林旅行记》的写作“既是科学的,也是文学的”。“科学”可能就在于这本书的民族志属性,契诃夫一开始便打算将《萨哈林旅行记》作为一本医学人类学著作,以便申请在莫斯科大学讲学的资格,所以他在这本书中尽可能采取了科学的调查方法与科学的阐释论证,试图对一个地方的生存状况作出全面、深刻的概括和分析。而至于“文学”,它首先指向的自然是契诃夫作为小说家独树一帜的写作技能,但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一个小说家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对复杂的道德和伦理的探索。所以,从以《萨哈林旅行记》作为范本这一点,就能看出作者纳拉扬的目的绝不是写一本简单的写作指南,她除了要教写作,更要教我们一套观察和认知世界的方法,既是来自人类学的社会科学的认知,也是来自文学的感性认知。
好,接下来,我将分三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大部分写作无外乎处理地点和人物,所以第一部分我们来讲对地点的理解和写作,第二部分我们讲对人物的理解和写作。最后我们来谈自我,我们如何在写作中理解和调用自我?
先来看第一部分,我们怎么写地点呢?三十岁的安东·契诃夫抵达萨哈林岛沙皇监狱两个月后,他给他的朋友寄了一封信,他写道:“我看到了一切,现在的问题不是我看到了什么,而是我如何看待它。”这句话可以作为一个提醒,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先得看见,然后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何看待眼前的一切。
纳拉扬在书中引导说,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环顾四周,用几行字描述你四周的一切。你不用担心会遗漏,也不用担心写得不够准确,因为我们对地点的观察和再现必定基于我们当下的特定的视角,它会传达那个当下特定的关注和情绪。而且有时候这种即兴的观察反而会比煞费苦心的观察要更打动人,纳拉扬在书中提到给学生的一个写作练习,她的教师朋友经常让学生根据记忆描述一个地点,然后去现场再次描述这个地点,她发现,无一例外,总是第一次的描述会更有生命力,第二次的描述因为有太多尽职尽责的细节而让读者失去兴趣。
当你有了这段即兴写出来的内容时,纳拉扬这时候抛出了第二个问题,你的描写是不是以视觉为主?纳拉扬说大多数人对地点的描写,往往都是以视觉细节为主,这一点不可避免,但纳拉扬提醒,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利用全方位的感官“唤醒”一个地点。你可以列出一份五种感官全部参与的清单,写出你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图像、气味、声音、味道、质地、纹理和触感等。
有了这基础的两步,你应该就能大致完成对一个地点的再现了,但显然这还不够,我们除了要让读者了解一个地点有什么,我们还要追求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这就是涉及对氛围的捕捉了。可氛围似乎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由哪些东西所构成的呢?纳拉扬以契诃夫为例,契诃夫在描述萨哈林岛的一个地区的时候,他以统计数据开头:“一年中雨雪天气平均是一百八十九天,其中下雪是一百零七天,下雨是八十二天。”紧接着他描述当地居民在这些雨雪天气下感受到的压抑,而在这个段落结束,他把这些数字和潮湿阴冷天气归拢到他观察到的一个时刻。他写道:“有一次,在一个晴天里,我看到浓雾像一堵乳白色的墙壁一样从海面上涌过来,仿佛是从天穹落下一道白色的幕布。”
我们可以从契诃夫这段找到营造气氛的门路,首先是聚焦描写这个地方在一天中某个时刻的状态,其中天气是一个很好的着眼点,但是只是天气与环境可能还不足以调动人的感受,我们还要关注天气和环境的时空组合,它们作为背景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契诃夫写的是湿冷,纳拉扬在书中举了另一个例子,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描写正午的酷热,她写道:“赤裸的小脚踩在沙地上,烫得他们又忙不迭地跑回屋檐下的阴凉处,不得已要出门的妇女用硕大的橡胶树叶来遮阳,或者用湿衣服包着头。”从这一段你能更直接地看到,要让人感受到酷热,要写的不是酷热本身,而是人在酷热下的反应和行动。在所有的这些基础上,契诃夫还有一个绝招,那就是他会写下一个能够浓缩环境中强大力量的画面,当他写“浓雾像一堵乳白色的墙壁一样从海面上涌过来”的时候,这一幅画面瞬间唤起了我们对湿冷的感受。所以纳拉扬提醒,我们也要试着捕捉这样的画面,她说你不妨以“……是那么……,以至于……”这样的句式来锻炼你捕捉和描述这样画面的能力。比如安德鲁·考西在写苏门答腊岛的雨季的时候,为了让读者感受到倾盆大雨的力量和速度,他就用了这个简单的句式,他写说:“水涨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排水沟看起来漆黑一团。”
另外,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比喻在这个过程中作用很大。我们可能在各种各样的写作课上都学过比喻,甚至背诵过一些固定的比喻搭配,像契诃夫的一些比喻也许确实是一种文学功底的体现,但纳拉扬在这本书中提醒我们,比喻本质上还是一种联想的能力,目的不在文采,而在于把你不同领域的经验联系起来,比如安德鲁·考西在写挖泥土时的感受,他说:“鼻孔被湿气充满时,我还闻到一股非常微弱的臭味,就像夏天发现衣服在洗衣机里洗太久一样。”而更好的比喻除了打通不同领域的经验,它还能超脱自己的经验,进入你写作对象的经验领域。余华曾经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在写《活着》的时候,写到福贵失去了自己的儿子,福贵在月色下回望儿子经常走过的一条路,余华先是试过将这条路比喻为“一条苍白的河流”,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比喻了,但余华仍嫌花哨,觉得这不像一个农民脑袋里能产生的联想,最后他找到了“盐”这个意象,他形容这条月色的小路“像撒满了盐”。盐对农民来说是很熟悉的东西,然后盐与伤口的关系又是所有人能够理解到的,写到这一步,余华才满意。而这一步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让“比喻”超脱自己的经验,进入写作对象的经验领域。
以上我们都是在讲对一个地点的再现,但在再现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接着思考我们应如何看待它。人类学的写作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有所不同,人类学格外注重将事物放置到一个比较的框架中去考量,并由此来分析事物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中所处的位置。这么说有点抽象,但这件事其实可以通过一个又一个很具体的步骤展开。比如对一个地点来说,我们一定对它有一个固有的印象,那么我们能立马做的一个比较就是,将我们的固有印象与我们的实际考察作比较,看看其中的出入,并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纳拉扬在书中说,你甚至可以尝试列出那些在大众想象中与你计划写的地点相关的图像,譬如人的类别、物体的种类、活动、颜色、气味等,然后逐一作比较。
纳拉扬说她16岁第一次从印度到美国的时候,每当她告诉人们她在哪里长大的时候,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其实正来源于他们对印度的固有印象。人类学家米尔顿·辛格曾总结西方人心中纷繁复杂的印度形象,他写道:“有由印度王宫那富丽堂皇的,由黄金、锦缎和香料构成的印度;有被贫困、疾病、种姓压迫、女性受压迫等问题缠身的印度;还有由古代文献、非暴力抵抗、大师、冥想、瑜伽等组成的灵性的印度。”所有这些都是印度,但又都不完全是印度,这也正说明比较的重要性,我们或许能在比较的出入之中看见一个更真实的印度。
除了印象在变化,地点本身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尝试比较不同时段下该地点的景观和人类活动,这一点也很有必要。比如在《萨哈林旅行记》中,契诃夫在写到杜伊卡河谷的时候,他就将他的观察与一位动物学家在9年前对该地点的观察做了一番比较。动物学家当时记录了该地有巨大、古老的森林环抱着河流,还有湿软的沼泽,而9年后,契诃夫看到的则是干涸的河床,四周的土地被填平成了定居点,并且还在持续扩张。契诃夫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架起桥梁,然后他进一步思考这种景观变化背后的权力关系,是谁给此地带来了这样的变化,谁在当中受益,谁又在当中受到剥削。他在书中写道:“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付出了多少劳动,进行了怎样的斗争啊!在水深没腰的烂泥潭里干活,还有严寒、冷雨、怀念故里、屈辱、笞刑。想到这些,我们的头脑里就会浮现那些可怕的身影。”
另外,纳拉扬在书中还格外提到,我们应时刻挑战自己的视野,这种挑战包括引入他者的看法,尤其是来自当地人的看法,尝试站在当地人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纳拉扬说你可以通过描述当地人在四季中最期待的是什么来刻画一个地点,在他们的期待中展示他们如何看待当地的景观地貌和社会实践。再有,我们还可以挑战的是,在刻画典型的、常规的事物之余,有意地去关注当地隐秘的、边缘的、非典型的事物,尤其我们不应该忽视一个地方的痛苦和灾难,因为常常是在一些灾难性事件中,我们会更清楚地看见当地社会的运转。
总的来说,与固有印象的比较、引入他者的看法其实都是试图提升写作的客观性,让写作不至于脱离当地的真实情况,而关注一个地点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关注人类活动在这种变化下的影响,并追溯这种变化的来由,还有关注一个地点隐秘、边缘、灾难性的角落,并分析这背后的社会运转,这体现的是一种道德性。如果“道德性”这个词过于抽象的话,我们可以换成契诃夫的一个说法,那就是“富有同情心”,对当地的自然和人的处境富有同情心,不遗余力地探索影响当地自然和人的处境的力量,思考这到底是一种好的力量,还是一种坏的力量。所以,保证客观性,秉持道德性,这可以说是纳拉扬在这本书中提示的关于写好一个地点的核心。
说完地点,我们再来讲讲人物,怎样写好一个人呢?我们从哪些角度入手来观察和理解一个人呢?
首先,像写作一个地点时一样,我们应该先把那些我们能看见的一个人的外在特征写下来。纳拉扬在书中参考了作家保罗·奥斯特的人物描写,给出了一份“保罗·奥斯特清单”,我们可以以此为线索观察一个人,它包括:这个人引人注目的身体细节,古怪的习惯,独特的食物或者饮料,与其相关的物品,他的一个日常活动,此人的动态的样子,他与其他人的相似之处,他在互动中展现出的特质,他的一项爱好或者乐趣。
在收集到这些特征后,纳拉扬提示我们可以从“类型”和“个体”两个方面来把握一个人。所谓“类型”,其实就是我们要写的这个人可以被归入怎样的人群类别,比如以契诃夫为例,他是19世纪伟大的俄国作家之一,他只活过了20世纪的头几年,在1904年去世。用来定位一个人的类别有很多,而且它会随着视角和此人的生活轨迹而改变,比如契诃夫曾经是学生群体的一员,后来是医生、作家、剧作家群体中的一员,此外你还可以根据他的出身、阶层背景,或是长期居住的地方来定位他。
当你确定下来一个类别的时候,你要尝试通过物品、外貌、着装、习惯、互动等方式,来具体地将这个人表现为某个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比如契诃夫的朋友康斯汀·柯罗文留下了这样一段描写契诃夫的文字,他写道:“(他的)长沙发上堆满了纸张和大学笔记本——他正在为他在医学院的期末考试做准备。他坐在长沙发的边缘,穿着一件当时许多学生穿的那种灰色夹克,房间里还有其他一些年轻人,都是学生。学生们在谈话,热烈争论,喝着茶和啤酒,吃着香肠。而他静静坐着,只是偶尔回答问他的问题。”这段描写将契诃夫安置在一个房间里,通过他的论文、笔记本、灰色夹克、同伴、饮食习惯,将他描述为一群学生中的一员。
此外,纳拉扬提醒我们要尤其关注一个人的长期特征,比如某种身体的印记、习惯性的姿势、癖好等,因为这部分往往会暗含一个人最根深蒂固的群体信息。比如纳拉扬在书中引用了人类学家西敏司在其著作《甘蔗工人》中的一段人物描写,他写道:“他的手看起来几乎是怪诞的,因为他是一个骨架很小的人,手看起来却属于一个体重和体型有他两倍的人。他的脸上满是皱纹,后来发现他实际有多年轻时,我为他年龄和外表之间的差距感到震惊。他的牙齿一颗不剩了,口中是一副镶嵌黄金的假牙。”西敏司这里留意的便是劳动在人身体上留下的痕迹,一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由此呼之欲出。
但“类型”充其量给出了一个人的轮廓,我们还需要在“类型”的基础上去探索一个人“个体”的一面,也就是他身上独特于其他人的部分。纳拉扬在这里提到一个“创造性参与”的概念,也就是一个人带着自己独有的想象、期待和理解来认知和做事的时刻,它是我们通往一个人内心的入口。具体来讲,你可以关注一个人如何描述那些对他至关重要的物品,纳拉扬在书中引用了一段描写裁缝的文字,裁缝说道:“你的手指中间捏着一根线,它到达衣服,到达手指,到达穿这件衣服的人的身上,所有这些可都是相互联结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你所做的是否能赚到钱。”这段文字中写到的针和线,揭示的就不仅是这个人的职业特征了,它还揭示的是一个人独特的认知和价值观。
再有,你还可以去比较一个人独处的时刻和他与他人互动的时刻,在这种对比中去捕捉一个人独特的内心。纳拉扬讲到作家亚历山大·库普林对契诃夫的描述,他讲到,早晨到午饭前是契诃夫写作的时段,你有时能看见他坐在房子后面的一张长椅上,那里是别墅里最幽静的地方,他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独自一人,也不动弹,只把双手放在膝上,看着前方的大海”,而到了下午,各种各样的客人来到他家,有的是来请他指教的,有的是来采访的,有的是纯粹出于好奇的看客,还有一些真真假假的来要饭的人,契诃夫几乎欢迎所有的人,他的慷慨远超过他微薄收入所能允许的程度。纳拉扬说库普林的这段描写打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给出了契诃夫在独处和互动时刻的极端对比,这个人可以完全封闭自己,但同时他又可以完全是合群的,由此你会不由得想这一动一静之下,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他究竟是何感受?在写作中,如果你再进一步,你或许就能以此归纳出这个人的一个核心主题,对契诃夫来说,内心生活和外在生活的冲撞或许就是他最大的主题,他的小说其实也都有关于此,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曾说:“在契诃夫的世界里,我们的内在生活有其自己的速度……自由的内在生活撞上了外在生活,就像两套不同计时系统的冲撞。”
但人是太过复杂的物种,我们虽然可以从“类型”和“个体”两个维度对其做出一定的概括,但我们不能就此觉得我们就彻底了解一个人了,更好的写作者会追求在作品中保留人的复杂性。纳拉扬对此也提供了一个方法,她说你可以去回想这个人留在你脑海里最念念不忘的那个瞬间,而且最好在这个瞬间中,存在你无法理解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仍以对契诃夫的描写为例,丹钦科是俄国戏剧家,契诃夫曾就《海鸥》的剧本征求丹钦科的意见,丹钦科后来回忆这件事时写道:“我无法解释,当我久久地详细分析剧本的时候,为什么他的身影如此深深地印入我的脑际。我坐在书桌旁,面前放着手稿,他站在窗口,背朝着我,像平常一样把手插在口袋里,至少有半小时没转过身来,也没说一句话……他是为了让我轻松一点,随便地发表意见,不让我因目光相遇而感到不好意思,或者相反,他是为了保持个人的自尊心?”纳拉扬说,这段描写之所以令她难以忘怀,就在于它的开放性,丹钦科没有假装知道契诃夫脑子里在想什么,也没有试图解释记忆中的一幕,而是问出了一个问题,让它揭示一系列复杂的原因,这实际比一份有条不紊给出最终结果的概要更能传达关于这个人物的信息。
好,人物我们说到这里。最后,我们来讲一讲自我。写作不可能绕开自我,我们写下的每一个字,描绘的每一个地点和每一个人物,实际上都暗含着我们的自我。在好的写作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清晰独特的自我,甚至我们能听见属于作者的声音。可自我,相对地点和人物而言,是一个更抽象的概念了,如何认知和书写自我,如何处理自我和写作的关系,纳拉扬在书中给出了一套来自人类学的方法。
在文学写作中,我们的自我常常是隐身的,它藏在角色的身后,但在人类学中,写作者的身份、目的、立场是必须处理的一个命题。很多人类学著作的第一章,往往是向写作对象解释作者的目的,回答“我到底在做什么”。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写作都需要做这件事,但我们可以借助这件事来想清楚我们与我们写作材料之间的关系,并训练如何在写作中明确自我,以及调用自我。
纳拉扬说你可以尝试把自己当成一个角色,去设想一个场景,当有人问起你,“你现在是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你会如何回答。她以民族志学者、小说家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作品做示范,在赫斯顿的作品《骡子与男人》中,她描述自己回到家乡的那一刻,当地的一群男人看见她,立马问起她这次回来要待多久等问题。赫斯顿写下了一系列非常日常的对话,其中有三句是这样的,一句是“我是来收集一些古老的故事啊、传说啊之类的,我清楚你们都知道不少,这就是我为什么回家来”,一句是“很多人想看,它们比你想的更有价值,我们想在时间还不算太迟之前把这事搞定”,还有一句是“什么叫不算太迟,就是在所有人把它们全都给忘了之前”,这三句话其实就揭示了赫斯顿此行的目的,也向读者预告了她接下来要写的内容,以及它也包含赫斯顿内心的一个自我论证的过程,如果回到这本书的序言,赫斯顿有进一步解释自己为什么在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改变后要回到家乡,以及为何要回归那些民间传说和民俗材料,这一系列自我论证对于明确自我,以及明确所做之事和所写之物的价值,有极大意义。
再有,我们可以像观察一个角色一样,去观察我们与人和事物的互动,去捕捉一个使我们产生强烈反应的互动时刻,并尝试挖掘我们做出这种反应背后的深层原因,尤其我们要关注我们生命的转折点,或者说我们生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想一想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有哪些社会力量在其中发挥作用。
纳拉扬在书中提到民族志学者、历史学家,同时还是小说家的阿米塔夫·高希,他来自印度,在牛津大学学习人类学,写了一本关于埃及之旅的著作,其中他讲到他在埃及参加的一场婚礼,婚礼上所有的中年男人都对高希表现出好奇与惊讶,问他有关印度文化和习俗的各种问题,但高希没法回答,他说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逃走了。事后他分析他这本能的反应,他在书中讲到他出生在东巴基斯坦,这是一个1947年成立、仅存在了二十五年的国家,之后他又随父亲去孟加拉国执行印度外交任务,所以他生活在各种各样地域与教派的纷争之中,埃及人问出来的那些关于文化习俗的问题,在他的脑海里是一场一场纷争的由头,他没有结论,并本能地感到恐惧。当我们一步一步追问我们那些本能反应的缘由,以及回溯什么让我们的生活发生转折,我们会发现我们始终受到历史、社会、文化等的约束,直面这种约束,其实也就是直面我们自身。
但写作不仅仅关于直面自我,也关于联结不同的自我。所以纳拉扬在书的最后提醒我们关注联结的时刻,尝试去捕捉那些打开自我、令人产生联结感的互动。她又讲到自己阅读契诃夫的体验,契诃夫有篇小说叫《大学生》,契诃夫曾说这是他众多短篇小说中自己最喜欢的一篇,讲述的是一名神学院学生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感到一切都很荒凉,他人也很抑郁,觉得人的苦难是无穷无尽的。半路大学生遇见两个农妇在生火,他走过去暖手,和她们攀谈起来。他讲起耶稣和彼得的故事,耶稣告诉彼得公鸡啼叫之前要三次否认认识他。黎明时分,耶稣受审,彼得醒来被指控他与耶稣是一伙的,彼得像耶稣所说,三次否认认识他,明白过来的彼得走出院子,痛哭不止。大学生讲到这儿的时候,她突然发现一旁的农妇掉下了眼泪,离别的时候大学生回望那团火光,突然觉得妇女们如此感动的话,那这个他所讲述的上千年前的故事和今天就还有关系,和一切人都还有关系,他觉得心头的无意义感和压迫感少了一点,因为真理和美过去在指导人们的生活,至今也一直不断地指导我们生活,这就是我们会感动的原因。
耶稣和彼得的故事感动了大学生,大学生对这个故事的复述又感动了妇女,契诃夫对这个故事的写作进一步感动到了今天这本书的作者纳拉扬,而后纳拉扬在自己书的最后重新述说这个故事,希望能够感动更多的人。纳拉扬写道:“我不也是抓住了人类传播的长链的一段,跨越时空和语言,走向其他的许多个自我。”也许写作的力量,就在于这样一种直面自我,并试图联结更多自我的时刻。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作者基伦·纳拉扬以一系列文学和人类学著作,尤其是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作为范本,给出了一套具体实用的写作方法,同时也是观察和认知事物的方法。她讲到从“客观性”和“道德性”两个维度来把握对地点的认知和写作,从“个体”和“类别”两个维度来把握对人物的认知和写作,纳拉扬始终在强调的是,我们要在比较中去认识个体故事与社会进程之间复杂的纠缠,在理解这些纠缠的过程中,来理解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和我们的自我。显然,这件事不容易,它需要我们长期练习和实践,甚至将它贯穿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示:生活在写作之中。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对这本书的内容感兴趣的话,非常推荐你阅读原书。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人类学的写作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有所不同,人类学格外注重将事物放置到一个比较的框架中去考量,并由此来分析事物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中所处的位置。
2.我们虽然可以从“类型”和“个体”两个维度对其做出一定的概括,但我们不能就此觉得我们就彻底了解一个人了,更好的写作者会追求在作品中保留人的复杂性。
3.当我们一步一步追问我们那些本能反应的缘由,以及回溯什么让我们的生活发生转折,我们会发现我们始终受到历史、社会、文化等的约束,直面这种约束,其实也就是直面我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