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想的悖论》 杨以赛解读
《妄想的悖论》| 杨以赛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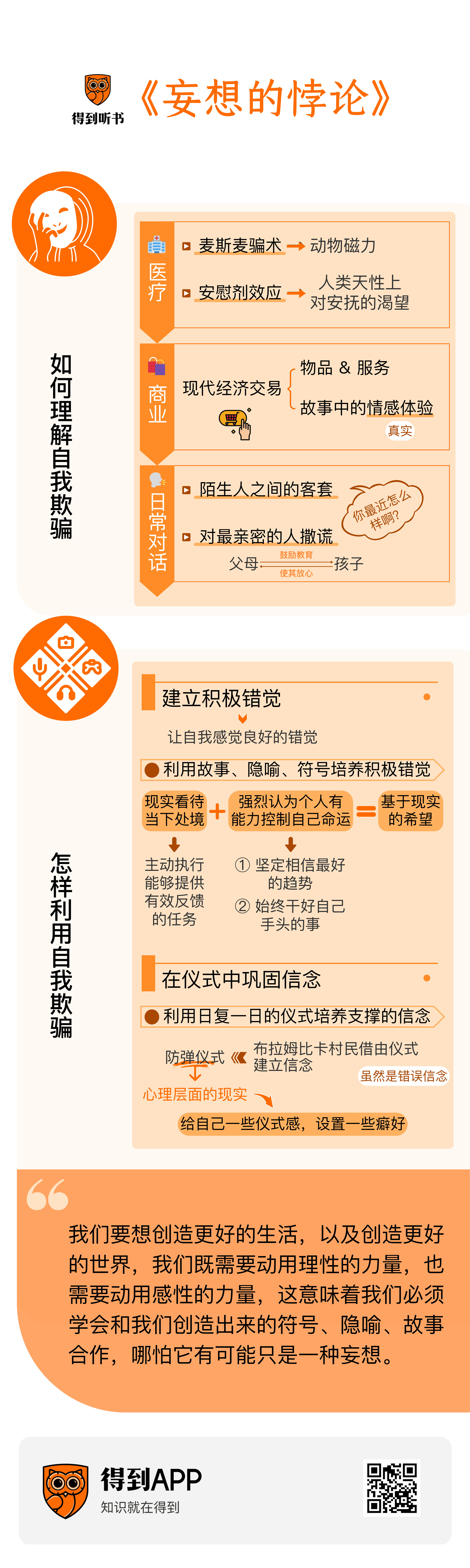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妄想的悖论》,副标题是“人性中自我欺骗的力量”。有很多书在教我们看清现实,认识自己,比如“得到听书”此前就解读过不少类似的书,它告诉我们要如何绕开大脑的陷阱、营销的陷阱、技术的陷阱等,看到事实真相。但今天这本书有点不一样,它试图告诉我们的是,自我欺骗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可以对此加以利用。
这本书的作者是尚卡尔·韦丹塔姆和比尔·梅斯勒,韦丹塔姆是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曾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兼职讲师,梅斯勒则是一位记者,长期为《科学美国人》等科普报刊供稿。他们的上一本书《隐藏的大脑》,“得到听书”解读过,在那本书中,他们仍在教我们如何辨别和避免大脑对自我的欺骗,但到这本书,他们的态度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在给《隐藏的大脑》这本书搜集材料的时候,两位作者去采访了一位叫做唐纳德·劳里的诈骗犯。简单来说,这位唐纳德·劳里假装成女性,给成千上万的美国男人写信,其中不少男人上钩了,他们坚信劳里是自己的灵魂伴侣,给他寄去几百万美元。但这起案子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当劳里接受审判的时候,那些受害者并没有控诉他,相反他们认为劳里把他们从孤独中解救了出来,因此纷纷来为他辩护,甚至指责检方拆穿骗局,毁了他们的生活。韦丹塔姆和梅斯勒起初认为这群受害者简直是执迷不悟、愚昧至极,但真正接触之后,发现他们在这个骗局中真的获得了很真挚的抚慰。因此,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再很强硬地跟这群人说,这都是假的,你们不要再自我欺骗了。
这就引出来所谓“妄想的悖论”,站在理性层面,欺骗和自我欺骗当然是不好的,但在一些时候,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要借助这种欺骗和自我欺骗,才能面对我们的生活。两位作者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采访和研究,他们梳理了来自心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众多研究成果,最终发现,自我欺骗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普遍,而且它可能确实是有效用的,它在我们追求成功和幸福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将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看“自我欺骗”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人们有时候会需要这种“自我欺骗”,“自我欺骗”是错误的吗,到底该如何理解“自我欺骗”?第二部分,我们来看,如果真如作者所说,“自我欺骗”也是一种力量的话,那我们要如何来利用这个力量呢?
我们进入第一部分,先来讲一个故事。1784年,有几位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聚集在巴黎,研究一个水桶。这个水桶号称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医疗装置,可以治愈很多疾病,甚至能使盲人重获光明。水桶的发明者叫弗朗兹·安东麦斯麦,奥地利人,毕业于著名的维也纳大学。他宣称他发现了一种叫做动物磁力的能量,通过这种能量能疗愈“癫痫、忧郁症、躁狂发作和疟疾”等疾病,他的水桶正运用了这种能量。安东麦斯麦后来开了24家磁力诊所,轰动一时,奥地利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美国独立战争英雄拉法耶特侯爵等都是他的常客。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疗法。当时的法国国王任命了法国最伟大的几位科学家来调查此事,其中包括被称为现代化学之父、命名了氧气和氢气的安托万·拉瓦锡,还有当时正在法国做大使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们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检验动物磁力是否真的存在,以及它是否真的能对人体施加影响,最终的结论是,这种力根本不存在,安东麦斯麦的水桶不过是一堆破铜烂铁,而其本人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委员们虽指出了这是一个骗局,但他们却并未明确制止患者们继续尝试这一疗法,富兰克林甚至在一封给患者的回信中写道:“这种治疗方法利用了人们的妄想和自我欺骗的天性,但即便如此,这种疗法或许仍值得一试,在每个城市都有一群病秧子,他们太热衷于药物,长期大剂量服用,最终损坏了自己原本健康的体格,如果这时有人告诉他们不必依赖药物,医生只要将手指或是一根铁棒指向他们,他们就能痊愈,说不定反倒会有不错的结果。”
在安东麦斯麦骗术被揭开的几百年后,医疗上对这种“骗术”有了更多研究,一个叫做“安慰剂效应”的词被提了出来。“安慰剂”的拉丁语原义是“为了取悦”,它是一种“为了取悦患者而不是为了改善患者状况的药物”。不少临床试验中都曾出现过“安慰剂效应”,也就是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病情竟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哈佛大学安慰剂研究与互助治疗项目负责人特德·卡普特丘克说,“安慰剂效应”的存在提示我们,当你拿到一张处方单时,帮助治愈你的不仅仅是那上面开的药,还有其他很多要素,包括你去看医生这件事本身、去进行预约这一行为、候诊室里的氛围、医生听你描述时的专注神情,以及诊所所有工作人员为舒缓你的紧张情绪而提供的各种帮助等等。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医院有些时候就像是一座剧院,医生和患者在特定的情境下,合力演了一出戏,当中会有真实的成分,但也不可避免会有一些欺骗和自我欺骗的成分,这两者都会对最终的治疗产生作用。
韦丹塔姆和梅斯勒在书中分析说,“安慰剂效应”其实揭示的是人类天性上对安抚的渴望。早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动物们就已经体验过受伤和病痛的滋味了,在那个没有CT扫描仪和X光机器的年代,动物们寻求不到治疗,它们唯一能寻求到的是来自同伴的爱和关怀,并试图借助这种爱和关怀,来增加生存的概率,久而久之这成了我们天性的一部分。于是,即便现在我们拥有了医院和药物,这种天性依然存在,我们想从医生那里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份确切的诊断,我们还希望获得抚慰,哪怕这种抚慰可能来自妄想和欺骗。
其实,“安慰剂效应”背后的心理机制不仅存在于医学世界,它还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说医学世界有时候像一个剧院,那商业世界又何尝不是呢?它是一个更加“明目张胆”的剧院。
韦丹塔姆和梅勒斯在书中提到一档美国的电视节目,叫做《胡说》,里面分析了各种假象和欺诈行为。在2003年的一期中,节目主持人佩恩和特勒去到加利佛尼亚的一家餐厅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假扮成侍水师,为餐厅的客人推销饮用水。他们准备了三款饮用水,一款是具备法式风尚的法国水,一款是经由热带雨林自然过滤系统过滤的亚马孙水,还有一款是被称为天然利尿剂和抗毒素的富士山水。实际上,这三款水都是从花园水管里接的自来水,但加上这些天花乱坠的介绍后,客人们竟然真的愿意花高价购买这三款水,甚至还赞不绝口。这个实验很直观地揭示了,现代经济中的交易,不只是在交易物品和服务,它也是在交易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我们有时候会为了一个好故事,忍不住花远超实际价值的钱购买一件商品。这听起来很不值得,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上当受骗,但韦丹塔姆和梅勒斯在这本书中指出一点,他们说,我们可能购买了一个虚假的故事,但我们在这个虚假故事中获得的情感体验,却有可能是真实的。
他们在书中讲到美国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兰赫尔做过的一个实验,兰赫尔邀请了一群人来参加一场红酒品鉴会。他在现场摆了从5美元到90美元不等的红酒,但所有人不知道的是,兰赫尔调换了10美元红酒和90美元红酒的酒瓶。品鉴会最后,兰赫尔邀请现场所有人对不同酒瓶里的酒进行评价,所有人都称赞了那瓶标价为90美元,但实际只值10美元的红酒。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真正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兰赫尔召集研究人员对这群品酒者进行了脑成像扫描,他发现,当这群人喝从90美元红酒瓶里倒出来的10美元酒时,他们大脑中内侧眶额皮层的亮度要比他们在喝10美元红酒瓶中的酒要高,内侧眶额皮层是大脑中感受快乐的一个区域,这也就是说,这群人真的觉得这个更贵酒瓶里的酒,味道更好,并且他们真的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快感。那这就带来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这些人花了更多的钱,买了一个完全不值那么多钱的东西,但他们因此感受到了更多的快乐,那他们到底是被骗了,还是让钱花得物有所值了呢?
其实,除了买东西,哪怕是一次简单的日常对话,我们也可能面临这一问题。比如当对方说了一句谎话,但这句谎话真的让我很开心,那我到底是要相信还是不相信呢?美国社会学家哈维·萨克斯早在1975年就发表了一篇名为《每个人都必须撒谎》的论文,其中他采用语义分析的方法,详细列举了日常生活中大量的谎言,比如最基本的一句问候语“你最近怎么样啊”,恰恰可能是最客套的,问的人并不想知道,回答的人也并不用如实回答。后来心理学家罗伯特·菲尔德曼甚至尝试统计了陌生人在第一次见面时的说谎次数,他的研究结果显示,被试者在对话中大约每十分钟会说三次谎,其中有些人的说谎次数高达十二次。此外,我们还尤其擅长对我们最亲密的人说谎,比如父母常常会用谎言来鼓励和教育孩子,而孩子有时会用谎言来使父母放心。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乔治·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华盛顿砍倒了父亲最喜欢的樱桃树,父亲回家后勃然大怒,问是谁干的,华盛顿立马承认了错误,父亲非但没有责罚他,反而因为他的诚实奖励了他,我们经常会用这个故事来教导孩子诚实。但吊诡的是,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个谎言,它是1800年一个叫做梅森·威姆斯的牧师编出来的,他不过是想利用当时大众对华盛顿的狂热崇拜来捞一笔钱。那为什么这个捏造的故事会被代代相传呢?因为它作为一个故事,虽然内容是假的,但确实能带来教育的作用,小孩子们真的能在这个故事里认识和学习到诚实这项品质。
好,说了那么多,从医学说到商业,再说到普通的日常生活,韦丹塔姆和梅斯勒最终想向我们传达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欺骗和自我欺骗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普遍,而且在一些时候,它确实是有所效用的。我们能够在这种欺骗和自我欺骗中获得真实的安慰、关怀、快乐、满足、目标、价值、意义等等。所谓“妄想的悖论”,说的其实是,在理性上,我们都知道那种自我欺骗式的妄想是不好的,这不是现代社会所提倡的,但感性上,我们又确实需要一些这样的妄想。韦丹塔姆和梅斯勒在书中说,在今天,那种不去自我欺骗的能力,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特权。一个人要是说他从来没有自我欺骗过,往往因为他们一直都身体健康,事业有成,生活殷实,他们没有理由不快乐、不积极向上。生活给了他们优待,以至于他们不用像大部分人一样会需要在妄想中寻找喘息的机会。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谈论和提倡理性,这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所在,但韦丹塔姆和梅斯勒在这本书中指出,感性层面的直觉、本能、情感与信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套讲述和编造故事的能力,对于人类同样重要。他们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试想如果你要设计一个机器人,并把它送到一个遥远的星球,之后都不会有它们的音讯,你要怎样确保它们能在那个无法预料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且不断繁衍呢?你需要给这些机器人输入一系列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让它们知道怎么制造工具、寻找食物、繁衍后代等。但与此同时,你会希望它能提前感知到危险,所以你需要给它灌输恐惧,你还需要确保它能够为了自己的后代不顾一切,所以你需要给它植入情感。此外,你还需要它不会遇到困难就放弃,你想要它即便知道自己终将被毁灭,也仍然拼尽全力地挣扎,并试图存活,那这时候单靠理性分析和准确的感知就不够了,你需要给它们一些不切实际的追求与信念。所以最后,你不得不为它们创造妄想和自我欺骗的机制。反观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其实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说理性彰显的是人类的强大,那么妄想其实反倒折射出人类的脆弱与渺小,它们都构成了一种力量,支撑了我们的生存。
当然,韦丹塔姆和梅斯勒也在书中强调,他们论述那么多,并不是要为招摇撞骗和谎言开脱,他们只是想提醒我们不应该总是执着于分出真相和假象。因为真相不一定就导向好处,而假象也不一定就导向坏处,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真相和假象的原因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它的好处是否大于坏处,以及它是否能对我们构成帮助。韦丹塔姆和梅斯勒说,与其彻底铲除自我欺骗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我们不如想想怎样能让它为我所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讲讲我们可以怎样利用“自我欺骗”,我将此总结为了两点,一是尝试建立积极错觉,二是尝试在仪式中巩固我们的信念。我们逐一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建立积极错觉。我们从一个实验讲起,心理学家劳伦·阿洛伊和琳恩·阿布拉姆森做过实验,他们召集了一批抑郁症患者,试图验证抑郁症患者是否真的与现实脱节,健康的人是否真的比抑郁症患者更能够看清现实。实验是这样的,他们邀请抑郁症患者和非抑郁症患者按下一个按钮,这个按钮设置在闪烁的绿灯旁。这个实验是想让这两群人判断,按下这个按钮,会对绿灯的闪烁状况造成多大的影响。实际上,按钮对小灯闪烁状况毫无影响,但实验中只有抑郁症患会承认这一点,而非抑郁症患者则往往高估自己控制小灯闪烁的能力,坚持认为按按钮是有作用的。这也就是说,和我们预想的不同,抑郁症患者可能反倒比非抑郁症患者更能看清现实。而且后续研究还表明,经过治疗的抑郁症患者,随着不断好转,他们变得更有可能自我欺骗,出现控制和自信妄想。在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心理健康和现实的关系,他们逐渐承认,一定程度的自我欺骗不仅没有坏处,反而会带来积极影响。健康的人不是那些更清楚看待现实的人,而是那些以更积极的方式看待现实的人。其中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谢利·泰勒提出的“积极错觉”理论作为代表,所谓“积极错觉”其实就是一种让自我感觉良好的错觉。
韦丹塔姆和梅斯勒在书中坦言,起初看到“积极错觉”这一理论,他们是怀疑的。因为生活中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错觉会让我们陷入麻烦,而且那种因为拒绝面对现实而最终走向毁灭的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但随着了解的深入,韦丹塔姆和梅斯勒在各个不同领域都看到了支撑“积极错觉”的例子。
比如有研究人员研究了妄想和自我欺骗在创业中的作用,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的两万多个创业项目,他们发现,男性在创业的时候,募资的数额会比女性要的更多。换句话说,男性在募资的时候会比女性更有自信,认为自己可以筹到更多的钱。那他们募资的结果又是如何呢?女性的资金规模更合乎实际,因此她们会比男性更容易筹到资金,而且因为第一次的成功,她们在第二次或第三次筹资时,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也比男性高。但当研究人员去考察整体情况的时候,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他们发现,在他们所调查的筹资平台上,筹资成功的男性总人数比女性总人数要多。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有很多,像是性别歧视,但研究人员尤为注意到一点,男性是如此自负地沉浸在自我的妄想中,以至于他们不在乎失败,他们会不断地发起新项目,并且筹资目标依然定得很高,其中总有一些最终获得了成功,这帮助他们在总数上占了优势。这也就是说,“积极错觉”确实在一些时候会带来麻烦,但它也确实有所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会在长期的过程显现出来。
还有一项研究显示,“积极错觉”对女性也是有帮助的。1983年,美国心理学家谢利·泰勒对一批患有癌症的女性展开过研究。她发现,有更大程度积极错觉的女性会更容易改善病情。这个改善,针对的不是癌症本身,而是伴随癌症而来的诸如抑郁、感觉自己没价值、失眠、物质滥用和自杀冲动等各种心理问题,“积极错觉”会降低出现这一类问题的可能性,从而在整体上改善病情。
那既然积极错觉确实有所作用,我们要怎样建立积极错觉呢?以及我们要怎样保证它是适度的,不至于盲目,以至于招致不好的后果呢?在一本叫做《幸存心理学》的书中,作者费尔德曼和克拉韦茨也谈到了积极错觉,他们提出了一个等式:现实看待当下处境+强烈认为个人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命运=基于现实的希望,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等式来培养适当的积极错觉。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能够现实地看待当下处境,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主动去执行一些能够提供有效反馈的任务,由此来确保我们不会太过于脱离现实。然后我们需要建立我们有能力控制命运的信念,这一点存在个体差异,有些人天生会比另一些人更自信、更乐观,有更多的积极错觉,但不用担心,这是后天可以训练和弥补的。比如在第25期罗辑思维·启发俱乐部中,罗振宇就谈到了他是如何训练自身的信念感的。他提到两点,一是在各种未来的可能性中,坚定相信那个最好的趋势。二是别管它,始终干好自己手头的事。他以癌症举例,尽管病情恶劣且复杂,但仍要坚定相信有治好的可能。与此同时配合医生,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而在这本《妄想的悖论》中,韦丹塔姆和梅勒斯则提到说我们可以利用故事、隐喻、符号来培养积极错觉,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尝试利用仪式来培育和巩固自身的信念。
在刚果,有一个叫做布拉姆比卡的村子,村子所在区域流血冲突事件频发,联合国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曾称布拉姆比卡村附近区域的性暴力事件是“全球最恶劣的”。2012年,在邻村发生屠杀事件后,布拉姆比卡的一位老人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自己的祖先,祖先告诉他去远处的一个森林里,挖到特别的植物根茎,然后加上动物肠子,调和在一起做成粉末,再施加一些咒语,就可以帮助他们防御子弹了。2015年,经济学家纳恩和德拉谢拉前往布拉姆比卡村,想要了解他们的防弹仪式。任何理性的人,应该都不会相信这个仪式,但令人惊讶的是,在施行仪式的两年时间里,村民们还真就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没有遭受任何袭击。纳恩和德拉谢拉了解到,防弹仪式让年轻人大受鼓舞,在遇到攻击时不再逃跑,而是勇敢迎战。与此同时,防弹仪式震慑了攻击者,因为四处都在传言村民们誓死抵抗,他们慌张之下就撤退了。从科学角度看,布拉姆比卡的村民们借由仪式建立的信念,显然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的信念却让村子里的人都活了下来。
“防弹仪式”当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但它和世界上各类仪式的机制是一样的。韦丹塔姆和梅斯勒说,仪式的意义不在于他们是否真的生效了,它的作用体现在心理层面。而有些时候心理层面的现实,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现实,就像布拉姆比卡的村民最后果真击退了袭击者一样。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可以被构建成仪式,从而具备仪式的效用。比如每天早上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报纸,再比如在去做重要事项前洗澡,并且换上幸运衬衫。韦丹塔姆和梅斯勒在书中特别提到美国棒球运动员韦德·博格斯,他每天5:17开始击球练习,7:17做短距离冲刺,他在比赛前只吃鸡肉。博格斯被称为美国棒球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之一,与此同时,他也被称为最迷信的击球手之一。他的这些癖好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具备了仪式的意义。所以,我们不妨也给自己一些仪式感,设置一些癖好,我们不必瞧不起那些把幸运日期、幸运号码挂在嘴边的人。因为有时候,就算是一个数字背后的一点点信念,也可能支撑我们走到很远。
当然,还有必要一提的是,也并不是所有的欺骗和自我欺骗都能够被我们所利用。其中有一些是带有破坏性的欺骗,比如谣言、诈骗、阴谋论等,我们仍然需要学习抵制它们。但究竟要如何抵制呢?去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去搜集更多的资料和证据,这样就可以了吗?韦丹塔姆和梅斯勒在这本书中说,这些措施固然重要,但它的作用是有限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人们之所以会选择轻信和支持一些错误的信念,常常并不是因为他们愚昧无知,而是他们确实可能在这种信念当中获得了安慰,减轻了焦虑,振奋了精神,甚至是感受到了某种归属。所以更明智的做法是,尝试去了解自身,也了解别人,我们究竟在这种错误的信念中获得了什么,还有别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去获取这些东西吗?正如韦丹塔姆和梅斯勒在本书最后的“尾声”一章中所说的,所有的欺骗和妄想其实归根到底是一个问题:我们缺失了什么,以及我们怎样能够弥补这些缺失。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作者韦丹塔姆和梅斯勒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阐释了人类的自我欺骗。他们发现在医学、商业,还有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自我欺骗现象无处不在。现代社会不断强调厘清现实,认识真正的自己,但韦丹塔姆和梅斯勒却在这本书中指出,自我欺骗这种行为“与其说是人们心智或智力的映射,不如说是我们对环境做出的反应”。我们常常是在面对生活的艰难时,选择了自我欺骗,我们不得不借助自我欺骗来寻求抚慰与信念。在这个层面上,韦丹塔姆和梅斯勒认为自我欺骗在一些时候是支撑我们生存的力量。
认识到这一点后,韦丹塔姆和梅斯勒在书中强调说,我们与其总是放言要铲除自我欺骗,不如想想怎样能让它为我们所用。他们在书中梳理了一系列来自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在这里集中讲了两点,一是尝试建立“积极错觉”,用适当的错觉去支持我们的行动。二是尝试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仪式,用日复一日的仪式,培养可以永久支撑我们的信念。
这本书叫《妄想的悖论》,所谓“妄想的悖论”,其实提示的是人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拉扯。有太多的书会向我们强调理性和逻辑的重要性,但这本书中,作者将诉诸直觉、本能、感受、情绪的感性部分,拉回到了我们的眼前。他们指出,我们大脑中这两部分永远是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的。我们要想创造更好的生活,以及创造更好的世界,我们既需要动用理性的力量,也需要动用感性的力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和我们创造出来的符号、隐喻、故事合作,哪怕它有可能只是一种妄想。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所谓“妄想的悖论”,说的其实是,在理性上,我们都知道那种自我欺骗式的妄想是不好的,这不是现代社会所提倡的,但感性上,我们又确实需要一些这样的妄想。
-
我们要想创造更好的生活,以及创造更好的世界,我们既需要动用理性的力量,也需要动用感性的力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和我们创造出来的符号、隐喻、故事合作,哪怕它有可能只是一种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