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理学破案手册》 杨以赛解读
《毒理学破案手册》| 杨以赛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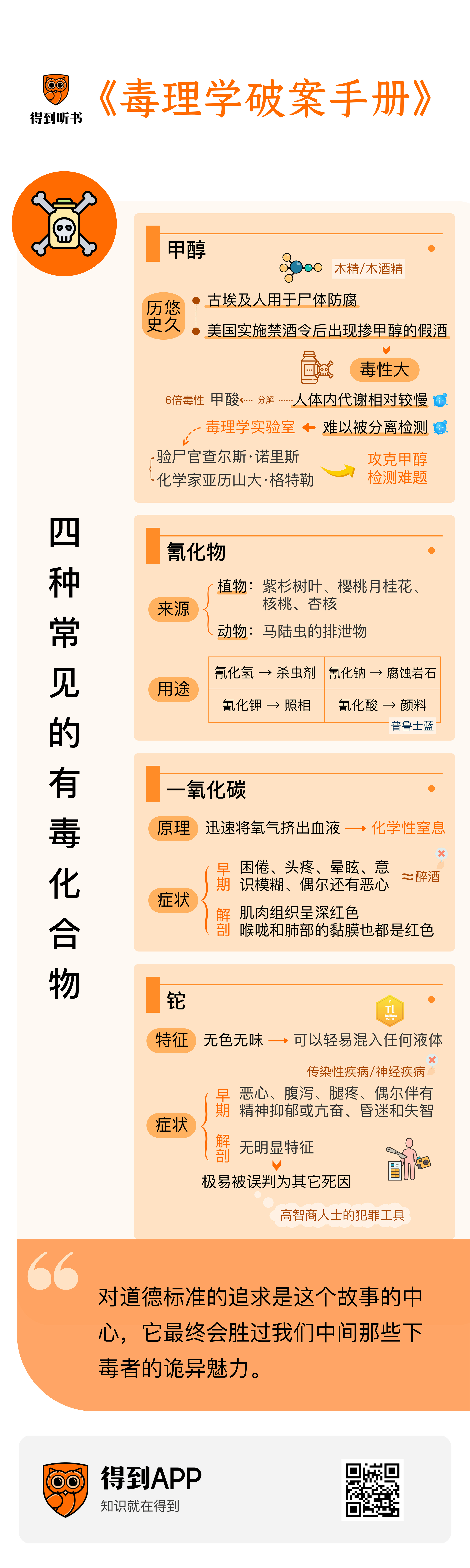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毒理学破案手册》。这是一本讲述毒药与谋杀,以及化学与刑侦的书。
毒药有很漫长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下毒。起初可能是一种意外和无知,但越往后,这当中就越充满了恶意。下毒者不像其他犯罪者,他们冷静、细致、无声无息,也因此他们更显可怕。正是这一事实催生了毒理学这门学科,简单讲这是一门与下毒者展开竞赛的学科。今天的这本《毒理学破案手册》,讲述的便是这场竞赛。
作者黛博拉·布鲁姆,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奈特科学新闻项目负责人,曾为《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卫报》等著名媒体撰稿,1992年她因一系列对灵长类动物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在这本书中,黛博拉介绍了11种具有代表性的毒物和相关案件的侦破过程,同时回顾了毒理学这门现代科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诞生过程。你可以将这本书视为一本科普读物,从中你可以了解到那些我们熟悉又陌生的有毒化合物。同时你也可以将它视为一本历史读物,跟随作者回到20世纪初期的纽约,在毒理学刚刚诞生之际,看那时候的人们是如何与毒物作斗争的,并从中窥视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如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毒理学副教授常秀丽在评价本书时所说:“毒理学的发展其实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从粗鲁到优雅,从迷信到科学,从取人性命到救死扶伤。”
这本书一共介绍了10种毒物,我从其中选择了四种,它们一方面在毒理学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它们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四种毒物分别是甲醇、氰化物、一氧化碳,以及铊。
我们先来认识甲醇。甲醇在工业上被称为木精或木酒精,人类使用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古埃及人在尸体防腐过程中就曾使用它。它的制作很简单,将木板和木片放入封闭容器,加热到200多摄氏度,木材变为木炭,其中所含的自然液体蒸发,再经冷却、浓缩、蒸馏后会化为一摊相当浑浊的水,其中会含有甲醇、丙酮和乙酸。再蒸馏一遍,就可以提取出纯粹的甲醇了,它是一种像玻璃般透明,无色无味,但却含有剧毒的液体,两汤匙就能杀死一个孩子。
在20世纪初的美国,美国政府出手禁酒,关闭了大量酒吧,此举使得那些爱酒如命的人秘密建造起大量蒸馏室,自制酒精,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假酒。所谓假酒,其实就是掺有甲醇的酒,提纯的甲醇和从谷物中提取出来的乙醇尝起来差不太多,但价格却便宜得多。当时在纽约,每三十多个死于中毒的人当中,就有六个是死于假酒的。
为什么同样是酒精,从木材中提取而来的甲醇毒性要比从谷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乙醇大那么多呢?这主要因为甲醇代谢相对较慢,而且它在人体内被分解后会形成甲酸,甲酸的致命性至少是甲醇的六倍。用书中作者的话来说,“饮用甲醇的人会泡在一种越来越致命的鸡尾酒里长达大半个星期”,在这个过程他会有剧烈的腹痛和呕吐,失明,昏迷,最后心力衰竭而死。
随着美国禁酒令一步一步成为现实,有毒的假酒也越来越泛滥,并且蔓延到全国,各地都在上报甲醇中毒案例。这一情况难以管控,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甲醇难以被分离检测,这让美国的相关部门无计可施。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一门叫做“毒理学”的学科诞生了。20世纪之前,检测尸体当中的毒物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所以调查者往往只能通过死者在死亡之前极度痛苦的状态推测毒物,或是通过将死者死前最后一餐喂给动物来立案,这让下毒杀人盛极一时,但“毒理学”的出现有效遏制了这一点,而这背后有两位关键人物,一位叫查尔斯·诺里斯,另一位叫亚历山大·格特勒。
查尔斯·诺里斯是纽约市的一名验尸官,在他的领导下,纽约市验尸官办公室成为为美国各地验尸办公室制定标准的部门。诺里斯毕业于耶鲁大学,之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1892年得到了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继续出国学习,专攻病理学。《时代》周刊曾形容诺里斯:“名声在外,爱讥讽人,留着山羊胡子,一心为公。”他曾严惩了他办公室的全部职员,就因为他们出具了一份报告,轻率地指出某人死于甲醇。诺里斯说,医生应该切除肝脏和大脑并保存好以供化验,其他证据比如装着有毒威士忌的瓶子也应该保留并加以分析,而且还要询问目击证人并记录其陈述,如果这些工作没有做到位,地区检察官就无法起诉含甲醇的酒类的供应商。在甲醇中毒人数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诺里斯聘请了一位异常勤奋又极具天分的化学家亚历山大·格特勒,诺里斯希望他能够从零开始设计一间专门的毒理学实验室,攻克甲醇难题。
这份工作对格特勒来说再完美不过了,他热衷于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而且狂热地相信化学的力量,他痛恨那种在化学分析中轻易放弃的行为,如果检测方法还不存在,那就发明一套检测方法。1918年至1919年期间,格特勒检查了七百多份人体组织中的酒精,评估了58种不同的在人体组织和酒品当中鉴别甲醇的方法。其中他发现最有效的一套方法是取一块五百克左右的组织,磨碎,加上一滴矿物油,再放入沸腾的水盆中加热,使其冒气,最后在其中加入酸和活性氧化物搅拌,这就能让甲醇冒着泡出来了。这样的一种方法,虽然复杂,但绝不会弄错。格特勒还想做到快速检测,他发现最好的方法是把一枚铜币加热到红透,再将它投到酒中,加热的金属会让甲醇与空气中的氧发生反应,释放出刺鼻的气味。这种方法精确度不高,但好在快速易推广。1919年12月,诺里斯和格特勒决定发起一项运动,向各地居民警示甲醇的危险。很难说他们这一行动对当时各地甲醇中毒情况,以及明显带来消极作用的美国政府禁酒令起到了多少作用,但至少一时间很多人都知道了有这么一间实验室,在做着检测毒物的事。
不过当时的纽约市市长仍觉得这间实验室没什么用,不断克扣预算。实验室里所有的新设备几乎都由诺里斯本人或员工买单。格特勒还要动用他本不丰厚的薪水去买实验用的额外的化学药品和生肝。诺里斯为此专门写信给纽约市政府,他说:“有罪或无辜完全要依赖于犯罪现场证据的化学和生物分析,市政府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个前提,那么法医办公室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
像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22年的一天,一位退休的毛毯商人和他的妻子被发现死在他们公寓浴室的地板上,警方无力破案,最后不得不求助于毒理学实验室。而这起案件也涉及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第二种毒物——氰化物。
1922年4月27日,75岁的杰克逊和他60岁的妻子被发现倒在浴室,他们穿着日常的衣服,牙关紧咬,嘴唇上沾满了干涸的血沫,整张脸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蓝色。负责此案的医生怀疑是双双自杀,可能吞服了某种快速起效的毒药。但警察在现场又未发现毒物。两人的家庭成员认为绝不可能是自杀,因为杰克逊夫妇是在独自生活多年后才遇见彼此,结婚不到一年,两人生活幸福而健康。
尸体被发现两周后,该案仍毫无进展,警方随后通知了诺里斯的部门,格特勒被委派对尸体和犯罪现场做更为详尽的化学分析。格特勒先是做了一系列酒精检测,排除了酒精中毒的可能。随后他切除了杰克逊夫妇的胃,对其做了检测,他的重点是查看其中是否存有氰化物。
氰化物也是一种有漫长历史的毒物了,它在我们周围大量地生长着,它藏在紫杉树叶中、樱桃月桂的花朵中、核桃和杏核中,以及一种叫做马陆虫的排泄物里。人类很早就认识到富氰化物植物的杀人潜力,埃及的象形文字曾提及“死于桃子”,有学者推测这背后可能就涉及氰化物。但氰化物被人们广泛认知到则得益于一位德国画家偶然的实验。
这位画家叫做海因里希·狄斯巴赫,他当时将一堆原材料在烧瓶里疯狂搅拌,期待能产生一种血红色,但事与愿违,烧瓶里出现的是一种紫蓝色,类似于傍晚时分的天空的颜色。狄斯巴赫将这种颜色称为柏林蓝,后来一位英国化学家又将其改名为普鲁士蓝。大概80年后,一位瑞典化学家将普鲁士蓝与酸溶液混合,产生出了一种无色气体,看不见,但有淡淡的苦杏仁味道,这种气体很容易浓缩成一种酸性液体,被广泛称为“普鲁士酸”,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氰化物。后来氰化物在工业产品中被大量运用,氰化氢被用于制造杀虫剂,氰化钠在采矿业中被用来腐蚀岩石以提取黄金,氰化钾被用于照相,总之它大量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但说到下毒,氰化物其实是大多数下毒者会避开的一种毒物,因为它留下的痕迹太过明显了。摄入这种毒药两到五分钟之内,人就会倒下,而且往往还会因为痛苦伴随着高声尖叫。由于氰化物会阻断体内的氧气传送,所以死者死后,皮肤会泛出蓝色斑点,另外嘴唇、口腔和食道的黏膜则会呈现深浅不一的红色。格特勒领导的毒理学实验室调查过发生在纽约市的79个氰化物致死案例,其中49例是自杀,用的都是氰化钾,因为氰化钾最为便宜。其余案例则多是意外死亡,比如氰化氢一般会用来给建筑物和船只消毒,偶尔会有工人被这种气体毒死。
说回到杰克逊夫妇一案,格特勒在杰克逊夫妇的胃组织和胃内容物上都做了普鲁士蓝检测,但令他失望的是他并没发现氰化物的痕迹。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警方传来消息,在杰克逊夫妇死亡的那天,他们公寓地下室门窗上都贴上了封条,这是进行蒸熏消毒的标准程序,所谓蒸熏消毒就是给室内注入含氰化氢的气体,由此来给室内消毒。格特勒做出推测,难道水管和蒸汽管道将地下室和杰克逊夫妇的房间连在了一起,气体沿着管道而上,进入到杰克逊夫妇的浴室,最终致使了他们死亡。有了这一推测后,格特勒立马又对杰克逊夫妇的肺部组织展开化学检测,杰克逊夫妇的肺部立马闪耀出普鲁士蓝怪异的夜空般的光芒。非但如此,格特勒还严谨地做了犯罪模拟,他将六只小白鼠放入杰克逊夫妇的浴室,随后在地下室释放氰化氢气体,不到三小时之后,所有的小白鼠都死了,这进一步证明了格特勒的推测。杰克逊夫妇一案就此宣告侦破。
但令人沮丧的是,检方随后对实施蒸熏消毒的经理和消毒工提起诉讼,但他们的律师却坚持宣称氰化物不可能在腐烂尸体中检查出来,就算检测出来了也有可能是尸体腐烂而产生的,所以格特勒的检测是有问题的。最终法庭对经理和消毒工做出了无罪判决。检察官在败诉后对格特勒解释说,毒理学这门学科实在太新了,相关研究还是太过匮乏,很难说服陪审团和公众,这是他们败诉的原因。
但不管怎样,这个案子初步建立了毒理学实验室的声誉,同时也刺激了格特勒和诺里斯,要更加努力。格特勒在杰克逊案后继续对氰化物展开研究,他用实验证明尸体中的氰化物在头四周内的含量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以及腐烂的尸体确实有可能产生微量氰化物,但很快就会分解掉,并不会干扰氰化物中毒案的判断。他还分析了一系列氰化物致死案例,发表了一篇名为《氰化物的毒理学》的论文,这篇论文不断被人参考引用,直到21世纪。而诺里斯则在杰克逊案的几个月后,发起了“改善法医学环境”的改革运动,他会见了来自各大城市的验尸官、病理学家、法医,向他们宣讲,他决意使这一职业得到它应得的信任和尊重。
但只有宣讲显然是不够的,还是得要发挥实际的作用,让人眼见为实。1926年,诺里斯和格特勒向被称之为“最可靠杀手”的一氧化碳发起了进攻。
一氧化碳在自然界中比较罕见,它紧随闪电、森林和草地大火,以及任何富含碳的燃料燃烧而形成,一旦在大气中出现,它很容易与其他氧原子结合,转化成二氧化碳而扩散。但这种气体却广泛存在于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它不断从火炉、烤箱、燃气热水器、火车烟囱、汽车排气管中飘出来。正因为它在生活中如此常见,所以利用一氧化碳杀人,并伪造成因家用设备故障而意外死亡的事故数不胜数。
在1920年代的纽约市,一个人只需要把家里用来照明的煤油灯的盖子揭开,就可以实施谋杀了。一个经典的案例是1923年冬天,一名纽约市失业画家给他二十八岁的妻子买了一份一千美元的人寿保险,随后他在她睡觉的时候用枕头闷死了她,紧接着他扭断了墙上本就破破烂烂的煤气灯,当听到煤气的咝咝声时,他离开房间,关紧了房门。第二天早上妻子被发现死亡,乍一看这就是一场意外事故,不会有任何人怀疑。好在有病理学家察觉到了异样,格特勒的实验室抽取了尸体体内的血样,检测之后发现,血液内并无一氧化碳,相反充满了二氧化碳,这是窒息的典型结果,结合尸体脖子后面的黑色指印,他们判断有人曾猛烈挤压她的皮肤,致使她窒息而亡。
那如果真的是一氧化碳中毒,症状是怎样的呢?一氧化碳窒息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把氧气挤出去。我们体内的氧气由血红蛋白运输,但一氧化碳对血红蛋白的吸引力是氧气对血红蛋白吸引力的两百倍,所以一旦一氧化碳进入体内,它会迅速将氧气挤出血液,最终导致化学性窒息。急性一氧化碳中毒的早期症状是困倦、头疼、晕眩、意识模糊,偶尔还有恶心,这其实和醉酒的状况很像,所以早期的医生经常把一氧化碳中毒误诊为醉酒。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的人,肌肉组织会呈现深红色,喉咙和肺部的黏膜也都是红色,如果把一氧化碳中毒者的血液抽出,倒在盘子里,加入一些碱液,它会变成一团光滑的泛红肉冻,正常的血液反倒会是泛绿的深灰色。
1926年12月,浓雾笼罩纽约,一位巡逻的警官在码头上看到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包裹,鬼鬼祟祟的样子,巡警朝他喊话,他不理,巡警掏出枪再次喊话,那人仍然不理,他把手中的包裹投到河里,然后逃进了雾里。巡警立刻向空中开了三枪,附近的其他巡警闻声赶来。其中一个警察正面撞见了这个人,将他扑倒在地,警察立刻注意到这人脸上红得古怪。带到警局后,这人什么也不说。警察后来去了他的公寓,那里简直像一个血腥屠场,厨房地板上是一个被分尸的女人。警察立刻以谋杀及分尸的罪名,将这名叫做特利维亚的男人关进了囚房。
那天晚上,诺里斯应召来到犯罪现场,他凑近看了尸体的脸,发现这张脸泛出一种粉红色,他告诉警察说,你们不能以谋杀抓特利维亚。警察感到莫名其妙,没有理诺里斯,他们迫不及待要以谋杀罪论处特利维亚,但随后格特勒的一系列检测让他们目瞪口呆。格特勒从女尸的心脏中抽血,展开标准的化学检测,这些血液都没有变成正常含氧血的深灰色,而是呈现出耀眼的红色。格特勒就此报告说,死者在特利维亚拔出刀子之前就已经死亡了。
特利维亚后来供述说,那天晚上的起因是这名叫安娜的女人来找他要酒喝,安娜四十出头,邻居们都说她是个酒鬼。特利维亚分给了安娜一些酒,之后试图请安娜离开,但安娜不走,两人起了一些争执,后来特利维亚作罢,借着酒劲,在桌边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他醒来,看见安娜躺在地上,摸上去又冷又硬。他当下的第一反应是认为自己在争执的时候不小心把安娜掐死了,慌张之际,他做出了要处理掉这具尸体的决定,于是就有了前面我们讲到的一系列事情。
特利维亚的供述,加上诺里斯和格特勒提交的一系列检测说明,再加上当天晚上特利维亚放在煤气炉上的一个咖啡壶,三样证据最终帮特利维亚免去了谋杀罪名,被判非法肢解尸体罪,这意味着他可以进监狱,而不用承受残酷的电椅刑罚。这起案件也让诺里斯和格特勒一战成名,他们让所有人认识到毒理学是个强有力,并且值得信赖的工具,在这之后医学专家可以自信地站在警察和法官面前,用清晰的化学图表展示他们眼中的真相。
但检测的技术和方法越先进,下毒的材料和手段也越高超。接下来我们要再讲到一种有毒化合物,一种极为凶险,又几乎完全不留痕迹的毒物——铊。
“铊”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thallos),意思是长出新叶的植物,但实际上它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脱发剂的主要成分。《美国医学会杂志》曾报道说有一名女人使用含铊脱毛剂,最后头发全掉光了,还有一位女性更糟糕,不仅头发掉光了,还失去了视力。美国医学会不断发出警示,呼吁停止和使用此类产品,但爱美的人们根本听不进去,在他们眼中,这种剧毒物质,是一份能让皮肤焕发出白皙光泽的礼物。
铊无色无味,可以轻易混入任何液体。铊中毒者,最初的迹象是恶心、腹泻、腿疼,偶尔伴有精神抑郁或亢奋、昏迷和失智等,这些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某种传染性疾病或者神经疾病。而且铊中毒者在死后解剖中,也很容易让人疑惑,因为这种物质几乎不会给身体制造异质性损害,它不像氰化物有蓝色信号,或一氧化碳有红色信号,也不像镭中毒会导致骨骼破裂,急性铊中毒,尸体也许会显示出胃黏膜发炎的情况,器官上有些许血块,其余不会有任何痕迹了。所以铊中毒死亡太容易被误判为其他死因,有人因此说铊是一种属于化学家的毒物,或者说它是高智商人士的犯罪工具。
1935年,纽约市曾发生了一起一家五口离奇死亡案件,格罗斯的妻子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相继去世,他们的统一特征是死时头发几乎都掉光了,邻居回忆说其中一个小女孩的头“秃得就像你的手”。格罗斯先生和他一个儿子没有死,但因类似症状住进了医院。医生怀疑他们一家患上了支气管肺炎和脑炎。但据毒理学实验室对尸体的检测,他们都是慢性铊中毒而死,最大的嫌疑人是格罗斯先生本人。
警方后来发现,格罗斯的公司积压了一批可可,雇主卖不出去,就提出低价出售给雇员们,格罗斯买了一批远超过他实际需求的可可粉。随后警方又发现格罗斯的公司还储备有充足的硫酸亚铊,用来给大楼灭虫和灭鼠。于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格罗斯先生在可可粉中下了毒,致使妻子和孩子死亡,他的动机就是贫穷,当时格罗斯的薪水从每周三十五美元减至二十美元,根本无力负担家庭生活,他买下这么多可可,是为了给家人充当晚饭。但格特勒对这批可可粉做了一系列检测,却又并未在其中发现铊元素。
这时警方传来消息,他们在格罗斯的公寓搜到了几本书,扉页上有格罗斯太太的名字,其中有两本是医书,讲述了各种毒药的信息。随后警方又通过询问邻居得知,格罗斯太太曾说她已经弄到了一种毒药,起效缓慢并且绝对致命,她打算让孩子们吃下这种毒品,因为她实在无法忍受在如此绝望的贫困当中养育自己的孩子了。而她之所以没有给丈夫下毒,是因为她相信如果没有一大家子的花销,丈夫还能找到更好的生活。
格特勒在所有的孩子体内都发现了铊,但格罗斯太太体内却没有找到,她如原本诊断的那样是死于脑炎。这提示出一种可能,最后关头格罗斯太太或许还想在毒死四个孩子后,带着肚子里还未出生的孩子和格罗斯先生重新开始他们的婚姻生活。因为在可可粉中并未发现一丁点格罗斯公司的硫酸亚铊,法庭最终以缺乏足够证据为由驳回了对格罗斯先生的指控。但这就说明格罗斯太太是凶手了吗?其实也不一定,毒品从何而来,下毒方式又是如何,再也无人知道了。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铊成功地藏匿了凶手,铊让凶手在谜团中无处可寻、无从确证。
格特勒的毕生所求就是制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格特勒在1959年退休,他在工作生涯中分析超过十万具尸体,发表了足以塞满一个图书馆的论文,还帮助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毒理学家。他的学生参与创立美国法医科学院毒物学部门,他们在写作中多次提到:“如果有谁能担当得起‘美国毒理学和法医学之父’这个称呼,他就是格特勒博士。”
投毒杀人的故事显示了我们道德中最坏的一面,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杀手有那么多种,但最可怕的杀手是“那个事先周密计划,欺骗朋友、妻子、情人吞下某种会令器官溶解、皮肤起泡、肌肉痉挛的东西,并且明知这一切会发生还要那么做的人”。但毒理学实验室的故事也显示了我们对于正义和道德标准的追求。这两个故事此消彼长,揭示出了我们天性中的两面性。作者用这本书回望了毒理学的起点,这个故事离我们很遥远了,但也正因为遥远,它或许包含了一种初心和信念,正如作者在书的最后写道:“我相信,对道德标准的追求是这个故事的中心,它最终会胜过我们中间那些下毒者的诡异魅力。”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作者黛博拉·布鲁姆在书中为我们介绍了10种常见的有毒化合物,今天我们主要了解了其中四种,包括从木材中提取而来、一度被用来制造假酒的甲醇,呈现出诡异蓝色的氰化物,不断飘荡在我们生活中的一氧化碳,以及无色、无味、不留痕迹的铊。此外,我们也回顾了美国毒理学的诞生过程,诺里斯和格特勒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着手搭建毒理学实验室,他们用标准化的化学检测辅助案件的侦破,一举提升了验尸官、法医、化学检测师在刑侦过程中的地位。毒物的历史很长,毒物与我们生活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有时候毒物与药物的区别仅仅在于剂量,但回顾历史,我们也发现总有人在设立和捍卫我们的道德标准,在利用技术追击暗处中的下毒者。这是一场永远不会停下的竞赛。
此外,除了我们今天介绍的四种毒物,书中其实还介绍了尝起来有金属味儿的砒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汞、带有放射性的镭等,今天碍于时长,我们没有一一展开,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非常推荐你翻开原书读读看。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毒理学的发展其实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从简单到复杂,从野蛮到文明,从粗鲁到优雅,从迷信到科学,从取人性命到救死扶伤。”
-
毒物的历史很长,毒物与我们生活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有时候毒物与药物的区别仅仅在于剂量,但回顾历史,我们也发现总有人在设立和捍卫我们的道德标准,在利用技术追击暗处中的下毒者。这是一场永远不会停下的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