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盘》 杨以赛解读
《洋盘》| 杨以赛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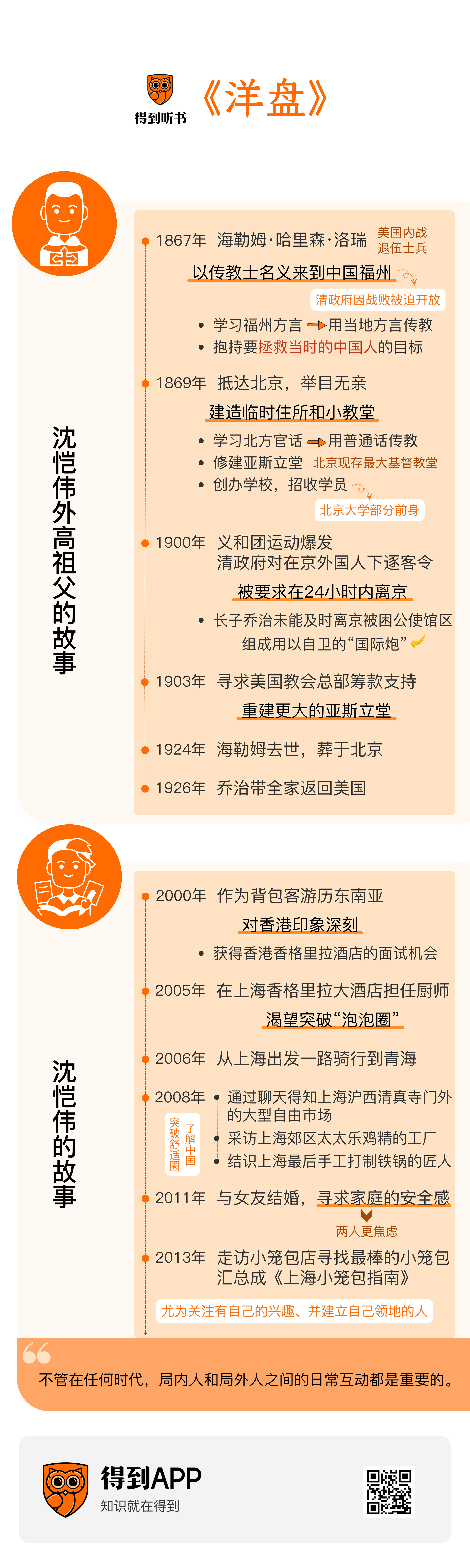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洋盘》,副标题是“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这是一本在上海生活了20多年的外国人写下的上海生活录。
“洋盘”是一句上海方言,指的是那些不太了解本地习俗的外来者,这是本书作者沈恺伟对自己的一个自嘲。沈恺伟,英文名叫Chris,2005离开家乡迈阿密,来到上海,在这里从24岁待到40多岁。他在上海做过厨子,做过杂志编辑,眼下他开办了一家咨询公司,专门考察中国的餐饮业。这20年多间,他游走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探访了一个又一个城市角落。这本书记述的便是他这20多年在中国的经历与成长。
这本书一方面呈现了一个外国人视角下的上海,你可以借此从另一个角度感受上海这座城市。电视剧《繁花》在2023年年底大火,“得到听书”也已经解读了《繁花》的原著。如果说《繁花》描绘的是上世纪60至90年代的上海,那《洋盘》描绘的则是一个当下的上海,是全球化时代下的上海故事。另一方面,在这本书中,沈恺伟除了讲自己的故事,还讲到了自己外高祖父的故事。100多年前,他的外高祖父曾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参与了燕京大学和同仁医院的建设。沈恺伟在书中交叉讲述了不同时代下“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以此折射出社会与人的变迁。用《鱼翅与花椒》作者扶霞的话来说:沈凯伟怀着对中国的深厚感情,真诚地探究了外籍人士在中国生活意味着什么。
好,接下来,我将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回到100多年前,来听听沈恺伟的外高祖父的故事,那一代外国人是怀着怎样的目标来到中国,又在中国经历了什么。第二部分,我们来了解沈恺伟在中国的经历。他的经历和他外高祖父的经历相比有何变化,这背后又折射出了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时间回到100多年前,1867年,沈恺伟的外高祖父,一位年轻的美国内战退伍士兵海勒姆·哈里森·洛瑞,以传教士的名义来到中国。当时,中国已在鸦片战争后开放了几十年,共有五个通商港口对外国人开放,福州是其中之一,而这也是海勒姆来中国的第一站。他在福州待了两年,这期间他非常努力地学习福州方言,希望能够用当地的语言来传教。与此同时,美国的教会长老们觉得时机已到,想把传教事业拓展到中国北部,海勒姆又被选中去北京建立一个新的传教所。
1869年春,海勒姆和家人乘船离开福州,在四月抵达北京。他在这里举目无亲也无朋无友,样样都要自己摸索。在北京的头几年,他们过得极其艰难。当时的京城被划分为两个城区,北边是以紫禁城为主的内城,是八旗子弟的居住区,南边是汉人居住的外城,无论是哪边,都很难再找到一块地皮了。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海勒姆才在哈德门,也就是现在崇文门外的南北向主干道上找到了一处地皮,建造了住所和一处临时的小教堂,就此安定下来。
海勒姆花了两年时间学习福州话,来北京后,他又要学习北方官话,也就是普通话。他很有天赋,不出几年,就能用普通话传教了。他的传教足迹遍布整个华北地区,与他同时期的传教士记录了当时他们在北京街头的见闻:“京城街道拥挤、嘈杂,熙熙攘攘,如同在中国别的大城市一样,很多行当的底层工匠会在街头揽活儿摆摊儿……不管在哪里,只要补鞋匠、补锅匠和铁匠找到活计,就会当场铺开摊位;甚至屠夫也是当街屠宰动物;卖药的通常也是算命的,卖唱的和江湖郎中,他们吆喝起来可是以一当十……最引人注目的是剃头匠,他们在露天为顾客剃头、扎辫子,极其认真,一丝不苟。所有底层市民——甚而一些高阶权贵——都会在街头理发。”此外,除了这些商贩,街头上还有大量的骆驼。当时北京市内供暖靠煤,而所有的煤都是用骆驼从西北地区运来的。
海勒姆后来在京城修建了一座能容纳三四百个座位的砖砌教堂,叫做亚斯立堂,你至今还能在崇文门内大街见到这座教堂,它是北京现存的最大基督教堂。海勒姆和其同伙们还借由亚斯立堂创办学校,招收了四百多个学员,既有教会子弟,也有附近的妇女和儿童。他们还在19世纪70年代末创办了寄宿部,后来这个分部发展成为怀理书院,再后来海勒姆又将它拓展成为汇文书院,而这其实也就是北京大学的部分前身。
不过,传教士的到来毕竟是清政府因战败而被迫开放的结果,他们的活动和主张在很多地方都不受欢迎。早在传教所落地福州的时候就发生过传教士被围攻的事件。海勒姆在华北也是麻烦不断,有一次他要穿过南边的外城,去接一位来访的主教及其妻女,就在途中被一群人投掷泥块和石头,他数次被砸中,但幸好没受重伤。除了这些时不时的攻击,他还要应对当时动荡的时局、鼠疫、大范围的饥荒与接二连三的洪涝。在一份1899年的教会工作报告中,有传教士写道:“在我们的传教地区,黑死病、鼠疫继续肆虐。今年,在好几个区域,会员离世致使我们教会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其中两次,新教会的工程因此被迫中止。这么多人因病死伤,加上随之产生的额外费用,迫使我们放弃建业。”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有很多传教士陆续离开中国。尤其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很多人逃难,并想寻找防身的方法,一时间锻造刀剑的广告牌随处可见。这年六月,有消息传说德国人在公使馆里打死了一名义和团人,由此矛盾激化,大多聚集在外城的义和团人涌入内城,看到外国建筑物就打砸抢烧。清政府就此对在京外国人下驱逐令,限他们在24小时内离京,清军会护送他们安全抵达天津,登船离境。
这年海勒姆人在芝加哥,但他的长子乔治·洛瑞身在北京。乔治出生于福州,在北京长大,此时是传教士医院的外科医生。他没能在清政府限定的24小时内离京,最后同一群传教士和华人基督徒被围困在了公使馆区。公使馆区是一个300多亩的长方形地块,诸国在区内都有自己的独立院落。没有人知道自己会被困在这里多久。当时公使馆区里共有150匹马,他们每天宰两匹,分给众人食用。他们还在屋子里找到了一个磨盘,用它把粮仓里的小麦磨成粗面粉,做成了粗面包。此外炮火一直没停过,他们无意间发现了一枚曾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使用过、早已生锈的英国炮弹,之后意大利公使馆提供了炮架,俄国提供了弹壳,美国提供了炮手,组成了用以自卫的所谓“国际炮”。关于这段历史,有很多叙述版本,这里是传教士视角的叙述,“得到听书”此前解读过一本叫作《中国切片,1900》的书,它也叙述了这段历史,不过是从清政府和义和团的视角,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
围城一共持续了55天,1900年秋,海勒姆回到北京,他平生的心血都化为了废墟,传教所连地基都被撬了,以至于海勒姆已经无法辨认原来的楼舍在哪里了。但年届六旬的海勒姆不愿放弃,他恳请美国的教会总部筹款支持,在1903年年底,他重建了一座比以前更大的亚斯立堂。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业,而他的儿子乔治则在新建起的医院担任外科医生,这间医院其实就是今天的同仁医院的前身。
海勒姆1924年在北京去世,葬在了北京。乔治在1926年带着全家回到了美国,他的儿女们都在北京出生长大,回到美国后只要相聚,就会说起中文,但他们和中国的牵连也就仅此而已了。用沈恺伟的话来说,他们在中国的岁月就此成为一段鲜少被人提及,甚至连子孙也逐渐遗忘的历史。他们一家与中国的关联在20世纪60年代乔治的小儿子去世后就彻底断了,直到40多年后,2005年,他们的外孙沈恺伟又从美国来到中国。
沈恺伟抵达中国时是24岁,和他的外高祖父海勒姆·洛瑞是同样的岁数,但他们的动机有着天壤之别。海勒姆是带着一份宏大的使命、抱持要拯救当时的中国人的目标而来,而沈恺伟单纯地因为喜欢就来了。他们面临的中国也完全不一样,海勒姆面对的是一个试图救亡图存的中国,而沈恺伟面对的是一个以独立自主的方式与世界各国交往,并凭借强大的经济引力吸引了很多人前来的中国。沈恺伟在书中说,当他回看他的家族历史的时候,一方面他为外高祖父们在中国的奉献和成就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当他看他们写的一些关于中国人精神和中国人的文章时会感到有些难以接受,觉得他们带有一些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感觉。沈恺伟说:“当今中国不需要一群奔波的外国人来‘拯救’。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拯救别人——我至今仍在卖力地学习如何拯救我自己。”所以,沈恺伟的故事是一个全新的故事,是当代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2000年年初的时候,沈恺伟以背包客的身份游历了东南亚,其中他对香港印象深刻。在沈恺伟看来,香港个性独特,兼有中西方文化,他感觉特别新鲜,特别想在那儿闯荡一下。回到美国后,他开始琢磨要怎样才能在香港找到一份工作。他当时已经在迈阿密最好的餐厅干了3年厨师的活儿,他想也许他可以杀到香港半岛酒店的后门,跟主厨提出免费打工。随后他立马卖掉了他的摩托车,处理掉本就不多的几件家什,和亲朋好友告别,奔赴了香港。
但事情根本不像他想得那么容易,他连半岛酒店主厨的面都没见到,而且冷静下来后,他意识到半岛酒店里都是一等一的好厨师,怎么可能会要一个不会说粤语,而且根本没资格在香港合法工作的外国人呢?等钱快用完后,他打算去泰国,那边东西便宜,能省一点钱。转机就出现在了去泰国的飞机上。坐他邻座的男人也是厨师,在曼谷一家五星级酒店工作,他认识香港餐饮界很多人,在他的帮忙下,沈恺伟得到了香港香格里拉酒店的面试机会。几周后,他飞回香港参加面试,面试官开门见山,说香港地区的工作有点困难,但他要去内地的话,倒是可以立马安排。就这样,沈恺伟在2005年来到了上海,在陆家嘴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担任厨师。
当时沈恺伟对上海的第一印象是这里到处是工地,他在书中写道:“深夜下班时,我能看到焊接时的火花从高楼侧面飞溅下来,直落几十层楼,像橙色的萤火虫在空中飞舞。建筑工程全天推进,24小时不间断。打光灯照亮了工地。”工地显示了蓬勃的发展形势,当时浦东房价已经涨到了3万元一平方米,沈恺伟要是在当时买了一套房,眼下就是千万富翁了,但他没有买,一来他没那么多钱,二来他打算在上海待一年就走。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都是这种想法,一次只想12个月,过一年算一年。但事实上后来他们都在中国待了很多年。
上海的外国人有自己的圈子,用沈恺伟的话来说,上海分为中国人的上海和外国人的上海,外国人的上海是一个围绕着意大利餐厅、进口超市、法国幼儿园和英国医生所建立的圈子,几万的外籍人士很舒适地生活在这个圈子里,沈恺伟把这称为“泡泡圈”,因为它像泡泡一样光鲜亮丽但又很脆弱。沈恺伟不想一味待在这样的圈子里,他想“真正地活在中国”。于是他总是不断想尝试一些“泡泡圈”之外的活动。来上海的第二年,沈恺伟辞掉了在酒店的工作,开始给一些刊物写稿,他借由这个机会,对中国展开了一番探索。
2006年的夏天,沈恺伟骑着一辆摩托车从上海出发,一路骑到青海,横穿半个中国。他穿过了皖南的山林,登上了当时刚刚竣工的三峡大坝之巅,在甘肃他在佛教石窟群休息了一天,在兰州他吃了生平第一顿地道的拉面。11月底,他终于抵达青海西宁,这将近5000公里的旅程,让他感叹,“中国是无穷尽的”。
2008年,他在上海和一群卖羊肉串的人聊起来,随口问起他们是在哪里买羊肉,结果收获一条线索,在上海沪西清真寺门外有一个只在周五出摊的大型自由市场,来自各地的人会在这天聚集在这里吃饭、购物。夏季,小贩们会用巨大的冰块做刨冰,淋上酸奶、蜂蜜和金色的葡萄干。冬季,人们去吃热气腾腾的羊肺子、羊肠子。今日,这个起初不为人所知的集市已经成为中外游客的观光目的地。
此外,他还去采访了上海郊区太太乐鸡精的工厂,结识了上海最后一批手工打制铁锅的匠人。沈恺伟在这个过程中一边了解中国,突破自己的舒适圈,一边作为一个此前从未受过写作训练的人,他学习到:不管写作的主题是什么,只有当你深刻地了解人性、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乃至最终了解我们自己时,你才能写出最好的文章。
当然,这些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他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要面对自己的收入问题,以及婚姻和家庭问题。沈恺伟说他刚到上海的时候拿到的工资和中国本地副厨师是一样的,月薪一万元人民币,而其中房租就要花掉4300元。后来辞掉厨师工作,写稿获得的收入就更低了。沈恺伟在书中打笑说:“在美国时,我是一个年轻的厨师,太穷了,买不起保险;在中国,我成为一个年轻的作家,还是穷,还是买不起保险。”因为没有保险,他有10多年一直唯恐自己受伤患病。但这些大体上都能撑过去,真正令他感到棘手的其实是他的爱情。
沈恺伟的女朋友萨拉在2008年来到了中国,她是一名陶瓷艺术家,沈恺伟一直希望她能将她的陶瓷技艺融入中国的艺术传统,因此还承诺说在萨拉找到一份她中意的工作前,就由他来承担养家的任务。两个人当时租住在石库门公寓的一个小房间,日子过得很拮据。萨拉后来在一个摄影画廊找到一份工作,拿最低工资。在中国开创自己的艺术事业这件事比她想象得要难多了,她常常在和朋友的通话中泣不成声,而沈恺伟也不知道怎么能帮助她。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因此出现了一些裂缝。沈恺伟为此很内疚,他在书中说:“她离开了亲朋好友,放弃了她在底特律艺术界的立足之地,和各种艺术家社群都断绝了联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半吊子的美食作者、自由撰稿人,靠给公司写文案才能凑合过活的人,这家伙还不能全心全意地让她幸福?我羞惭难当。”
2010年的时候,沈恺伟的奶奶去世,他回了一趟美国。他们全家人一起聚在奶奶房间,陪着她直到去世。沈恺伟在其中感受到了家庭带来的安全感。他突然意识到,他也许需要建立一个家庭了,也许只有家庭会给萨拉带来安全感。2011年1月,沈恺伟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87层向萨拉求婚,然后4月份他们在安徽西递古镇举办了婚礼。
但婚姻和家庭没有像预想的给他们两人带来安全感,相反让他们都更焦虑了。沈恺伟认为是他自己的问题,从十几岁以来他便存在抑郁的问题,这让他很难投入亲密关系,没办法带领两人进入更幸福的境地。很多次萨拉会因为无助而在夜里大哭,这时他们住在楼下的房东,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就会邀请他们去她家,用她知道的最好方式安慰他们。但后来他们还是没撑下去,选择了离婚,离婚那天他们都哭了,从政府办公楼走出来后,他们手挽手走到一条更宽阔的大马路上,沈恺伟在书中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了。
沈恺伟在中国的经历跟他的外高祖父对比起来,可能要显得细碎和鸡飞狗跳得多,甚至可以想象,他的故事在他肩负崇高使命的外高祖父看来可能不值一提。但这就是他的生活,这也可能也是今天很多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个地方生活,然后着力在解决那些普通又平凡,甚至可能是每一个在中国的年轻人都要面对的生活问题,从这个层面而言,他们或许比他们的祖辈更深入地融入了中国。
眼见在中国就快待到第十年了,沈恺伟的状态越来越差,越发严重的抑郁几乎彻底阻断了他的生活,那究竟什么能够拯救自己呢?他后来发现还是那些具体的人和事,是那些他觉得有意思,并且能充分体现他自我价值的事情。
自2013年年底,沈恺伟脑袋中就一直有一个想法,他想要走访25家小笼包店,找出全上海最棒的小笼包。他很快就行动起来,从淘宝买了尺子和电子秤,带着它们到各个店测量小笼包面皮的厚度、肉馅的重量和汤汁的量。他的这项行动一直持续到2015年,他将他收集的信息汇总成了一本《上海小笼包指南》。这本指南让他名气大涨,很多媒体争相来采访他。沈恺伟很意外,他本来以为他会被骂,会被说一个白人竟然敢给上海本地的小笼包排名,但他竟然被接纳了,还出名了,甚至上海餐饮协会的负责人还表示要支持他后续的研究。沈恺伟说他当时直接哭了出来。
也是2015年,沈恺伟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外出散步,他在一个巷口的小卖部停下来,小卖部的玻璃柜上摆了很多啤酒,而且还都是他从未见过的牌子。沈恺伟自己很喜欢喝啤酒,他知道上海大部分卖啤酒的店卖的都是国产品牌和少数进口啤酒,其实主要就是比利时啤酒,在一个其貌不扬的小卖部见到那么多种类的瓶酒,这让沈恺伟大吃一惊。更让他大吃一惊的是这个小卖部的老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40多岁的上海妇女,她一边经营小卖部,一边做复印生意。沈恺伟随即采访了这位妇女,她叫张银娣,她其实不怎么懂啤酒,就是喜欢喝而已,退休之后开了这家小卖部,她联系了几家啤酒供应商,跟他们说你们就把手上的啤酒都带来就好了,她想没人买就自己喝,也不亏,就这样她开出了上海有最多啤酒种类的一家店。沈恺伟将张银娣的故事写成了报道,不到一天就有了20多万的浏览量,张银娣一下子成了网红,很多爱喝酒的人慕名前来。张银娣后来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开了五六家门店,最远的开到了江西南昌,她在那里储存了上万个品牌的啤酒。
沈恺伟看到的上海是极其丰富和多元的,他尤为关注那些有自己的兴趣、并围绕这个兴趣建立了自己领地的人,他借由他们深入上海的一个又一个角落,也从中汲取了不少力量,帮助他去打理自己的生活。从24岁来到中国后,他在这里工作,结婚、离婚,可以说人生的大事几乎都在这里发生了,眼下他44岁,他开始考虑他接下来的大事,比如死亡。一个外国人在上海死亡会面临一些什么?自2008年起,外国居民不能在中国的墓地下葬,一部分人会选择委托国际遗体遣返公司将遗体遣返回国。沈恺伟去拜访了上海一家叫作“罗斯泽特”的遗体遣返公司的创始人,这位创始人告诉他,每年大约有1500名外国人在中国死亡,他们都面临着复杂的后事处理程序。一旦考虑起死亡的问题,就不得不考虑要在什么时候要离开这里的问题。沈恺伟逐渐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他还没有答案,但眼下他还在中国,继续着对这里的挖掘和探索。
在书的最后,沈恺伟回顾了他外高祖父的故事和自己的故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它们折射出了很多社会的变化和人的变化。但这两个故事也有一些相同的题旨,它们显示出来,不管在任何时代,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日常互动都是重要的。用沈恺伟在书中的话来说:“每个外国人,甚至每个来过中国、对中国有所了解的游客,都会在回家后变成非正式外交官。他们会向别人介绍这个国家,描述现代化的城市和高铁、不可思议的食物、干净的街道以及任何令他们难忘的细节,就这样,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普及了活生生的中国形象。‘中国’由此不会再让人感觉太抽象,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地方,甚或是生活过、爱过的地方。”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沈恺伟在这本书中写下了两个不同时代下“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100多年前,他的外高祖父带着使命来到中国,作为传教士,他一心想援助和拯救当时的中国人。100多年后,24岁的沈恺伟带着一颗迷茫的心来到中国,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想在这里建立一份有意思又有价值的生活。外高祖父的故事是宏伟的、理想主义的,但在今天看来其实也是带有一些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而沈恺伟的故事是细碎的、鸡飞狗跳的、是关于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寻找和建立自我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对比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在这100多年间的发展变迁,由此无论是外国人看中国的视角,还是中国人看外国的视角,都有了相应的变化。如果说100多年前,海勒姆想的是谁拯救谁的问题,那沈恺伟和今天的我们面对的则是如何认识自我、并在广袤的天地下安置自我的问题。沈恺伟的故事或许提示了我们,越是想要认识和建立自我,其实就越要勇敢地去探索陌生的环境,并且接纳和理解他者。以他人为镜,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沈恺伟的故事是一个全新的故事,是当代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
-
越是想要认识和建立自我,其实就越要勇敢地去探索陌生的环境,并且接纳和理解他者。以他人为镜,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