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说忧伤》 杨以赛解读
《诉说忧伤》| 杨以赛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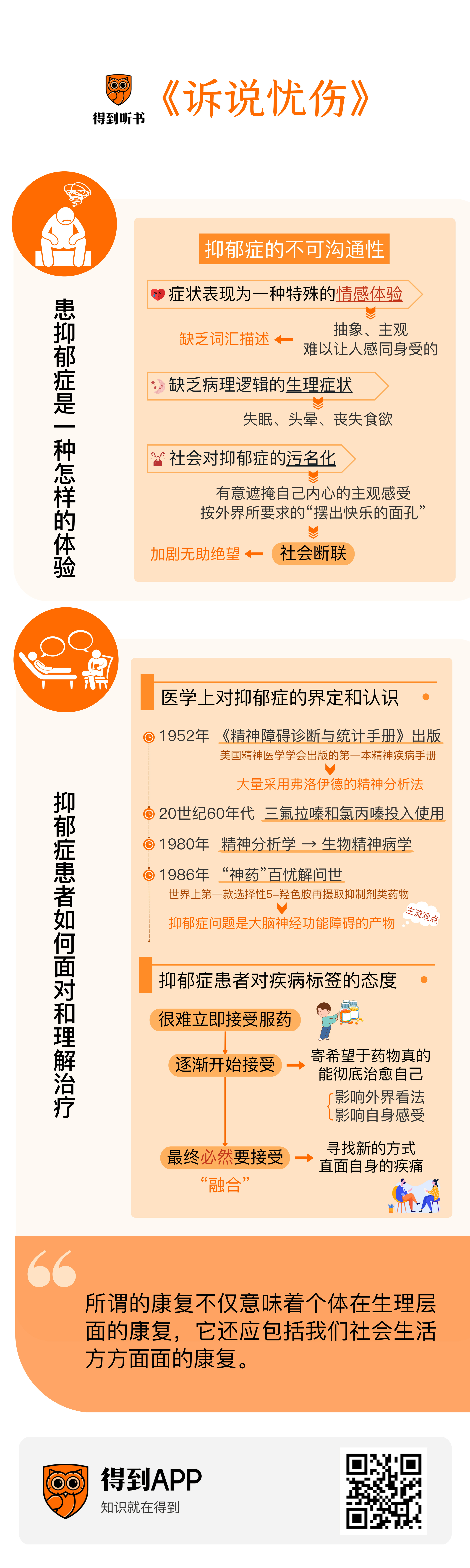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诉说忧伤》,副标题是“抑郁症的社会学分析”,这是一本从社会学角度探讨抑郁症的书。
据医学期刊《柳叶刀》在2022年发表的《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抑郁症重大报告》统计,全世界每年有5%的成年人患有抑郁症,它是自杀死亡者中最常见的精神疾病。报告中还称抑郁症每年导致全球经济损失达一万亿美元,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我们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中会听到这一疾病,似乎对它已经很熟悉了,但真要问起这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它有何症状,如何治疗,它的危险和困难是什么,我们似乎又不太能回答出来。
“得到听书”此前已经解读过不少与抑郁症相关的书籍了,像是《深渊》《抑郁帝国》《正午之魔》等,今天这本书和这些书的不同在于,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戴维·A.卡普,是美国波士顿学院社会学名誉教授,他是一名社会学家,同时他也是一名抑郁症患者。卡普自身与抑郁症斗争多年,可能也正由于此,他十分强调抑郁症患者自身的视角。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卡普提到,所有的抑郁症研究,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听了一大堆来自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治疗师等专家的声音,却始终听不到患者自身的声音。出于这一点,他决定要写一本书,让患者亲自来谈论抑郁症究竟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情绪、态度和个人观点的。
卡普深入采访了50位被明确诊断为抑郁症,并接受了长期治疗的患者。他说他这本书,目的不在于提供一套能够解释抑郁症的理论,或是一套摆脱抑郁症的方法,因为这不是他一个人和一本书能够做到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让患者说出他们的心声。卡普坚定地认为,要真正理解一个人的经历,就必须从经历者的主观视角出发,也就是说你必须听取来自经历者的心声。卡普说,他希望读者能够借由这些心声,更准确地认识抑郁症,理解它的深层困境,并感受到困境背后患者真实的痛苦和勇气。
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将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看患抑郁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抑郁症患者是如何描述这种体验的。第二部分,我们来看对抑郁症的治疗,抑郁症患者面对的医疗过程是怎样的,他们在当中有怎样的感受和思考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患抑郁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这个问题可能只有抑郁症患者自己能够回答。在这本书中,卡普采访了50多位抑郁症患者,他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要如何向没得过抑郁症的人描述抑郁的感觉?
有一位叫做尼娜的患者,一开始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没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后来她给卡普回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她将抑郁描述为一个黑洞,她说:“抑郁偷走你过去的身份,也阻止你预见将来的自己,并用黑洞取代你的生活。你就像一件被蛾吃掉的毛衣,没有留下任何最初的东西,只有些许残片,暗示你曾经的才干、能力、潜力都已不复存在了。”
还有一些患者将抑郁症描述为“溺水”,或是“困在笼子里、走不出去的动物”。有患者甚至会说:“那感觉就像被人拿着一根点燃的火柴烤着,火焰真的很热,你试图忍受着,它就耗着你,越耗越厉害,一直到最后火焰燃尽,你也耗尽了。”
你会发现这些患者都选择采用一些意象或比喻来描述抑郁症的体验,这其实提示出抑郁症的特殊性,它不像其他病症一样有肉眼可见的症状,抑郁症的症状更多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要让其他人明白这种情感体验是非常困难的,哪怕用上更多、更准确的意向,它也只能是抽象、主观、难以让人感同身受的。
当然,抑郁症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生理症状,诸如失眠、头晕、丧失食欲等,但更严重一些的症状,常常因为缺乏病理逻辑,同样让人难以理解。比如有患者举例说:“当你真的很抑郁的时候,如果你在卧室里,有人说卧室的另一边有100万美元,你要做的就是抬脚下床,走过去拿走那100万美元,但你就是没办法去拿。”
我们常建议一些遇到情绪问题的人去室外活动、与人交际,或者随便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在一些时候是可行的,但当情绪问题发展成为病症,这些建议就难以实现了。书中一位患者直言:“我当然知道这些事情可以舒缓情绪,但你要知道,我觉得糟糕的时候,我甚至不能下床。”“像起床、洗澡这样的事都让你感觉力不从心,如果不是你自己体验过这件事,你就无法真正理解它。”
如此种种,让抑郁症患者很容易被人误解。在书中,有患者提到说当她尝试向家人说出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家人只会说,“为什么你不能振作起来”,或是,“这有那么难做到吗?你为什么不帮你自己和其他人一个忙”。甚至有时候,面对专业的心理医生,沟通起来也仍然是困难的。有患者在书中说:“我觉得我不能正常工作了,我已经很歇斯底里了,心理医生却仍然在用他们那一套心理学术语跟我说,你要去处理森林的兔子和狮子什么的,我的天呀,她就是不明白。”
而且,我们还不能忽视的是,社会存在着一种对抑郁的污名化,这让本就困难的沟通变得更困难了。书中记述了一位患者,她很直接地说道:“我从没告诉任何人我在想什么,因为我感觉谈论不好的事情或者不好的感觉在这个社会是一种禁忌。我担心我告诉别人我的感受,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会觉得我疯了,他们就不会再尊重我了。”
所以,到头来很多抑郁症患者,一方面要承受这个疾病本身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承受这个疾病的不可沟通性所带来的痛苦。用患者自己的话来说,“这痛苦对我真的有点新,因为你没有相关词汇来描述它”。
久而久之,抑郁症患者会因为这种费力而拒绝与人沟通,甚至是有意遮掩自己内心的主观感受,按外界所要求的“摆出快乐的面孔”。作者卡普在书中说:“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许多严重抑郁的人居然长期坚持完成了表演,而表演的代价就是让本就痛苦不堪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
最终,抑郁症患者会在这种不可沟通中把自己越来越孤立起来,以至于内在和外在都彻底失去与这个社会的联结,作者卡普将这称之为“社会断联”。卡普说,这就像是一个悖论,抑郁症患者为了避免由沟通带来的痛苦,选择孤立和断联,但孤立和断联,又不可避免会加剧抑郁症患者的无助和绝望,但他们仍不懂求救,于是这种无助和绝望只能导致更进一步的孤立和断联,这就像一个恶性的循环。在卡普所采访的患者中,有一些患者明确表示,他们自杀一方面是想逃离抑郁的痛苦,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身边的人能理解他们的状况到底有多严重。有一位41岁的女性患者说:“我认为第一次自杀是想告诉一些人,事情要超出你的想象。这就是我想达成的效果,我希望他们后退一步,然后理解这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
抑郁症的不可沟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断联,是抑郁症患者极容易被忽视的困境。那要怎么才能走出这个困境呢?作者卡普在书中也讲到了自己的故事。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存在情绪问题是在1974年,那一年他家庭和事业各方面的状况都很好,他在波士顿学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且刚刚签下了自己第一本书的出版合同,有一个好妻子和一个帅气的儿子,还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女儿,按理说他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可不知道怎么,他突然开始睡不着觉。尤其是那一年他外出出差,整整一周,他都无法入睡。他起初觉得可能是来到一个陌生城市,借住在别人的公寓,对周遭不太熟悉的关系。但他经常出差,从没有过如此严重的睡眠障碍,所以他又想,是不是得流感了。但这症状和流感又不完全一样,他感到又累又痛,在晚上,他的脑海里都充满了令人不安的胡思乱想,到白天,他又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悲伤,就像有亲人去世了一样。这种感觉持续了很长时间,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尝试去弄清楚他到底是怎么了,他要如何命名这个问题,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如何向其他人描述这个问题,以及如何带着这个问题继续生活。他坦言这个过程充满了困惑和不安。要到什么时候他才稍稍从这种困惑不安中走出来一点呢?他在书中说,是当有人告诉他,他患有临床抑郁症,需要服用“抗抑郁药”的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换一句话说,当抑郁症患者知道我生病了,我可以告诉别人我生病了,以及我可以通过服药来治疗我的病,这些确切的东西会把他们带向一个全新的阶段。他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而是一个明确的疾病。书中的一位患者更是直接将此形容为是一种解脱,她说:“此前我的脑海里没有抑郁症这个词汇,当这个词汇进入我的脑海后,我才开始能够理清我一生的感受和事情,我知道我并不奇怪,我只是生病了,这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这样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充满犹豫和挣扎的,对抑郁患者来说,要承认自己生病了,并决定接受各种方式的医学治疗,这当中每一步都会影响他们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来讲一讲,抑郁症患者如何面对和理解治疗,过程中他们会经历一些什么,以及他们有怎样的感受和思考?
在讲到患者的经历和感受前,我们要来简单回顾一下医学上对抑郁症的界定和认识。在医学上,关于抑郁症有一套非常清晰的话语。
作者在书中系统梳理了这套话语的发展过程。20世纪上半叶可以被说成是“心理治疗的时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法,这是一套全新的可用来理解我们自我,并梳理我们内在心理过程的方法,这个革命性的理论推动了心理治疗在美国,乃至在全世界的盛行。1952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了第一本精神疾病手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当中便大量采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精神疾病的成因,并给出相应治疗方法。但到了1960年,人们对于心理治疗的效果没那么乐观了,因为说到底,心理治疗是通过谈话来治疗,它很难被标准化,它的效果也很难被检验。尤其在学界内部,精神科的医生迫切希望被认可为可以治疗明确疾病的、真正意义上的医生,那要达成这一点,就必须将精神疾病明确视为基于生物学的疾病,寻求生物学上的解释。
关键的转折发生在两种强镇定药的发现,在上世纪60年代,三氟拉嗪和氯丙嗪这两种药物被投入使用,人们发现通过服药就能控制精神疾病,患者在服药之后便可以回归家庭和社区了。这两种药物更加坚定了精神科医生的信念,那就是,第一要将精神障碍的描述规范化,第二是要加快寻找药物以治疗疾病对应的生物功能障碍。
在这个观念的推动下,更多的药物被研发出来了,比如治疗焦虑的眠而通、利眠宁和安定等弱镇定药,人们越来越认可药物对情绪健康的有效性,其实也就是认可情绪问题本质上是一种生理障碍。1980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又出版了一本《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相比1960年那一版,这一版从“精神分析学”全面转向了“生物精神病学”。1986年,被称为“神药”的百忧解问世,这是世界上第一款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药物,它能让抑郁症患者迅速恢复活力。之后更多同类药物出现了,像是喜普妙、来士普、帕罗西汀等,它们向世人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是抑郁症的产生,是因为大脑中缺少一种名为5-羟色胺的神经递质。尽管近些年来,很多人都在质疑这类药物对抑郁症的真正疗效,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表明,这类药物的效果并不比安慰剂强。有一项对比研究提出说,如果5-羟色胺理论正确,那么降低大脑中该神经递质的水平的药物应该会诱发抑郁症,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在实验中出现,这说明5-羟色胺与抑郁症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这个问题仍然有争议,现在精神病学学界和大众对抑郁症的主流看法仍然是,抑郁症问题是大脑神经功能障碍的产物。
这样一种清晰、确切的话语到了患者面前是怎样的呢?抑郁症患者是如何逐步认可他们的痛苦是病理性的,又如何判断他们的痛苦达到了需要医疗干预的程度呢?前面我们提到,这一话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将抑郁症患者从深不见底的黑洞中拉了出来,缓解了他们的不安与困惑,甚至是给予了他们希望。有患者直接将这称之为是一种解脱,但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中也充满着不为人知的挣扎。比如作者在书中重点提到,确诊抑郁在一方面给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找到了一个有形的容器,但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你给自己打上了一个巨大的标签。此后你所有的情绪和行为都将会染上这个标签的颜色,并且在没有通过医疗的评估和认可前,你无法自行撕下这一标签。
作者卡普在书中提及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罗森,他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叫做“精神病院中的正常人”。罗森教授为了弄清楚精神正常者和不正常者是否有区别,他让他的8名同事假装成病人,申请进入12家不同的精神病院。实验要求这8名假病人谎称自己经常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但一旦入院,他们就要把一切据实相告。这8名假病人都立即被接纳入院了,其中有7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随后他们不再假装,开始表现正常的自己,但他们的正常却并不能让医院的工作人员相信,唯一质疑过他们病人身份真实性的是病房里的其他病人。这是一个设计得很极端的实验,围绕它有很多的争议,但不管怎样,它让我们看到了精神疾病标签的影响力,罗森教授将这称之为一种“黏性”,也就是说你一旦被打上这个标签,这个标签会彻底黏住你,以至于你无论做任何事都甩不掉它了。
我们可以从抑郁症患者对药物治疗的态度上,看出他们对疾病标签的复杂心理。首先,患者很难立即接受服药。有患者在采访中说道,“难道所有的病都可以用药物治愈吗?精神医师对所有的病都能开出药物,他们喜欢用药物来修补身体,而不是设法让人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们只看了我一眼,就宣布我有抑郁症了”。还有患者更直接地说:“把一个人简化成一系列的化学反应,这让人感到骇人。”
但随着病情的加重,一些患者会不得不说服自己接受药物治疗,也就是接受这一疾病标签。他们甚至会去求药问药,试验各种新药,他们寄希望于药物真的能彻底治愈自己。但很快他们会发现这是不现实的,抑郁症的病理实在太复杂了,市面上的药物很难说是真的找对了症结,还是只是偶然有效。这时候,患者会意识到这个本该将他们从抑郁的黑洞中拉出来的药物,又把他们带往了另一个黑洞,他们要纠结这个药物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有效,哪种药物会更有效,以及究竟是不是要停药。有患者就在采访中直言:“如果按内心想法,我肯定不吃药了,因为我不知道吃和不吃有什么不同,但我又害怕,我好怕一旦我真的离开了药物,我会变得更糟。”这其实正显示出精神疾病标签的作用力,它不仅影响了外界对抑郁患者的看法,它也影响了抑郁患者对自身的感受,患者意识到了标签存在着一些不对,但仍然不得不顺应它行事。
卡普教授在书中说,抑郁症患者最终必然要接受,医学上的话语和手段实际仍然不能完全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需要寻找新的方式直面自身的疾痛。卡普发现很多患者这时候会开始调整他们对这一疾病的看法,既然治愈不可能,那是否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们和疾病共同生活呢?卡普在书中提到“融合”这个词,这个词指向的是,患者需要尽可能地与抑郁症作斗争,但同时也需要尝试构建一种以抑郁症持续存在为前提的生活,带着抑郁症活下去。
卡普在书中记述了他与一位精神健康工作者,同时也是抑郁症患者的对话,他们讲到到底该如何定义痛苦。那名患者告诉卡普说,我们不要试图去区分什么是正常的痛苦和什么是异常的痛苦,因为当你做这种区分的时候,你实际在说,有些痛苦是不必要的。“我最终觉得没有不必要的痛苦,痛苦可能会让人不舒服,但它不是罪,它和世间万物一样,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还有患者更直接地说道:“我们所有人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都会有某种程度的抑郁,如果我们不允许它进入我们的生活,它就可能是破坏性的,如果我们让它进来,它说不定有可能会是一位老师,一位我们可以拥抱和融入的老师。”
卡普在书中提及这些话,他并不是说这些话里的观念就是对的,他更多是想展示抑郁症患者可能最终还是靠自己来直面抑郁这个黑洞,他们要靠自己来定义这个疾病,并排列它在生活中的位置。换一句话说,他们要建立一套全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来应对这个疾病。这个结论显然是有些悲观的,它相当于彻底承认了抑郁症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以至于强调我们要说服自己去接受它,与它长期共处。但这个结论又不全是悲观的,它也包含着一丝乐观,卡普在书中说:“(我相信)人类具有非凡的适应能力,因为他们有独特的能力,来定义那些制约我们生活的事物的意义。”
在这一章的最后,卡普引用了一段患者的话,他坦言这段话给予了他力量。这段话是这么说的,“我想抑郁让我变得更坚强。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认为我培养出了一些正常情况下无法培养的技能,我变得更加敏感,也更有同情心了。而且我开始更加努力从我的生活中找到一些意义,而不仅仅是漫无目的地走下去。在某种程度上,这抑郁是我生命意义的一部分。”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在这本书中,作者戴维·A.卡普深入采访了50名被正式诊断为抑郁症,并一直在接受相关治疗的患者,他向我们展示出一个抑郁症患者在患病过程中可能会经受的四个阶段。一开始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出了问题,但是他们缺乏词汇来描述这个问题,因此难以和人诉说自己到底怎么了。这样的一种不可沟通性让他们陷入深深的孤立之中,甚至与社会断联。然后随着他们被确诊抑郁症,他们便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奇怪,自己只是生病了,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不安和困惑。但紧接着第三个阶段,他们需要考虑是否要接受一系列的医学治疗,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第二部分中重点讲到的,他们在面对精神疾病标签和医疗手段的时候,内心的犹豫和挣扎。到最后,第四个阶段,抑郁症患者最终不得不承认,医疗上的那一套话语和手段实际也不能完全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必须直面疾痛,尝试利用一套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来解释自身的困境,并评估未来的走向。
卡普在书中极为耐心地展示了抑郁症患者患病的整个过程,并且他有意选择让患者自己来诉说,而非由他来归纳、总结、妄下论断。于是读完这本书,你可能会有一些茫然,因为你最终似乎也不知道抑郁症的成因和相应的对策是什么,但这恰恰可能才是抑郁症的关键所在,也是眼下我们需要面对的困境所在。卡普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试图描述出抑郁症背后的社会网络。他通过对这四个阶段的描述,让我们看到抑郁症的成因是复杂的,症状是复杂的,以及它的诊断和治疗也是复杂的,当中牵涉到文化、历史、心理、生理、社会等各个因素,剥离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不可能真正理解它,更别提去应对它。卡普在书中说引用了社会学家朱迪·钱柏林的一段话,她说,我们要用一个广义的视角来看待精神疾病,它不仅意味着我们的身体损坏了,它还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在某些方面也损坏了。因此,所谓的康复不仅意味着个体在生理层面的康复,它还应包括我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康复。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卡普提到,所有的抑郁症研究,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听了一大堆来自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治疗师等专家的声音,却始终听不到患者自身的声音。
-
所谓的康复不仅意味着个体在生理层面的康复,它还应包括我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