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为什么会失败》 于理解读
《规则为什么会失败》| 于理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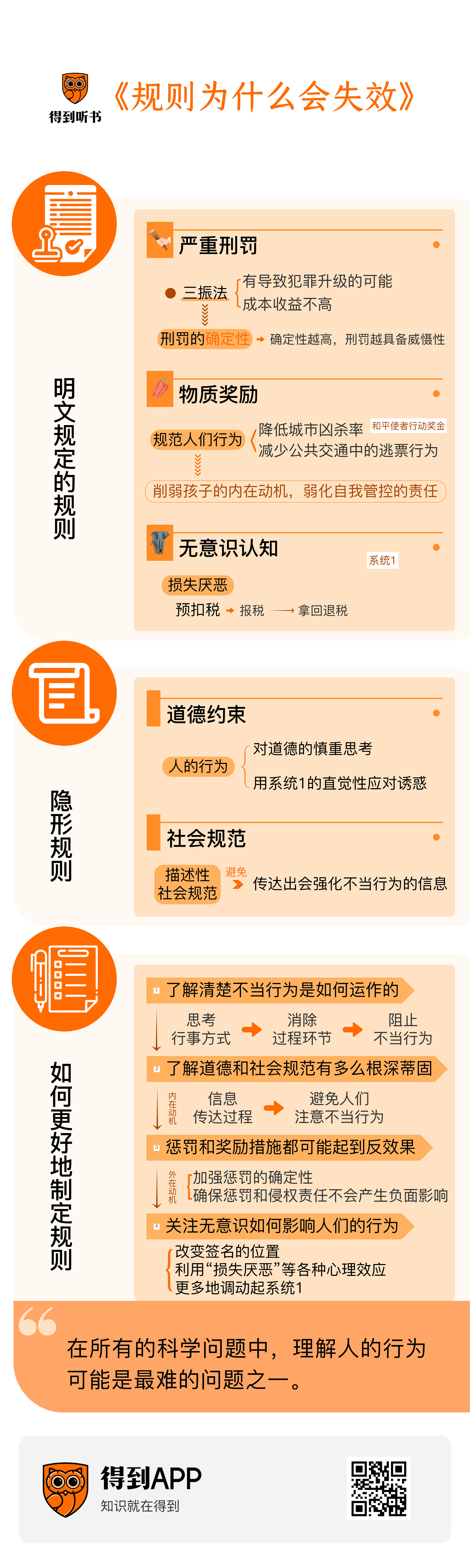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叫《规则为什么会失败》,出版于2023年10月。正如书名一样,这本书讨论的主题是,规则。
我们的社会是由各种规则构成的。坐车要系好安全带、过马路时要等绿灯亮起、按时打卡上班……小到家庭里父母给孩子定下的规矩,大到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各种规则之中。设置规则的目的是规范人的行为,但事实是,规则不是万能的,总有人冲破规则,甚至无视法律。
为什么呢?因为规则要约束人的行为,而在所有的科学问题中,理解人的行为可能是最难的问题之一。举个例子,如果我问你,如何才能更好地制定规则,减少违规行为呢?你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很可能是:惩罚。
面对不良行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进行惩罚。但是,惩罚一定管用吗?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以色列有一个港口城市叫海法,那里的日托班每天总有一些家长很晚才来接孩子,给老师添了不少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托班引入了一项新政:迟到十分钟以上的父母需要支付罚款。多数人都预测,这项新政应该能减少迟到的家长人数。结果,事实完全相反,日托班迟到的家长更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惩罚措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社会情境。在引进罚款措施之前,家长们觉得准时接孩子是应该的,迟到的家长是例外。所以,家长会督促自己准时来接孩子。但有了罚款之后,准时接孩子就从社会义务转化成了市场契约。家长没有把罚款看作惩罚,而看作了额外付费服务。他们觉得,我可以晚一点接孩子,因为我会为你的时间付费。罚款就这样变成了价格。后来,这个日托班把罚款政策给取消了。但是,迟到的家长人数还是之前的两倍。因为这个破坏已经没法恢复了,家长们已经觉得晚点来接孩子也是可以接受的了。你看,人是社会性动物,会遵循一些不成文的行为规则,也就是社会规范,它不是简单的惩罚或者激励措施就能改变的。
很多规则的制定者可能不是社会或行为科学的专家,他们依靠的是自己对人类行为的直觉,但其中很多直觉都被实证研究证明是错的。那么,如果我们想要使规则更有效,就要去研究社会科学,理解人类的行为,这也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是荷兰的法学教授,叫做本雅明·范·罗伊,他的研究领域很广,包括贿赂与腐败、逃税、食品安全、工业污染等等。另一位是美国的心理学及刑事学教授,亚当·费恩,他研究的是人违法的原因、人与法律的关系。在这本书里,作者分享了大量的案例,覆盖了欧洲、南北美洲、东亚多个国家的刑法、税法、治安法、环保法、交通法规,甚至还包括公园和地铁的规定和公益广告。你能看到,为什么有些规则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而有些规则却没有用。通过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案例,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复杂性。
接下来,我会分三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先来聊聊那些明文规定的规则是否有用;在第二部分,我们再来说说那些隐形的规则,包括道德约束和社会规范,看看这些隐形规则对我们有哪些启示;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如何更好地制定规则。
好,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这本书,来看看规则到底是怎么失败的。
我们先来聊聊那些明文规定的规则。归根结底,规则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对人的约束,分别是惩罚和奖励。我们可以用一句更生动的俗语来表达它们:胡萝卜和大棒。
大棒一定有用吗?刚刚我们讲的日托班的故事,就给了我们否定的答案,罚款这样的惩罚也不一定能改善人的行为。那如果我们推得极端一点,严厉的刑罚呢?如果刑罚足够严酷,是否能有效地约束犯罪呢?
我们来看个例子。20世纪末,为了打击各地的犯罪浪潮,美国曾出台过一个“三振法”。意思是说,如果被告人曾经犯过两次罪,又犯了第三次罪的话,那么他就要被判处25年至终身监禁,顾名思义,他要被“三振出局”了。在第三次犯罪时给予严厉刑罚,威慑罪犯不要再次犯罪,听起来很合理。但是,犯罪学家们发现,三振法出台后,它似乎并没有对罪犯起到明显的威慑作用,更糟糕的是,有一些证据表明,三振法甚至可能还增加了犯罪,特别是暴力重罪。有学者指出:“由于三振法要求对有前科的罪犯处以严厉的刑罚,那些犯过两次罪的罪犯可能会铤而走险。”对于他们来说,一旦决定要第三次犯罪,那么无论罪行如何,结果都一样,都可能是终身监禁。那既然结果都一样,为什么不干票大的?所以,第三次犯罪的罪犯可能会变得格外暴力,犯罪可能会升级。
除了有导致犯罪升级的可能性,三振法的成本收益也不高。有学者提出,由于三振法更严厉的刑罚,政府花在判决、监禁罪犯的成本高达46亿美元。如果把这个成本花在增加警力巡逻上的话,估计反而能更有效地打击犯罪。因为刑罚的威慑作用是主观的,它完全取决于犯罪者的认知。如果他低估了刑罚的确定性,那么刑罚对他的影响就会减弱。那么,如果增加巡逻警力,有犯罪企图的人能看到警察,他就会更加忌惮。此外,有学者指出,比起刑罚的严厉性,刑罚的确定性对于罪犯更有威慑作用。刑罚的确定性越高,犯罪者越容易被抓、被起诉、被定罪,刑罚就越具备威慑性。除了刑罚,另外一类大棒——侵权责任也是如此。比起侵权的赔偿金额大小,确保必须给予受害者损害赔偿,可能会更有效地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
除了惩罚的“大棒”之外,我们还会使用“胡萝卜”,用物质奖励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有一个用胡萝卜代替大棒的经典社会实验。美国旧金山地区有一座小城市叫里士满,那里的凶杀率是全美第一,每10万居民中每年都会发生46起谋杀案。2010年的时候,该市的社区安全办公室邀请了25名年轻人来到市政厅,这些年轻人都是一些有过犯罪记录的危险人物。社区安全办公室的主席告诉这些年轻人:这座城市的和平要靠他们。还给了他们每人一千美元的现金。如果这些年轻人能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比如找到更好的住房、停止滥用药物、考取驾照或者支付拖欠的罚单,市政府还会给他们更多钱。这项计划被称为“和平使者行动奖金”。计划实施后的7年里,该市的凶杀率下降了50%还多。
这么看,胡萝卜似乎确实有用。不过,这个项目的成就也不只是靠现金奖励,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一项目还为那些犯罪青年提供了他们从未得到过的关怀和关注,表现比较好的人甚至会被带去迪士尼乐园等地方旅行。这些年轻人也看到,在他们充满暴力的成长环境之外,还有着诸多积极的可能性。
提供奖励,还能减少公共交通中的逃票行为。意大利有一个度假胜地叫里米尼,有些不太自觉的乘客,经常不付钱乘坐公交车。于是,公交公司安排了一些查票员随机查票,但这招也不管用,于是公交公司不得不求助于研究人员。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在一些公交车上贴了海报,告知乘客,购买公交车票就有机会中奖,奖金高达500欧元。接着,研究人员比较了有奖巴士和普通巴士分别卖出了多少票。结果显示,有奖巴士多卖出了30%的车票,这说明逃票现象大大减少,这一奖励措施的效果可以说非常不错。
胡萝卜确实可以减少不良行为,但它依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它可能会削弱人的内在动机。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小红花奖励,能让孩子遵守纪律、帮助同学。但是,面对这样的外在奖励,孩子会不会专注于满足给他奖励的大人,而不是事情本身呢?我不是为了同学好才这样做,我只是想要那张贴纸。因此,奖励措施可能会降低孩子的内在动机,弱化他们自我管控的责任。
刚刚,我们聊了生活中的那些奖惩措施。我们能看到,虽然我们在看到不良行为时,第一反应总是拿出大棒,但过于严厉的惩罚也可能会适得其反,比起惩罚的严重性,惩罚的确定性可能更加重要;当大棒失效时,我们也可以拿出胡萝卜,用奖励来规范人的行为。胡萝卜可能会改善人的行为,但这种方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无论是大棒还是胡萝卜,我们刚刚的讨论都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决定守不守规矩,都是理性思考后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候,人们是在无意识中做出了某种行为。
伦敦商学院有一位老师叫做丽莎·舒,她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填写的很多保证书或者表格,比如税表或保险表格,签名的位置都在纸张的底部。也就是说,人们大都是在填完表后才签字的,目的是证明我们保证上面所填的内容是事实。那么,如果我们改变签名的位置呢?把签名的位置放在开头,人们的诚信程度是否会有变化呢?
丽莎·舒的团队对一个汽车保险产品进行了实验,这一保险要求员工在每年年底上报各自的总里程。实验结果发现,在表格顶部签名的人报告的里程数要远高于在底部签名的人。在顶部签名的人比在底部签名的人表现得更诚实。这一结果表明,仅仅是改变签名的位置,没有额外成本,也不需要更严格的执法,就能大大减少虚报。
原因是什么呢?丽莎·舒认为,在填表前先签下自己的名字,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然后我们就会变得更加真诚。但我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这是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结果。在丹尼尔·卡尼曼的著作《思考,快与慢》中,他指出人脑使用两个系统,分别是系统1和系统2。系统1是“快思考”系统,它凭直觉和经验自主运行,为我们迅速地做出各种日常决定,也因此经常出错;系统2则是“慢思考”系统,它更审慎,也要花费更多脑力。有心理学家用骑象人来比喻人的思维方式,系统1就是一头大象,它遵从本能,也就是自主运行的无意识认知;系统2则是骑象人,它用有意识的认知来引导大象。问题在于,我们很多决定和行为都是这头大象自己做出的。
于是,矛盾就产生了。很多规则的前提,是人们会理性地权衡各种激励和惩罚措施,人们的行为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时候,人跟随的是自己那容易出错的直觉。那么,如果想要更好地制定规则,我们就要学会和头脑中的大象对话。
如今,其实已经有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学者们想知道,有没有对系统1同样有效的激励或者惩罚措施。比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给你提供两个选项,一个选项是能得到一千元人民币,另一个选项是有80%的机会赢得2000元,但有20%的机会什么也得不到,你会选择哪一种?多数人可能会选择只拿走那一千元。这是因为,我们有一种躲避损失的本能,它的学名叫“损失厌恶”。多数情况下,我们对损失的恐惧会超过对收益的渴望。在这种本能的驱使下,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去仔细地计算各个选项的利弊得失、概率几何,而是直接选择那个规避损失的选项。
那么,我们能怎样利用“损失厌恶”来制定规则呢?来看看税务部门是怎么做的。如果你发现税务局欠你钱,你会有什么感觉?应该挺开心的,然后你估计会很快完成报税。但如果你发现你欠税务局的钱呢?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一遍遍地检查,看看是怎么回事。还有人可能会试图想办法降低自己所欠的金额,毕竟如果有可能损失金钱,就有人会倾向于弄虚作假。税务部门肯定也很清楚人们的这一心理。那么,如果税务部门在人们收到薪水之前直接从中自动扣除高于实际应付额的税款,也就是所谓的预扣税,人们就从报税变成了拿回退税。报得越好,拿回的退款就越多,人们就更愿意遵守规则了。瑞典就曾展开过一项针对360万瑞典人的纳税情况研究,结论是:“如果预扣税额调整到大部分纳税人都需要退税的水平,那么人们就更愿意依法纳税,收税审计成本也会降低。”你看,学会和大象对话,我们就可能创造出更有效的规则。
到这里,我们逐渐意识到了人类行为和认知的复杂程度,简单的胡萝卜或者大棒不一定能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当然,在胡萝卜、大棒还有大象之外,人类的行为还会被一些更隐蔽的力量所影响,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
有一位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心理学家曾在芝加哥组织过一项大型研究,研究的是芝加哥人遵守法律的原因。他发现,在人们遵守规则的理由构成中,最重要的不是对惩罚的恐惧,而是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某条规则和人们的道德观越一致,人们就越会遵守规则。如果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推行禁烟令,估计没多少人会遵守,因为当时很少有人会认为在公共场合吸烟是不道德的。等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已经认为吸烟是有害的,并且在道德上支持禁烟的规则。这时,美国大多数州都实行了禁烟令,效果就很好。
不过,人的行为并不总是能被道德约束住。有时候,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有研究者曾做过一项有趣的实验,实验要求参与者掷骰子并且自报点数,点数是4的话就可以赢得金钱奖励。当然,参与者可以撒谎。这里还有一个设计,那就是研究人员把参与者分成了两组,一组用母语完成实验,另一组使用外语。随后,他们会评估每组参与者总体上报告的掷骰子结果,看看这在统计上是否可能,以此来比较母语组和外语组的诚实程度。结果发现,当参与者用母语参与实验时,比用外语更容易撒谎。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为了个人利益而撒谎,是系统1的一种直觉性反应。而当参与者使用外语时,会更多地激活系统2,也就是慢思考系统,系统1就受到了抑制,于是参与者就会更慎重,更少出现作弊行为。
系统1可能会让人更不道德,因为它要求我们用直觉来应对诱惑。许多其他研究也发现,当人们更多地使用系统1时,更可能做出道德有亏的行为。比如,有研究发现,一夜没睡的人道德意识较低,他们对行为的道德判断能力也比较低。这是因为他们的大脑非常疲惫,没有那么多的脑力调动系统2。还有一项名为“诚实星期一”的研究也发现,和周一相比,人们在周五的时候更容易不诚实。
总之,人的行为不是简单的无关道德的理性选择,但也不是无关道德的非理性选择,它关系到人们对道德的慎重思考,也有系统1的直觉性应对。在道德规范之外,还有一类隐蔽的行为规则是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理解人类行为、理解人类为什么违反规则的关键。还记得我们在开头讲的那个日托班的故事吗?它就说明了理解社会规范对于制定规则有多重要。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行为影响力研究的权威罗伯特·恰尔迪尼曾着手研究美国的一项重大环境问题:如何减少美国家庭的能源消耗。研究团队在郊区近300所房屋的大门上挂了宣传节能的传单,传单共四种,信息分别可以概括为:一、节能对环境有益;二、节能有利于社会;三、节能可以省钱;四、节能很常见。你可以猜猜看,哪一类信息的效果最好?
答案是第四条:节能很常见。研究团队测量了每个家庭在收到信息后两周内的能源使用数据,他们发现,收到第四条信息的家庭大大减少了能耗,即使是过往最浪费的用户也是如此。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第四条信息触发了一种社会规范:“描述性社会规范”,它告诉我们别人都怎么做。在听说别人都这样做后,我们就会有意无意地以同样的方式行事。
总之,对于人的行为,社会规范是一种强大的影响因素。当人们看到多数人在做正确的事情时,自己也会这样做。不过,看不到别人正在做错误的事情,也很重要。
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有一个石化森林国家公园。两亿多年前,这里倒下的树木被一层又一层的火山灰等沉积物覆盖,这些木材如今石化成了紫水晶、黄水晶等宝石。这些石化木吸引了每年50多万的游客,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小偷。几十年来,公园的管理部门想出了各种办法阻止游客偷窃这些化石。他们试过罚款,也试过在公园出口检查,还竖起过大型警告牌,甚至还张贴过小偷的悔过书,但是都没有用。有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想帮帮公园的管理部门,他制作了两种标牌,一张标牌上张贴了三个人偷石化木的照片,另一张标牌上是只有一个人在偷石化木的照片。他分别在公园里竖起了这两种标牌,然后等着看有多少石化木被盗。结果,两种标牌的效果差异很大。当标牌上只显示了一个小偷,人们只会偷一点石化木;但如果标牌上是三个小偷,人们偷的石化木几乎多了五倍。仅仅是改变标牌上的人数,就极大改变了被偷窃的石化木的数量。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细微的信息变化也可能会助长不当行为。三个小偷的标牌,向人们传达的是偷盗行为司空见惯,这触发了负面的社会规范,导致了更多的偷盗行为。公园管理部门的大型警告牌、张贴的小偷悔过书,都是让更多人知道,这种盗窃行为一直在发生,那么这就说明,石化木可以被偷、经常被偷,而且被偷的量很大。很多时候,规则的制定者想要减少不良行为,反而触发了负面的社会规范,导致不良行为变得更常见。
所以,制定规则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避免传达出某些会强化这类不当行为的信息。再举个例子,为了规范纽约地铁乘客文明乘车,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制作了很多标牌。有一种标牌针对的是一些叉开腿坐着的乘客,这类乘客总是把腿大大咧咧地向两边分开,挤占了旁边乘客的落座空间。这类标牌上面写的是:“哥们儿,别叉腿。”但是,引入这类标牌后,这类行为依然很常见,根本没能得到改善。这是为什么呢?
最直接的答案是,这些标语想要制止的负面社会规范过于强大。如果只有几个人违反规则,那么这类标语可能有用。但如果大多数人都经常性地违反规则,那么增设标语就没什么用处了。在地铁里,叉开腿坐的人司空见惯,这产生了强大的负面社会规范。看到这个标语的人不会想“我最好把腿并拢”,而是“如果其他人都叉腿坐,为什么我不能也舒舒服服地坐着?”放置标牌,制止违规行为,这符合我们的直觉。但标牌也可能只是提醒了人们规则在被破坏,它甚至还会提醒那些违规的人这类行为有多常见,结果反而可能削弱规则的力量。
好了,到这里,我们聊了不少规则会失败的原因,还有头脑中的大象、道德约束、社会规范等人类行为规律。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行为,更好地制定规则呢?在书里,作者给了我们一些提示。
首先,规则的制定者要先了解清楚这些不当行为是如何运作的。比起先思考行事原因,不如先思考他们的行事方式。通过分析不当行为的执行方式,我们或许能想办法消除过程中的某个环节,从而阻止不当行为。这样是最简单直接的,我们甚至不用去引导动机。比如,我们现在乘坐飞机时是不能携带大量液体、喷雾或胶体登机的,这类规定其实源于一次幸免的恐怖袭击。2006年的时候,英国警方发现有一伙恐怖分子打算携带液体炸药登上飞机,于是英国各航空公司都接到电话,暂时禁止一切随身行李登机,乘客只能随身携带钱包。在当时,这一规定几乎导致伦敦希思罗机场停摆。在这一事件之后,全球各地机场的登机规定里,几乎都增加了一条“禁止携带大量液体登机”的规定。这一规定本身非常简单,但它从根本上成功地增加了实施袭击的难度。因此,这是一条非常简洁、有效的规则。
其次,在内在动机方面,制定者需要了解和不当行为有关的道德与社会规范有多么根深蒂固。如果不当行为在现行的道德或社会规范中植根很深,那么在信息的传达过程中,就要避免人们注意到这一点,就比如我们说的那个石化木的例子。但如果不当行为没有根植于现有道德和社会规范的话,那么干预措施就可以去利用这些积极的道德和规范。
在外在动机方面,规则的制定者需要知道,惩罚和奖励措施都有起到反效果的可能。加强惩罚的严厉性,不如加强惩罚的确定性。此外,我们还要确保惩罚和侵权责任不会产生意外的负面影响,像是过于严厉导致人们“破罐子破摔”,或者破坏了人们的内在动机。
最后,我们还可以多多利用起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关注无意识如何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比如改变签名的位置,利用起人们的“损失厌恶”等各种心理效应,以及更多地调动起人们的系统1等等。
好了,以上,就是这本书里我想和你分享的主要内容。在这本书里,作者讨论了各种规则失败的原因,从法律法规到地铁上的文明标语,那些失败的规则背后,是复杂的人类行为。其实,在这本书里,作者在字里行间经常传达出一种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关于“惩罚”的那一章节中,作者写得最多的句子,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比如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某种惩罚一定有效,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侵权责任能减少损害行为。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作为法学教授的严谨,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印证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在生活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规则的遵循者,也是规则的制定者。了解一些社会科学的知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更好地理解人性,也制定出更有效的规则。
好了,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要是你喜欢这本书,也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人的行为不是简单的无关道德的理性选择,但也不是无关道德的非理性选择,它关系到人们对道德的慎重思考,也有系统1的直觉性应对。
2、很多时候,规则的制定者想要减少不良行为,反而触发了负面的社会规范,导致不良行为变得更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