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了不起》 杨以赛解读
《每个人都了不起》| 杨以赛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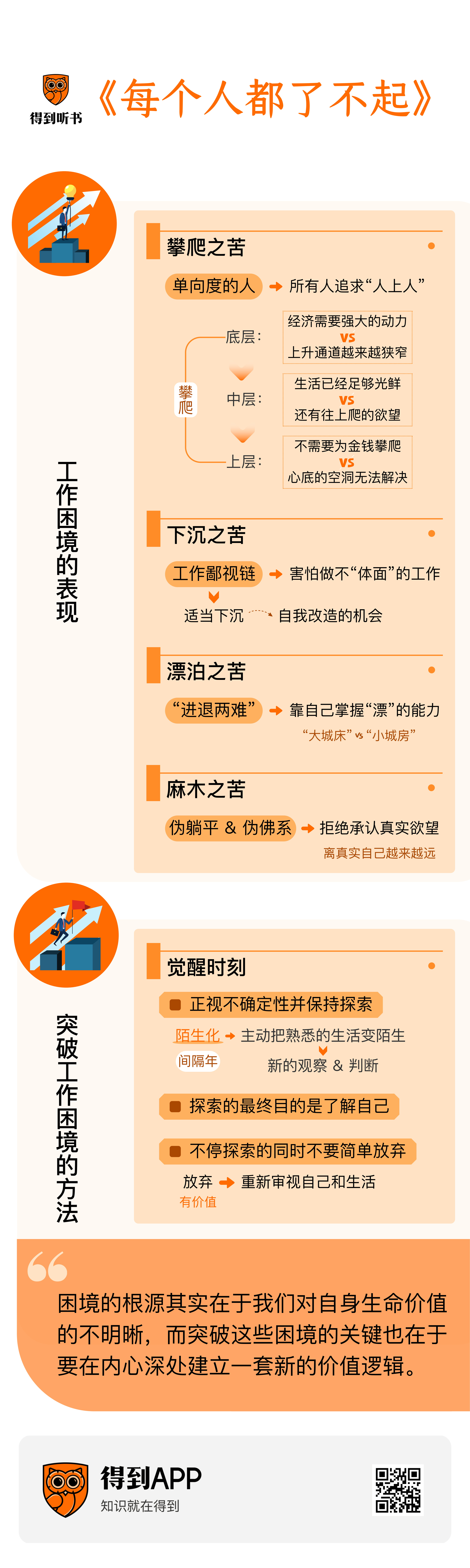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每个人都了不起》,这是一本讨论当下工作困境的书。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人生的1/3可能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我们为工作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能量,也在工作中体现和收获我们的生命价值。但工作显然不是一件易事,尤其在当下,“内卷”“躺平”“佛系”“打工人”“做题家”等词汇层出不穷,它显现的正是人们在工作中越来越深的困境。工作为什么让我们疲惫,我们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以及我们又该如何突破这些困境,今天的这本书试图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梁教授研究比较文学和电影,同时关注城市文化和青年文化,曾被评为复旦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视频博主,因讲解的内容既有理论深度,又能紧密联系当下生活,而受到大量追捧。这本《每个人都了不起》是梁永安在2023年8月出版的一本新书,他在序言中介绍说,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就是年轻人如何突破工作中的困境,“如何以创造性的现代思维和在空白处创新的勇气,找到自己喜欢同时又有时代价值的事。”
这本书的书名“每个人都了不起”,出自梁永安在高铁站偶然看到的一句标语,他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是了不起的。这个了不起不在于你做成了多大的事,而在于你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人。他说:“人不是按照外在的、阶层的尺度生活,而是应该有属于自己生命的成长尺度。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没有荒芜的土地,只有荒芜的人。你怎样活成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人,这才是最根本的。”
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将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讲讲工作中究竟有哪些“痛点”,它们源于什么。第二部分,我们来讨论到底要如何突破工作中的困境,找到自身的成长尺度。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很多人在工作中感到疲倦、焦虑、迷茫,但当问及你到底因为什么疲倦、焦虑和迷茫的时候,却又往往答不上来。弄明白这些感受从何而来非常重要,如梁永安在书中说,“对处于任何社会阶段的年轻人来说,意识上的明亮度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明白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以及到底能做什么。
梁永安在书中为我们一一盘点了多个工作中的“痛点”,他最先讲到了工作中的“攀爬之苦”。这不难理解,巴尔扎克有本小说叫做《幻灭》,讲的是一个人从外省来到巴黎,奋斗半生,却终成一场幻灭,城市并没给他提供什么通道,相反这里很多东西都在打压他,苦不堪言,这就是梁永安所谓的“攀爬之苦”。
对很多人来说,这种苦几乎是一种必然。著名的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一个社会在要进入发达阶段却还没有进入的时候是最难的。一方面经济需要强大的动力往前走,另一方面上升的通道却又越来越狭窄。反映到个体的身上,就是向上爬变得越来越难,可你又不得不向上爬。
这不仅是底层需要面对的,其实中层,甚至是上层也在经受这种苦。梁永安在书中分析说,对社会中层的人来说,一方面要担心掉下去,另一方面在生活已经足够光鲜的情况下,又还有往上爬的欲望。梁永安在书中提到他的一些做金融的朋友,他们住在一百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但眼里还在关注着那些住170平方米和230平方米房子的人,于是目标就一直是再多挣点钱。而对上层阶级来说,看似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可心底的空洞却不一定解决。比如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写的是一个暴发户,他从山区奋斗到了首都,到首都后他唯一的目标是把女儿嫁入到上流社会,因为他觉得其他有钱人看不起他。他可以不再为金钱攀爬,但又开始为名望攀爬。
在这样一种所有人都在向上攀爬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单向度的人”。这个词是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提出来的,简单讲就是人变得只知道功利性,只往一条道路上走,所有人都在追求“人上人”,但到底什么才是“人上人”,以及“人上人”有什么好,又说不上来。其实,攀爬并没有错,但你得要明白你到底在为什么而攀爬,你自己的生命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个不明白,只是为爬而爬,那这种苦就没有任何意义。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话很直接、很不留情面,他说这种人归根结底是个奴隶。
与“攀爬之苦”相对的是“下沉之苦”,其实工作除了有钱多钱少之分,还有体面与不体面之分。在社会学领域有一本很著名的著作叫做《学做工》,里面说社会把工作分为脑力活和体力活,然后我们总是推崇脑力活,贬低体力活,认为体力活是不体面的。梁永安说的“下沉之苦”,是说很多人困在这样一种所谓“工作鄙视链”中,害怕自己做一份世俗意义上不体面的工作。
他在书中提到了自己收到的一条留言,一位网友跟他说,自己在一家外企上班,待遇很不错,但却一直不是很开心,她从小想做一名舞蹈演员,现在也还是很想去健身房做一个舞蹈老师,可心里又觉得这很掉价,所以很纠结。梁永安就此说:“我看到这条留言非常感慨,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环境给人造成的艰难。”
梁永安提到一个叫做“身体技术”的理论,它是法国思想家莫斯提出来的,是说你如何支配自己的身体,其实取决于你所属的文化圈,也就是你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可避免会形成一些定见,而这些定见决定了你做出的选择。这件事不可避免,但当我们的定见让我们感觉到痛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审视一下这些定见呢?尝试一下跳出这些定见看世界呢?
梁永安在书中讲到他最佩服的一位美国摄影师薇薇安·迈尔,她是一位很杰出的摄影师,但却一辈子甘愿做保姆。为什么?因为这个身份让她可以不停转换环境,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同时也让她可以不动声色地靠近人,由此捕捉到那些最本色的照片。梁永安说薇薇安证明了职业的好与坏、体面与不体面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定义,所以说“对于下沉的担心实际是一种多虑,这是我们某种脆弱的表现,一个内心不坚定的人,才需要依靠别人的眼光来确定自己。”
梁永安甚至觉得一个年轻人适当下沉其实是好事,这是一次自我改造的机会。梁永安说,他向来认为人会出生两次,第一次是父母给你生命,第二次是精神出生,其实也就是你的自我出生,第一次出生是你自己不能决定的,但第二次却是你可以决定的。这件事不容易,过程充满了考验,比如是否坦然面对“下沉”可能就是其中一个考验,它要求你与自身,以及与社会的习见和偏见做斗争,一旦你经受住了这些考验,你就有机会创造出一个属于你的自我。
好,讲完“攀爬之苦”和“下沉之苦”,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漂泊之苦”。中国很早就有“游子”一说,我们也都能背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句诗,但梁永安在这本书中说,中国大规模的“漂泊之苦”实际是很晚近才出现的,至少比西方晚了几百年。为什么这么说呢?西方从1492年哥伦布出航,开辟大航海时代开始,人群就开始迅速流动了,进入工业化社会,这种流动又进一步加速,最终可以说人人都处在了漂泊之中。但中国在很长时期都处于农业社会,历史学上将之称为“超稳定社会”,漂泊实际是少数人在经受的。要一直到工业化社会后,人群才开始逐渐流动起来,而这其实也就近百年来的事。在眼下中国,最常见的情形是我们的上一代还生活在相对稳定的生活中,但下一代却被极速推向了漂泊大潮,这也让我们的“漂泊之苦”显得尤为剧烈。
“漂泊之苦”到底苦在哪儿,其实不单单是苦在“出门在外”,它还苦在“退不回去”,用梁永安在书中的话说,“进退两难最折磨人”。眼下大量的人群从乡村流入城市。进城的农民并非不能回去,他们在农村仍然有地有房子,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在城市过得那么艰苦呢?一方面当然因为城市收入高,但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已经习惯城市丰富的生活,难以再退回去了。也不单单是农民,很多人都在经受这样的“进退两难”,这也是为什么关于“大城床”和“小城房”这个问题会被一遍又一遍地被讨论,它没有标准答案,它显现的其实就是我们在这种两难中的困惑和焦虑。
此外,梁永安还在书中指出说,年轻一代最是能感受到这种漂泊之苦的,因为他们没有上一代的示范,几乎什么依据都没有,他们要完全靠自己去掌握“漂”的能力。梁永安说他在纽约的时候,被纽约城里人与人之间传递话语、传递感情的能力惊讶到,这是现代城市生活培养出来的非常好的能力。但这不是一时形成的,这是好多代人接力之下才逐渐形成的,但眼下的我们却是在一点准备都没有的情况下,蒙头流向城市,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当然,像“攀爬之苦”“下沉之苦”“漂泊之苦”,似乎都可以借助时间去习惯和适应,但还有一种苦,是时间无法撼动的,那就是“麻木之苦”。梁永安在书中引用了一位青年朋友跟他的对话,这位青年朋友说,自己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充满着激情和动力,但现在彻底“佛系”了,好像怎么生活都无所谓,怎么着都可以,感觉生活轻松一点,但心里又有点空虚,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在梁永安看来,这就是所谓“麻木之苦”。
很多人会脱口而出“佛系”“躺平”这类词,但梁永安觉得很多人其实只是“伪佛系”和“伪躺平”,他们并不是没有愿望,而是达不到自己的要求,于是用“佛系”“躺平”这类词语来欺骗自己,好像自己真不在乎了,但其实只要这时有一个实现愿望的机会,他可能立马就不佛系了。在梁永安看来,这种“伪佛系”和“伪躺平”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层的麻木,它意味着拒绝承认自己真实的欲望,还给它打上了一个“美丽”的标签。长此以往下来,它会让我们离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
梁永安在书中提到《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楚门这个年轻人每天上班,活得很开心,但最后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是演出来的,他周边所有人都在欺骗他,他的生活全是布置好的场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其实很多的条条框框也是人为设定的,而我们给自己打上的种种标签也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设定,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构成了一种布景。梁永安说:“有很多人就这样在空洞无物的生活中奔波忙碌着,一辈子也走不出这个布景。”
那讲了那么多困境,我们又该如何突破呢?在这本书中,梁永安在每一节的最后都以“觉醒时刻”为题,讲了讲他的一些看法。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就来听听他的看法。
其实,前面我们讲到的所有的苦,在梁永安看来都源于对于价值的不明晰。很多人要么是找不到自身的价值,要么则是忙忙碌碌地服务于别人的价值。因此想要打破工作的困境,靠换一份工作或换一个环境是不足够的,它需要我们在内心深处建立一套新的价值逻辑。
而这第一步是要放弃原来的生存理念,投入未知的不确定的生活中。在梁永安看来,我们内心很多的成见、定见,其实都来源于我们对确定性的依赖,但实际上这个世界并没那么确定,它充满了随机性、非线性、偶然性,甚至是荒诞性。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有一本著名小说叫作《小径分叉的花园》,“得到听书”此前解读过,它核心讲的就是这个世界布满了分叉的小径,有无数种可能,你根本不知道你会通向何方。具体来说,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内容,再过5年、10年会变成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能再执着于用一套旧有的逻辑去审视和规划我们的未来,而是要正视不确定性,并在不确定性中保持探索。
这说来容易,具体要怎么做呢?梁永安在书中提到戏剧学家布莱希特的一个理论,叫做“陌生化”,简单讲就是主动把熟悉的生活变陌生,然后产生新的观察,做出新的判断。布莱希特在排戏的时候运用这个理论,他从不在舞台搭设实景,用一个圆就代表了月亮和太阳,他还让演员的动作有意与真实生活拉开一点距离,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观众一方面欣赏强烈的戏剧冲突,另一方面又不会完全沉浸其中,他们知道自己在看戏,所以能够保持思考。在梁永安看来,这个理论不仅是一个好的戏剧理论,它其实也是一种生活哲学,看戏可以陌生化,那我们的生活何尝不可呢?我们可以试试跟我们的生活拉开一点距离,用一种陌生的眼光审视它,说不定会看到一些新的东西。
西方社会的年轻人间流行“间隔年(Gap Year)”,它指的是在升学或工作前进行一次长期旅行,体验跟自己生活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其实就是一种“陌生化”的策略。当我们能够去一些更远、更陌生的地方,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原来的生活有多狭窄,才会知道世界的宽广,然后也才会明白世界在变动,自我也需要变动。
但梁永安也在书中提到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开展“间隔年”,更多的人要学会的是“就地陌生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场景,家庭、学习、工作、娱乐等等,梁永安说我们可以以一个参与者的角色深入这些场景,但我们也可以以观察者或者旅行者的角色深入其中。比如就拿工作来说,参与者可能只会想着工作内容,但一个观察者和旅行者则会把工作看作是一个好玩的课题,当中不仅有工作内容,也有丰富的人和人的互动、企业和社会的互动,以及它和技术发展、文化发展的互动。如果你能开启对这些东西的观察,那工作就不仅只是为绩效服务了,它也为我们探索和创造自我服务,这样的话说不定它就没那么苦了。
梁永安还特别讲到说,上海这个城市有多达7000家咖啡馆,它们是上海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咖啡馆,人们在这些咖啡馆里只是为了喝一杯咖啡吗?梁永安觉得并不止于此,他认为咖啡馆是人类文明巨大进步的体现,不同阶层的人只要买一杯咖啡就可以自由坐在这里,它打破了传统社会贵族沙龙的门槛。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生活的人在这里相遇、交际,最终构成了一副极具多元性的景观。从这个层面来讲,像咖啡馆这样的公共空间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探索自我的场所,你会不断地见识到新的人,也不断被新的文化震动,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认识自己。
不过,关于对自我和生活“探索”,其实也有一些亟待厘清的误区。比如我们不断讲要探索新的价值逻辑,那这是说原来的逻辑就完全是不对的吗?其实不是的,梁永安在书中指出,抱持着“对错之分”的探索并不是一种好的探索,探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了解自己,了解自己适合什么,又需要什么。她举到了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小说《都柏林人》,当中讲到一个想要打破原来生活的女孩,她决定跟一个小伙子私奔,结果到了码头发现自己过不去那个栏杆,身体本能地不动了,最后她很沮丧地回到了她原来的生活中。你能就此说她对于她生活的探索失败了吗?梁永安觉得说不是,因为这个女孩跟私奔前的自己完全不一样了,她在这个过程中更了解自己了,也因此活得更明白了,尽管她的生活一成不变,但她的探索仍然是有意义的。
另外,有很多主张探索的人,他们也是一些很容易放弃的人。因为探索似乎意味着要不断尝试、不断转向,因此免不了要不断放弃。但梁永安在这本书中却指出,我们要不停探索,但同时我们不要那么简单放弃。梁永安说,放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批判思维,是对原来的生活的否定。但这个否定应该建立在你对原来的东西足够了解,有足够深的体会之上,否则这个否定就很轻率。所以,当我们想要放弃的时候,我们应该先问自己我们为何放弃,放弃之后又要追求什么?这是一种逃避吗,还是一种游戏,我们是非放弃不可了吗?借由放弃来重新审视自己和生活,这才是有价值的放弃。
好,讲了那么多“探索”,梁永安几乎在这本书的每一节中都在倡导年轻人要不断探索自己和探索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自己的价值逻辑。一个有自己的价值逻辑的人,便能时刻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不会在“攀爬”“下沉”“漂泊”与“麻木”中乱了阵脚。但“探索”也有“探索”的风险,它意味着你可能会走上一条从没有人走过、迷雾重重的道路,这条道路也许能带你逃脱开一些以往生活中的苦痛,但这条道路本身也是很难走的,甚至可能是煎熬的。梁永安在这本书中鼓励我们要敢于承受这份煎熬。他提到法国雕塑家罗丹,他最著名的雕塑作品是《思想者》,但梁永安更喜欢他另一个雕塑,叫《青铜时代》,是一个人从原始森林里走出来,阳光太刺眼,他举起手遮挡,然后眺望远方,有点迷茫,但又充满向往。在梁永安看来,这是探索者的样子。
梁永安说,任何有深度的生活都必定有煎熬。他提到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讲到人成才有两条路,一条是积学,也就是老老实实一点点学,另一条是顿悟。梁永安认为这两条路并不矛盾,积学到一定程度,可能就会有恍然一下的顿悟。你得要在煎熬中不断磨炼你的意志、品质、智慧和情感深度,才能最终促成那个顿悟。
梁永安特地在书中讲到了一段他小时候的经历。他有一次一个人去远方,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隧道。天色将晚,走到隧道前他就有些紧张了,但不通过隧道又不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隧道里黑咕隆咚的,隔很长一段才挂一盏灯。那时候他才九岁,就这么摸黑往前走,中途还有火车穿进来,呼啸而过,把他吓得不行。他走了10多分钟,才看到远处有亮光的隧道口,最后终于走到了光亮处。梁永安在书中写道:“人生总有一个隧道时期,有这样一个一开始有点煎熬,看不见前路,后来慢慢豁然开朗的短暂时期。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特别大。尽管那时候我很小,但是我们明白了一点,人生有时候就是要经过一个隧道,一定要有勇气去穿过它。”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梁永安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梳理了当下工作中的种种困境。在第一部分我们集中谈到了围绕单一价值体系、一刻不停竞争的“攀爬之苦”,在意工作体面与否、为了世俗意义上的体面而回避心之所向的“下沉之苦”,在故乡与外地之间进退两难的“漂泊之苦”,以及丧失激情与动力,并以一种自我欺骗的方式回避真实世界与真实欲望的“麻木之苦”。在梁永安看来,这些困境的根源其实在于我们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不明晰,而突破这些困境的关键也在于要在内心深处建立一套新的价值逻辑。
价值是多元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每个人特定的价值逻辑,我们无法贯彻他人的逻辑。因此梁永安在书中反复提及“探索”二字,他鼓励人们要敢于承认和接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并在其中保持探索。在第二部分,我们讲到的便是梁永安对于探索的思考。他提到“陌生化”的概念,鼓励人们以一种陌生的眼光审视自己的生活和世界,从而看到新的可能性和价值。同时他强调,探索的道路必然荆棘密布,它甚至可能比以往的老路更难走,但一个坚定走在自己道路上,能够按照自己价值尺度生活的人,一定是一个更开心和更了不起的人。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是了不起的。这个了不起不在于你做成了多大的事,而在于你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人。
-
困境的根源其实在于我们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不明晰,而突破这些困境的关键也在于要在内心深处建立一套新的价值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