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社会》 游识猷解读
《心智社会》| 游识猷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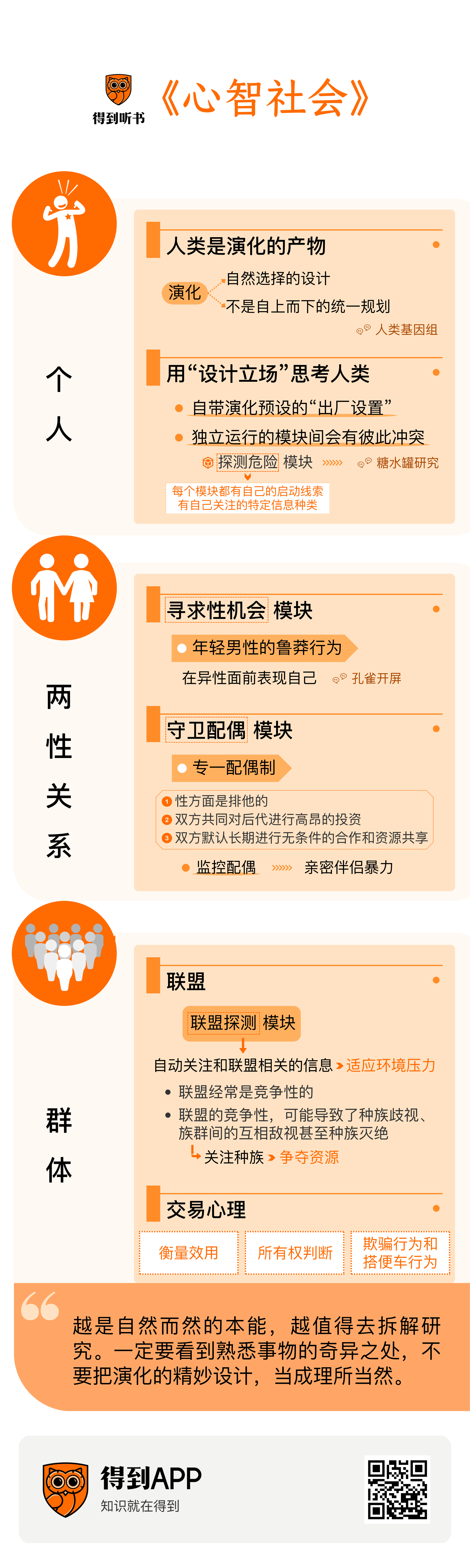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来到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心智社会》,副标题叫“我们的认识决定了我们的世界”。
这个书名是作者原书名的直译。说实话,这个原书名实在太过低调了,按照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也许可以叫做《颠覆你对人性的认识》,或者《不要把人当人看,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甚至来个网红体,叫《震惊!所有人本质都是双重标准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要从本书作者帕斯卡尔·博耶谈起。他现在的身份,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教授,是个“跨界”的科学家,既是演化心理学家,又是人类学家。博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进化心理学与人类的认知形成与发展,可以说是演化心理学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并在2021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截至目前,博耶的学术著作已经被引用了两万多次,和另一个网红心理学教授乔丹·彼得森的引用量差不多 。
如果光看目录,你会觉得这本《心智社会》,简直就是一部关于人类意识与行为决策的百科全书,内容无所不包,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群体之间的冲突、婚姻与家庭的起源,以及宗教为什么长期存在等等复杂问题。要想读懂这本宏大而庞杂的专著,就必须有一个抓手,或者核心知识点与方法论。在我个人看来,博耶这本书最值得记住的一个知识点就是,不要把人当一个整体的人看;用书里头的术语来说,就叫做,不要把人“人格化”。
听到这里你肯定糊涂了,不把人当一个整体看,那该怎么看?要把人拆成零零碎碎的器官来看吗?
感到别扭也不奇怪,毕竟我们长久以来都习惯了把人当做一个统一、不可分割的实体。打个比方,我们看到一个人端起一杯茶喝,就会认为这个人肯定是喜欢喝茶,或者他有什么目的所以做出了喝茶的举动。在这个推理过程中,我们一直把他视为一个整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人之所以喝茶,是因为他的口腔和喉咙感受到黏膜没有足够水分了,肾脏觉得无法正常过滤血液来产生尿液所以发出了警告,于是,他的大脑,就向手臂和手指发出了神经信号了:端起那杯茶,喝下去!
在博耶看来,这种“化整为零”的思路,才会让我们更接近,人的行为决策背后的底层逻辑与真相。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把人当成一个整体,如果你认为人是评估了所有的信息和想法,然后产生明确的行为动机,最后才有意识有计划地发起行动,那你就没法解释人类很多稀奇古怪的心理和行为。
《心智社会》这本书,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把人看作一个复杂系统,这个复杂系统可以被拆成很多个独立运行的模块。每个模块都有特定功能,负责获取环境里的特定信息,然后做出直觉推理。你必须逐个审视,每一个模块都干了什么,又如何影响了整个复杂系统的运行。
接下来,我就分三个部分,为你大致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为了让叙述具有一条鲜明的逻辑线索,我特地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也就是说,由简入繁,分别从个人、家庭、小团体和大市场三个量级,来为大家解读作者博耶对于人类思维和决策底层逻辑,以及演化过程的分析。
首先,让我们从单个的人说起。
把人当成一个整体,用信念和意图来描述人的行为,这种思考方式叫“意图立场”;而把人拆成很多模块,研究哪些模块影响了人的行为,这些模块之间又如何协作互动,这种思考方式叫“设计立场”。
博耶强调说,要想深刻地洞察人性,了解人类思维和决策偏好模式的来历,就必须从“意图立场”,转为“设计立场”。
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是演化出来的产物。我们的偏好、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侦测系统去接收哪些信号,归根结底都是自然选择“设计”出来的。举个例子,为什么狗是红绿色盲 ,但人类的眼睛可以分辨出红色和绿色?2017年英国皇家学会期刊发表文章认为,这是因为在演化过程里,狗狗吃的是肉以及人类提供的剩饭剩菜,而人类需要去采摘成熟的红彤彤的水果,所以能看见红色对人类的适应性很重要,对狗狗的适应性则不重要。
演化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是自上而下的统一规划,它是摸着石头过河,摸到哪块石头都舍不得丢,全都留在袋子里备用,久而久之,袋子里就装了一大堆石头,每块石头都有自己的用途,石头和石头之间没准还有矛盾。而我们人类,就好比很多块石头拼凑起来的产物,你去看人类基因组,那绝不是什么简洁优美的代码,而是各种来源的遗传基因,缝缝补补将就着用。举个例子,人类基因组里甚至有很久以前感染人类的逆转录病毒留下的模块,那就是“人类内源性逆转录病毒”(HERV),在人类基因组里能占到1%—8% 。连无用的病毒遗迹都还留着,更不要说其他有用处的模块了。
如果这样说你还是觉得很难理解,那我们还可以换个思路,把人比喻成一辆自动驾驶汽车。
现在有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平稳地开着,超过了一辆车,向右转了个弯,途中没有出事故。如果你把这个过程理解为这辆车喜欢超车,喜欢右转,不喜欢碰撞,你就是用了“意图立场”来思考,把这辆车人格化了,而且你依然不知道这辆车是怎么运行的。
怎么才能用“设计立场”来思考呢?你得把这辆车子拆开,细细分析汽车的每个部件。然后你就会发现,这辆车有着很多独立运行的环境感知系统 。比如说,导航系统,能让车知道自己在地球上的哪个位置;摄像头就像眼睛,能识别红绿灯、交通标志、车道线、天气、前方的行人车辆;激光雷达,可以生成周围环境的高精度三维地图;毫米波雷达,有比较强的穿透力,能探测盲点、定位附近的障碍物;超声波雷达,能帮忙倒车和自动泊车。每一套感知系统,都会独立地从环境里获取线索,分析信号、发出报告。然后这许多份报告经过算法处理过后,就会影响汽车的底层执行系统,于是汽车的动力系统、刹车系统、转弯系统就行动起来了。所有这一切都在瞬间完成。当你看到自动驾驶汽车向右转了个弯,这不是因为这辆车“喜欢右转”,甚至不是因为这辆车的中央处理器“决定要右转”,而是许多独立系统共同协作得出的一个动作。你看,用了“设计立场”来思考后,你是不是对这辆车的底层逻辑和运作机制有了更深刻的洞察?
人,其实和自动驾驶汽车非常类似。
首先,人类是生来自带“算法”的,很多研究早就发现,即使是刚出生的婴儿,也绝不是白纸一张,而是自带了很多演化预设好的“出厂设置”,比如说,婴儿会天然认为人声最重要,比其他声音都重要,这样,婴儿才能很快学会母语 。其次,在我们的皮囊之下,也有着许多个自主运行的模块。这些模块大部分时候协作得还行,毕竟磨合了几十万年了,但本质上还是各自为政,所以有时候也会彼此冲突。
说到彼此冲突的模块,书里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糖水罐研究 。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找来一群人,当着他们的面展示了两个玻璃罐子、一包糖粉、一罐水、两张标签纸,一张写着“糖”,一张写着“氰化物!有毒”。
科学家告诉你,两个玻璃罐子绝对干净,糖是绝对安全的白糖,水是饮用水,两张标签纸也是全新的,写着“氰化物”那张绝对没有靠近过任何氰化物,当然更没有沾到哪怕一点点氰化物。你自己动手,把糖粉和水倒进两个罐子里,然后你自己动手贴标签纸,随机一个罐子贴“糖”,另一个罐子贴“氰化物”。
现在你需要从一个罐子里倒点糖水喝,请问,你会从哪个罐子里倒?
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即使是贴着“氰化物”标签的那个罐子里也是绝对安全的糖水,但到了要喝糖水时,绝大多数人会喝贴着“糖”标签的那个罐子里的水。
如果你用“意图立场”来思考,把人当成一个整体,就会很难理解这种矛盾。一个人既不相信一个随意贴的标签就会让糖水变得有毒,同时又有点相信一个随意贴的标签就会让糖水变得有毒,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如果用“设计立场”来思考,这个矛盾就很好理解了。
就像之前说的,人是由很多个独立运作的模块组成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模块,就是用来探测危险的模块。
可以想象,探测危险的模块在人类演化过程里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的祖先面对的环境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放眼望去,尽是猛兽、毒蛇、危险的地形、有毒的食物……有了发达的探测危险的模块,我们的祖先才能活下来,留下后代,也就是我们。
回到糖水罐研究,你身体里的大部分模块肯定认为这两罐糖水没什么区别,但只要一看见“氰化物!有毒!”的标签,探测危险的模块肯定拼了命地报警——注意,这个模块可不管什么逻辑推理,它就是个条件反射,“疑似有威胁,我就拉警报”。然后你的脑子里就亮起红灯,然后你就会谨慎小心,进入防御模式,直接导致你拒绝从标记有“氰化物”的罐子里倒水喝。
我们还要记住一点,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启动线索,有自己关注的特定信息种类。如果信息和模块不匹配,那个信息就没法改变那个特定模块得出的结论。还是拿自动驾驶汽车来做比方,超声波信号只会影响超声波雷达,不会影响毫米波雷达,为什么呢?因为频率不匹配,超声波信号的频率是几万赫兹,而毫米波信号的频率是几百亿赫兹,所以超声波雷达和毫米波雷达只会接收和自己频率对得上的信号,不会去分析其他频率的信号。
人的模块也是一样。在糖水罐研究里,即使你理智上知道“这只是个游戏”“科学家和我无冤无仇,他没理由毒死我”“标签还是我自己刚才亲手随机贴的呢”,但这些信息不匹配“危险探测”的启动条件,所以这些信息最多只能进入理性思考、逻辑推演的模块 ,而无法进入危险探测模块,也就不能改变危险探测模块做出的结论。
说完单个的人,我们再来说说两性关系。
一旦用“设计立场”来思考男女两性关系,你也会忽然茅塞顿开,从而理解很多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年轻的男性为什么会做出一些鲁莽甚至是找死的行为?太平洋岛群美拉尼西亚的年轻男人,会玩一种类似原始蹦极的游戏,爬上24米高的高塔,脚踝上缠着藤蔓,然后直接跳下去 。
如果你用“意图立场”来思考,你会很难理解这种行为——这些男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挑战这种高死亡率的活动呢?
但如果你用“设计立场”来思考,就能理解一点。这些男性不是探测危险的模块不起作用了,只是“在异性面前表现自己”的模块太过活跃了。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为“孔雀开屏”,这确实非常形象,因为公孔雀的超长尾巴和人类男性的冒险行为一样,虽然不利于“尽量保命”的自然选择,但却有利于“吸引异性目光,彰显自己勇敢”的性选择。
再举一个例子,婚姻。
我们太过熟悉婚姻了,以至于觉得婚姻理所当然。绝大多数人类社会都实行一男一女组成的专一配偶制,而且这个配偶制有三大特征:首先,性方面是排他的,也就是说,双方原则上只跟彼此发生性关系;其次,双方共同对后代进行高昂的投资,也就是说,人类父亲通常会长期给小孩提供资源和帮助,而不是把小孩丢给母亲单独抚养;最后,这个配偶制通常是长期甚至是永久的,只要没有特别大的意外,双方默认一直进行无条件的合作和资源共享,也就是说,人类通常不会签订一个有时间期限的婚姻,比如我们不会和伴侣说,让我们结个五年的婚吧,相反,我们在婚礼上的誓词是,“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但从演化角度看,婚姻其实是有很多奇怪之处的 。
第一个奇怪之处,就是婚姻并不是动物里的普遍现象。
要知道,人类的灵长类近亲,其实并不遵循专一配偶制,大猩猩经常是一夫多妻,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则是杂交制,它们都不会结成所谓的“夫妻”,而且公猩猩也不照顾幼崽,都是母猩猩自己抚养后代。自然界里会结成长久夫妻、共同抚育后代的,往往是一些鸟类,但是鸟类和我们人类在亲缘上又非常遥远。
第二个奇怪之处,就是有些人一边抱怨婚姻,一边进入婚姻。比如说,有些人觉得婚姻要求性专一,这是束缚,是“反人性”的。但与此同时,婚姻在人类社会里又非常普遍,说明婚姻在某种意义上一定是“符合人性”的。
如果你用“意图立场”来思考,你就会很难理解,人为什么既厌恶婚姻,同时又渴望婚姻;婚姻为什么既反人性,同时又符合人性。
但是,从“设计立场”来思考的话,你只要理解两个模块就足够了。
第一个模块,是“寻求性机会”的模块;第二个模块,是“守卫配偶,保证亲生后代能存活”的模块。
这两个模块,同时在人类的身体里运行,它们都是人性,但是它们又彼此有着的冲突。一部分人性想和尽可能多的异性发生性关系,婚姻是反这部分的人性的。但还有一部分人性想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有亲生后代存活,而婚姻就是符合这部分人性的。
所以《心智社会》的作者就认为,人类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主要驱动力,其实已经不是“寻求性机会”,而是“守卫配偶,保证配偶不会出轨”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还是得回到人类的演化史。在过去200万年里,我们人类在演化过程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人类婴儿变弱了,以至于母亲很难单独养活婴儿了。
人类婴儿之所以变弱,则是因为人类后期变强了。用术语讲,就是我们人类演化成了一个晚熟的物种。人类在前期是早产儿,特别弱小,无法独立生活,依赖高密度高质量的亲代投资,需要漫长的发育过程;但人类到了后期,就能长出巨大的复杂大脑,从环境里学习到许多知识,能创新,能和其他人进行复杂合作,能狩猎比我们强壮得多的动物,甚至能改变世界。
但后期再强大,前面要是夭折了也是一场空。所以发展出一对一配偶制的人类,就获得了更大的演化优势。如果一对男女能密切合作,缔结一种包括了性关系、资源共享、养育孩子的复杂关系,采集狩猎时代,男方承诺长期带食物回来,女方承诺好好育儿,那么男女双方都能保证自己有后代存活。
婚姻就是这么诞生的。所以婚姻的各种奇怪之处,放在演化的背景下都很好理解 。为什么人类父亲对自己的后代极其关注?为什么成为父亲,甚至会改变一个男人的神经回路和激素水平?因为人类幼崽需要父母双方的高质量投入。为什么婚姻的期限几乎是无限的?因为对小孩的投入几乎是无限的,你多帮小孩一天,小孩的竞争力就越强一点。为什么人类喜欢举办盛大的婚礼?因为盛大仪式可以向尽可能多的外人传达出信号,这两个人要成为彼此的合作伙伴,定下长久的契约。付出这样的成本后,任何一方想要反悔,逃避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都要困难得多。
但同时,“守卫配偶,保证亲生后代能存活”这个模块,也导向了两性关系里的某些黑暗之处。
比如说,亲密伴侣暴力。
之前提到了,人类父亲会将巨大的资源投入在后代身上,他们会带食物给小孩,陪小孩玩,教小孩技能,在危急关头保护小孩。
假如付出了这么巨大的代价,养育的却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那么损失就太惨重了。所以,各种驱动力内部博弈演化的结果就是:人类男性的“守卫配偶”模块变得十分活跃。“守卫配偶”模块的目的,就是监控配偶,不让配偶有和其他男性接触的机会。为此,男性会诋毁或攻击竞争对手,也会想办法把伴侣藏起来甚至囚禁起来,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演变成对伴侣的暴力控制。
因为人类没有演化出亲子鉴定功能,所以“守卫配偶”模块会自动监控的其实是一些代理指标,比如男性自己的配偶价值、女方的吸引力、当前择偶市场的“行情”等等。男性自己的配偶价值越低,女方的吸引力越大,当地的经济越不平等、越可能“赢者通吃”,男性就越是会有强烈的“守卫配偶”需要。
这里值得特别解释一下“代理指标”这个概念。博耶认为,人类的模块经常会自动监控一些可观察到的线索,这些线索被称为“代理指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际上没法预知自己的基因未来会在整个基因库里占比多少,也就是我们没法直接观察到演化适应度这个指标。那么我们就退而求其次,找一些看得见摸得着,而且跟演化适应度密切相关的代理指标来监控。
英国统计学家乔治·博克斯(George Box)有句名言说,“所有的模型都是错误的,但有些模型是有用的”。 这句话用来形容我们的模块也很合适,严格来说,模块监控的代理指标都是错误的,但有些代理指标是有用的。
举个例子,人类有一个“防止近亲繁殖”的模块,关注的就是“童年时谁跟我共同居住”的代理指标 ,童年时期共同居住的时间越长,模块就认定这人和自己的亲属关系越强,然后就越愿意和这个人无条件合作,但会认为这人的性吸引力下降。
因此,博耶认为,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童养媳婚姻更容易破裂。因为在童养媳婚姻里,新郎新娘从小一起长大,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是“防近亲繁殖”模块会让他们潜意识里觉得对方就是自己亲生的兄弟姐妹,于是无法觉得对方有性吸引力,即使勉强结婚,也会觉得非常别扭。
说完了婚姻这个二人世界,我们来说更大一点的群体。注意了,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模块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深度理解人性的钥匙之一,那就是“联盟探测”模块 。
“联盟探测”模块是干什么的呢?这个模块会自动关注和联盟相关的信息:周围的个体属于哪个联盟?每个联盟有多少人?我所在的联盟如果和其他联盟发生冲突,更可能胜利还是更可能失败?联盟内部的个体之间团结吗?会不会相互支持?其他人对我这个联盟忠诚吗?等等等等。
为什么会演化出“联盟探测”模块呢?其实也很简单,人类的演化是为了应对环境压力,别忘了,其他人的存在就是一种“环境”,而且对我们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压力非常大的环境。萨特有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这句话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其他人所构成的环境是残酷且险恶的。如果你无法适应“他人”这个环境,你就会被演化淘汰掉。但如果你能够很好地适应“他人”这个环境,和其他人密切合作、共同行动,你就能取得极大的成功。
我们都知道,人类是非常擅长结成联盟、集体行动的。事实上,联盟可以说是人类能站上地球食物链顶端的主要原因,要是论单打独斗,人类远远不如各种猛兽。
我们都非常习惯联盟了,以至于觉得结成联盟好像是一种本能。但是《心智社会》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越是自然而然的本能,越值得去拆解研究。一定要看到熟悉事物的奇异之处,不要把演化的精妙设计,当成理所当然。
要形成联盟,所有参与者都需要具备至少6个复杂的心理机制 :①要有某个明确要达成的目标,而且单靠自己很难达成,要靠团队合作才更容易实现;②要能预期联盟里的其他人对这个目标有着和自己类似的看法,这样你才会预期其他人会和你合作;③要能够为了实现这个集体目标,而先忍受某些自己的损失,主要是在未来预期里,通过联盟合作得到的好处将超过目前的损失;④要把敌对联盟的收益视为自己的损失,把敌对联盟的损失视为自己的收益,这样就可以燃起对抗敌对联盟的动力;⑤要有心理准备,其他人可能会低估自己的贡献和牺牲;⑥要预料到,联盟里的其他人也会有类似的算计……
这么一拆解,是不是发现,要组成联盟并在联盟里为自己谋福利,这件事还真是有点难度。但你大脑里的“联盟探测”模块,已经演化成可以轻松而且下意识地完成这些计算,而且会不断地给你提供它的计算结果。比如说,只要你看到一群人在对话,你的脑子就会自动分辨谁和谁是同盟,而且这些信息你的脑子也记得特别牢,以后回忆时,你可能记不清每个人具体说了什么,但一定记得谁支持谁、谁反对谁、谁和谁是一边的 。
知道了“联盟探测”模块以后,你不但能理解人类的伟大,而且能理解人类的黑暗残酷。
第一点,联盟经常是竞争性的。你所属的联盟,经常要和其他联盟作对。
你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大家不能双赢呢,搞点正和博弈,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不好吗?
把蛋糕做大的思路,放在现代市场经济里很正确,但我们人类心智演化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繁荣的经济,也没有那么多的正和博弈。
在人类演化过程里,联盟在争取的主要是一样东西,叫“社会支持”。而“社会支持”基本上是零和博弈,我得到的支持越多,别人得到的支持就越少。而我的支持者越多、我的联盟越大,就越可能在战争里打败别人的联盟,实现资源的赢者通吃。
第二点,联盟的竞争性,可能导致了种族歧视、族群间的互相敌视甚至种族灭绝。
我们先从种族歧视说起。
一方面,人类非常在意种族。很多个社会心理学研究都发现,人类对“种族”非常关注,哪怕我们正在做的任务和种族根本无关,我们的大脑也一定要耗费认知资源,去自动记住遇到的人属于什么种族 。
但另一方面,从演化来讲,其实我们是没理由演化出对种族的关注的。不同肤色的人能面对面遇见,也就是近几百年的事。在人类演化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身边都是跟自己同种族、外貌肤色高度相似的人。我们根本没理由演化出专门识别种族信息的模块。
那为什么我们人会那么关注种族呢?
博耶认为,答案很简单,我们的“联盟探测”模块,会自动从环境里收集线索,分析其他人属于哪个联盟。这些线索就包括外貌、口音、服装、装饰、宗教物品、行为习惯等等。
当不同种族的人相遇时,他们不同的外貌、口音、习惯,就会被“联盟探测”模块自动捕捉,人们会下意识地认为,不同种族的人,和自己属于不同的联盟,跟自己会有利益冲突,会和自己争夺资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这个意思。
再强调一遍,“族群”被划分出来,是为了争夺资源 。本质上,歧视也好、刻板印象也好,是为了给争夺资源赋予一个正当的理由——因为你们这群人不行,所以我们这群人有资格打压你们,抢走你们的资源。
当人们察觉到某个群体和自己所属的群体具有竞争关系,就会对那个群体产生负面印象,因为人们会直觉地感到,打压那个群体的成员是一件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不同的联盟要争夺资源,才是歧视和敌意的真正起源。
以前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歧视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所以就有了刻板印象。那么怎么消除歧视呢?大家多在一起交流,交流了就没有误解了,就不会有刻板印象了,然后就没有歧视了。
但如果根据“联盟假说”,歧视是来自威胁,某个群体在争夺资源和发动复仇上的威胁越大,就会遭遇越大的歧视。
的确有研究支持这种观点,比如说在美国,比起黑人女性,黑人男性遭到的歧视更多。比如说,黑人男性面孔更容易激发人们对“无能、暴力”的联想,而且更容易自动激起排斥和恐惧的情绪反应;黑人女性面孔则不会引发相同强度的效应。黑人男性通常会被要求支付更高的保险费和押金,黑人女性遭遇这种歧视的概率要小一些。
同样是黑人,为什么更歧视男性?“联盟假说”很容易解释这点。从联盟角度,男性对另一个联盟的优势地位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为他们更强壮、更可能争夺资源、发动报复。
“联盟假说”还可以解释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不同群体之间,可能之前已经混居了好几代人,一直和平共处,但忽然成为死敌,彼此仇视并做出极端暴力的行为 。
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么大的转变?以前的解释通常认为,这些群体之间本来就有仇怨、猜疑和不满,有一天突然出现一个导火索,就导致了之前累积的恨意来了一个总爆发。
但“联盟假说”的解释则认为,必须区分“族裔类别”和“族群”。人都有族裔类别,但族裔类别不一定会发展成族群。
族裔类别是一种身份上的区分,这个区分既基于血缘、外表、语言、传统等等客观特征,同时也基于一些主观的标准和判断,比如说,犹太人、印第安人、爱尔兰裔……这些都算是族裔类别。
族群则是为了共同目标和利益而一起行动的一群人,族群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过程,既是个体的认知转变过程,也是群体的形成过程——人们开始用族群的视角去看待万事万物;开始将族群的收益和损失视为自己的收益和损失;当有足够多的人都采纳族群视角行动时,一个对内有强大凝聚力、对外有强大对抗性的群体就形成了。
说到这里,就让我们拿南斯拉夫内战和卢旺达大屠杀这两个悲剧事件来分析下:
在极端暴力发生之前,无论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还是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都已经共同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族裔类别,但在漫长的时间里,人们交往和打交道的都是具体的个体,这时候,只有族裔类别,而没有形成“族群”。但是当一些力量推动了人们的认知向族群视角转变,大多数人开始认为别的族群繁荣,就会让自己的利益受损,渐渐地,“族群”就开始形成。接下来,只需要一个导火索,悲剧就会发生了。
听了这些分析,你可能会感到悲观。但接下来要讲的模块,又会让你对人类的大规模合作感到乐观。是的,我们要谈的就是交易和市场经济。
从“拆解模块”的“设计立场”思路入手,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演化到底给了我们人类哪些模块,让我们能形成交易市场呢?
交易看上去非常简单,你有一筐苹果,我有一块布,我们彼此都觉得划算,就可以交换了。
但还是那句话——越是自然而然的本能,越值得去拆解研究。我们感觉交易很简单,恰恰说明了那背后有着演化和自然选择的精心设计,才能让交易不需要经过意识层面的努力思考,而是下意识地就可以顺滑运行。
拿刚才那个例子来说,重点在于,为什么苹果和布可以互换呢?黑猩猩之间也会有互惠行为,但通常都是“互换同一种类的商品或者服务”,比如互相帮助梳毛,这是当下立刻的互换,又比如,我分你一些食物,期待下次你也分我一些食物,这是延迟交换,交换的依然是同一种类的商品或服务。
但人却可以轻易地衡量不同物品的相对价值,我有剪刀,你有苹果,价值不对等没关系,可以用不同数量配比,来达成交换的效用平衡,比如一把剪刀换20个苹果。不同物品的交易在其他物种里非常少见,却是人类拥有的第一个“交易心理”模块,可以称之为“衡量效用”模块 。
第二个“交易心理”模块,叫做“所有权判断”模块。
要交易,首先就得弄清楚哪些东西是我的,哪些东西不是我的。某个东西的所有权如果不是我的,我就不能拿它来交易。
而演化恰好给了人类许多相关的模块,比如说,在所有权上,大家都会认同一些基本原则,原则一,“先到先得”,你先摘到的果子,就是你的;原则二,“按劳分配”,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果子,就是我的。
人类不但可以根据直觉就对所有权做出判断,还能够清晰地对所有权进行表述。人类的所有语言里,都有关于“所有权”的专门词汇,都有“某人拥有某物”的说法。而且所有语言都可以区分合理拥有、不合理的占有,以及暂时地使用权这些状况。
第三个“交易心理”模块,是专门检测“欺骗行为和搭便车行为”的模块。
大家都知道,肯定会有人想在交易里占便宜,多拿利益,少付成本。在这样的演化压力下,人类其实演化出了相应的探测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个会自动运行的防欺诈系统。
我们会想要调查和我们交易的人的身份,看看他过去的交易记录、声誉如何,他是合作者还是欺诈者,他是和别人公平自愿交易,还是会把不公平的交易强加给弱势者……这些信息我们都会很关心。而且一旦确认了合作方可信,我们就会很愿意和这个熟悉的伙伴进行多次交易。
总而言之,“衡量效用”“所有权判断”“检测欺骗和搭便车”这三个模块,共同帮助我们人类构建了交易市场。有了这些模块,才有了如今繁荣昌盛的劳动分工、市场经济,也才有了人类生产力的飞速蓬勃发展。
但也要注意一点,因为交易心理其实是在史前的熟人贸易中发展出来的,所以到了现代大规模的陌生人交易时,我们在心理上是不太适应的。
举个例子,人们经常会从直觉上反感自由市场,特别是那种只考虑商品的质量和价格、不考虑人情味儿的自由市场。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和陌生人进行的一次性交易,会触动我们的“检测欺骗和搭便车”模块,让我们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身份不明的人剥削利用 。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做生意的人要先“搞关系”,这其实符合人的交易心理,因为大多数人都更喜欢在彼此充分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和熟悉的供货商或买家进行重复交易。所以说,为什么大家都乐意在自己喜欢明星的直播间里买东西呢?这不仅是因为明星直播能带来相对优惠的价格,更重要的是,明星和自己的粉丝消费者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情感连接,让粉丝消费者觉得,自己的偶像是“熟悉的自己人”,是不会让自己在交易中受损失的。
再举个另外一个例子,人们通常会不信任追逐盈利的商业组织,而更信任做公益、不追求赚钱的非营利组织,哪怕很多时候,商业组织的效率更高,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从“检测欺骗和搭便车”模块出发,就很好理解这种现象了。“检测欺骗和搭便车”模块在自动运行时,一大重点就是探测对方的意图。如果对方的意图只是获取利益,那么不管对方提出的条件有多么诱人,都可能是在欺诈利用你;但如果对方的意图包含善意、想要帮助你,那么即使对方当下提供的交易条件不是最好,但从长久来看,和他打交道可能是最能让你受惠的。
好了,到这里,这本《心智社会》的大致内容,就为你介绍得差不多了。最后,我再来为你总结一下《心智社会》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1.不要把人当成一个整体,也不要用信念和意图来描述人的行为。要把人视为一个复杂系统,由许多独立允许的模块构成。这些模块可以被视为一种心理器官,本质上和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双手是一样的。
2.每个模块有自己的启动线索,有自己关注的特定信息种类。如果信息和模块不匹配,那个信息就没法改变那个特定模块得出的结论。
3.我们没法直接观察到演化适应度这个指标。所以我们的模块经常会自动监控一些可观察到的线索,这些线索被称为“代理指标”。
4.模块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是正确的、不一定是符合事实的,但通常是演化上有用的。
越是自然而然的本能,越值得去拆解研究。一定要看到熟悉事物的奇异之处,不要把演化的精妙设计,当成理所当然。
5.在人类男性身上,“守卫配偶,保证配偶不会出轨,亲生后代可以存活”的模块,比“寻求性机会”的模块更重要。
6.我们有自动运行的“联盟探测”模块。不同的联盟要争夺资源,是歧视和敌意的真正起源。
我们还有“衡量效用”模块、“所有权判断”模块、“检测欺骗和搭便车”模块,这三个模块,共同帮助我们人类构建了交易市场。
以上就是《心智社会》这本书的精华内容,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心智社会》这本书,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把人看作一个复杂系统,这个复杂系统可以被拆成很多个独立运行的模块。
-
越是自然而然的本能,越值得去拆解研究。一定要看到熟悉事物的奇异之处,不要把演化的精妙设计,当成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