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古典、李松蔚:《不上班咖啡馆》,建立“信以为真的力量”
【终版】古典李松蔚咖啡馆.MP3
迄今为止最特别的一期《大望局》的来历是这样的:
一、最早的打算:请职业生涯规划师、新精英创始人古典来谈一谈他的新书《不上班咖啡馆:打工人的12个觉醒时刻》,本书是近期国内“职场、人生规划、心理”标签下的热门书,也是我们得到电子书独家首发的新书。
二、随即,我想把话题搞得略复杂一点:扩大为困境。职业困境其实是人生困境,背后是心理困境。在本书的写作中,古典放弃了他擅长的知识压缩、提纯模型的思考表达方式,选择用具体故事来回应当下打工人的职场问题,正是为了综合地帮助当下人解决自己的困境——他认为,故事可以帮助一个人建立“信以为真的力量”,勇敢地走出第一步。有了“困境”这个主题,当然就要请来李松蔚老师,请他们从职业咨询和心理咨询的角度分别分析:当下人的典型困境是什么,有什么解决办法?
三、古典说:“好啊,不过,要不要搞得再好玩儿一点?既然是聊大家都在面对的困境,我们来组一个局,请十几位听众,带着他们的困境来一起讨论”。于是,我们在录制的前一晚,发起了一次“快闪招募”。在9月13日下午,从得到站内“知识城邦”和古典公号得到消息,选择不上班前来一叙的朋友有25位,其中,有6位在本次“开放麦”里分享了他们的困境体验(其中有三位朋友的分享会在加餐中放出)。
四、于是,你正在听的是史上最长的一期《大望局》(含下期加餐)。我们三个谈话发起人,也在现场发言朋友飞飞的启发下,公布了自己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困境。
古典,作家,新精英生涯创始人,资深高管教练,得到课程《超级个体》主理人
李松蔚,心理学者,作者,得到课程《心理学通识》主理人
以及大望局、新精英联合邀请到场的25位朋友
00:01:15 这本书与困境的关系是什么?
00:05:22 聊聊这本书的写法
00:12:53 大多数困境都有哪些特征?
00:24:26 第一位来访朋友:38岁,单身,女性,自由职业,在不被理解的过程中渐渐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怎么办?
00:43:51 第二位来访朋友:45岁,女性,即将从大厂离职,失去了所谓的“社会身份”,又该怎样定义自己?
01:01:31 第三位来访朋友:职业发展瓶颈期,继续沿着专业做下去,还是推翻过往选择新副业?
01:17:45 “人生产品化”
01:25:02 面对困境,有哪些确定的应对方法吗?
划重点
-
什么是困境?就像四面的围墙里面有一棵树,而这棵树需要长高、长大,所以迟早有一天就会面临着发生碰撞的情况。
-
困境,其实也意味着你有选择。正是因为有选择,你才会被这些选择困住。
-
至少,这个时代饿不死人了,你有能力接受最大的失败。很多困境,你把它想到极致的坏情况,想到极致,它会给你一种乐观。
-
“做自己”是成本,而不是收益。
-
有时候,你越是清楚地意识到做某种选择,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代价,反而会让这个事情变得容易一些。
-
面对困境,你只有先去做,才能找到解决方法,你只有在路上,才能想明白这件事情。
-
我以我现在的世界观,认为自我的状态像一条道路,它没有被探明的产生过程,没有固定的生发过程,可能也没有明确的意义,它仅仅是时空中的一个过程,留下的一条痕迹。道路本身不懂得终点的含义,它只是努力伸展。所以我不执着于常规意义上的“自我”,处在尚未探明以及明显未完成状态下的自我,也没什么可“彰显”的。但是我渴望把它够到尽可能远的地方(我也许倾向于某一部分的体验,这仅仅是我的选择),我有我的好奇想要完成,我会以这个比喻来说服自己为什么过程就是目的,我会为这条路最终消失之处而感到安慰与遗憾,这就是我的一生。那么,沿途遇到的人和事,天然就是我广义的“老师”,都值得停下来观赏,这也是一种他人和自我的关系--如果你们的关系足够深,就会形成一个个路口,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也是可能的。——这是当我审视困境时,它回答我的。
-
我们的生活会面临各种新选择、新阶段,兜兜转转一大圈之后,你会发现你过去的东西并没有丢失。人生就是如此。
-
什么是“人生产品化”?就是将自己的体验转化为信息、知识,传播给他人,创造价值,留下我存在的记忆。
-
人都会有跟昨日之我告别的过程。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势在必行的时候,你一定会去思考如何在更深层的地方与过去的自我相遇。
-
面对困境的六个方法:一是要体验,别躲避;二是去写下来,看见它;三是要瞎折腾,动起来;四是别把情绪放得太重;第五点是要通过领域去确定自己的位置;最后,去相信、拥护与我个体有关的事情。
-
干一件事,大不了就是干坏了而已。
-
说到底我们就是欠上帝这条命而已,把这件事想通了,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你都敢去面对。
-
人可以通过改变心态来改变生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伟大的发明。
-
“西郊有密林,助君出重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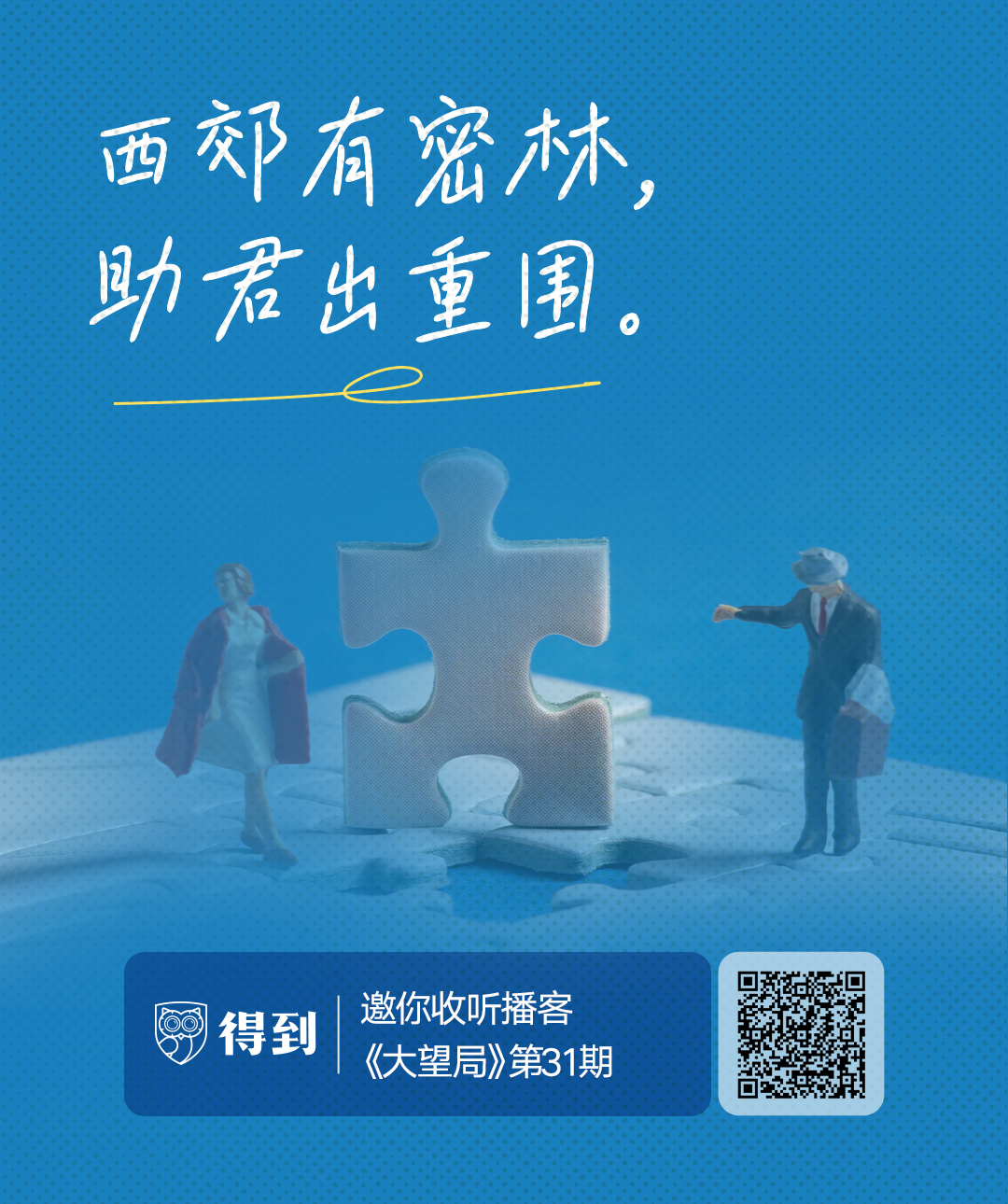
当小红马醒来
在某个时刻,古典发明出了他的工作——职业生涯咨询。我说不准时间,因为未必只是从他2007年创业的那天算起;说“发明”,因为他对这一行的理解和行动,是不大一样的。
好吧,先用极端形式模仿一下对职业生活的常见抱怨:
在职场里上班正在取代在地狱里推石头,成了愁苦人生的新象征。没班上的时候惶惑,有班上的时候痛苦,痛苦于为如此微薄的价钱失掉了自己,同时,又恐惧失掉继续这份痛苦的机会。在写字楼敞开的工位里,一切行动和流程都被切割,你不知道自己在做的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不信它有什么价值。你却要假装信那些注定失败的结构调整,假装信上司言不由衷的许诺,直到大家全都明了彼此都不信了,就发明出一套黑话,用来在会上“扯淡”,用来预防不慎说出心里话的追悔莫及。你看到一群聪明人在花样百出地干蠢事,眼前已无饼,头上仍有锅……
为了讨生活而无法继续生活,这真是个冷笑话。然而,这种荒诞的呻吟是真切的。我们调大音量,让它形成语音:说到底,人不自由,然而,人要是不信自己还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就没法感到尊严,甚至没法活着。这就是看似体面的职场的阴惨所在:它在清晰地提示你有多么不自由。曾经,我们以为熬过了白天就可以不再像西西弗斯一样,拍拍手,坦然地走上回家的小路,把这段被夺取的时间从生命里屏蔽出去,拥有一小段自己的生活。然而,在一切变得抽象以后,只有指纹打卡越发具体,具体为凌晨以后仍然不断跳出来的未读消息数字。是的,对不自由的提醒既清晰又不间断。
在物质和技术空前高涨的年头,生活下降为生存。传来传去的职场规则短视频,无非是勉从虎穴的生存术,说的人和学的人都懂得这是在加深错误,把旁人推入深渊,也使自己因冷漠而非人,或者说,而“职业范儿”。相关的另一个冷笑话是:森林里,两个人见熊来了,一起逃跑。跑着跑着,一个问另一个:“咱们也跑不赢熊啊!”另一个答:“谁要跑赢熊,我要跑赢你。”然而,谁告诉他熊这次只打算吃掉一个人呢?
这不是职业咨询这个行当能独立回答的绝境。然而,我清楚地记得,大约一年半前,古典眨巴着大眼睛盯着我,说:“一个人能不能在职场里真实地活出自己?我来写一本书,回答这个问题。”
我对他的专业领域一无所知,然而我相信眼前这人能做这件不太可能成真的事。
他是个怎么说就怎么活的人。在做职业咨询教练第三年的时候,他出过一本至今影响颇大的《拆掉思维里的墙》,其中说“这个时代(那本书初版于2010年)的玩法,就是找到热爱的领域,成为极限运动员”,“有意思比有意义更重要”,“真诚比智慧重要”,“人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意义和模型……你要找的,是现在最有感觉的那一个”。这些段落让我觉得那本书不该被书店摆在“职场·成功学”的架子上,他强调的是把人从目的明确的手段里解放出来,去寻找和感受自己的生活。
当然,这很难,多少人宁愿一直受苦也不肯面对这种难。古典的职业规划方法论是从人生的根部释放潜能。
而他好像是从来就在这样生活,至今也在这样生活,多年来不置固定资产,不在意“风口”,放任它们飞起又落下。他谈论项目,问的是“这件事好玩儿吗?要不要一起来玩”。而且常常一连十几天找不到人,跑到戈壁上去野营,骑越野摩托,在我看来,那些行动缺少必要的安全措施,随时可能马革裹尸。这些从野地里和太阳底下得出来的经验又让他感慨:自己和顶级高手的差距“不是能力,而是价值观”,那种价值观的基础是不计后果的狂热。
他常说的是,大部分人觉得活得没意思,不是因为生活没意思,而是因为他们只在自己的安全区里。做职业规划,得先探索自己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而无论是什么,“能对周围的人、对这个世界、对社会有价值,是人很重要的标志”。
一年多以前,我请他做一场关于职业的直播。提问者还是老问题:“大学毕业以后,觉得能找到的工作都没意思,怎么办?”他眨巴着大眼睛微笑着回答:“你先干着,现在能找到什么工作算什么工作,先干着。”提问的年轻人未必满意这个和自己家里人差不多的回答,特别还是出自古典的。直播结束后,他低声说:“现在的情况,不先找个事情干的话,会因为长期的空闲失去行动力。”
半年前,也是一个节目里,他说最近有点儿喜欢自己创办的组织了,这话让我惊异:创始人难道会不喜欢自己的公司吗?这是可以公然说出来的吗?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虽然我对职业咨询一无所知,但是我相信古典的诚恳,他所说的,即是他所奉行之事。而且他一直在体察变化,体谅来访者。于是,几个月前,古典说:“自己从前写的那几本书,说的是那时的环境。在当下,需要用另一种方式,和正在职场里彷徨打转的人说话。设定一个场景和几个有代入感的人物,讲讲故事怎么样?你看啊,职场里常见的问题无非是这么几类……”
我印象里,他那段时间大约是每天早起写作,再去上班,中间改过几套写作架构,直到现在的这本《不上班咖啡馆》。当然,中间他也不时中断书稿,四处骑行历险。
且说这“觉醒”。觉醒是大大小小的开悟。人,起码是故事中人,“渐悟”和“顿悟”并没有区别。一切内生的、重要的改变都需要必不可少的堆积和演化,一切也都需要偶然或突然的棒喝,所谓顿渐之分,无非是观测问题。比如,点亮一盏灯要获得火种,也要早早备下燃料。真正可惜的是拒绝再去感受、再去改变,只剩下一堆散乱的情绪和应激式的反应,关闭了超出自我的机会,或者将一切能量盲目地投注在自己厌恶的牌桌上。
如今的一种常见尴尬是,从前的安全区,此时剥落了镀金,现出了牢笼的本相——这里我不是说不清楚,是不能说得再清楚。然而,即便感受不到意思的工作,即便是发现自己是笼中鸟,也仍然不要放弃感受和思想,这是知道自己在活着的唯一选择。“工作中的人”和“生活中的人”原本也是一个连续的人。灯抽去了芯,变成了石头,石头当然不死,那是因为它没活过。古典常说的一句话是“无非是借假修真”,做一份引导他人渐悟或顿悟的咨询,成立一家自己也未必喜欢的机构,大约也是他在修自己。
何况,古典并不像我这么悲观。他在故事里化身胖子老板,把故事中人(以及读者)的问题关联到行业、职业分析,在各个阶段里发出了12张“觉醒卡”、12份觉醒之后的地图。
在第二个故事里,胖子老板向一个从前的优秀设计师、如今苦恼不堪的全职妈妈发出了下面这张觉醒卡:“好的人生玩家在角色顺利的时候,深深入戏;但当角色受挫,能跳出游戏,改写剧本。”
在差不多完稿的时候,古典在他的“新精英生涯”办公楼外抽烟,跟楼下餐厅后厨走出来的大姐借了火,给我讲起书中那个小红马的故事:农夫因为天冷,饲料短缺,不得不杀掉农场里的动物,作为补偿,每个动物可以被满足一个愿望。最后轮到小红马。小红马的愿望是“我不喜欢这个故事,我要去别的故事”,便撒开蹄子,跑进了旷野。他说,这个故事是这本书的种子,我该把它放在哪里呢?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了那个年轻的妈妈,好让她将来讲给她的女儿。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上班还是不上班”“找个什么样的班上”,我们没必要如此收窄对自己的想象,直到把自己锁死在一份工作里,我们甚至也不是被锁闭在固定的人生故事里。从这本《不上班咖啡馆》里醒来,再次相信自由是可能的,前往一个更好的故事。
贾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