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痛毒丸》 于理解读
《止痛毒丸》| 于理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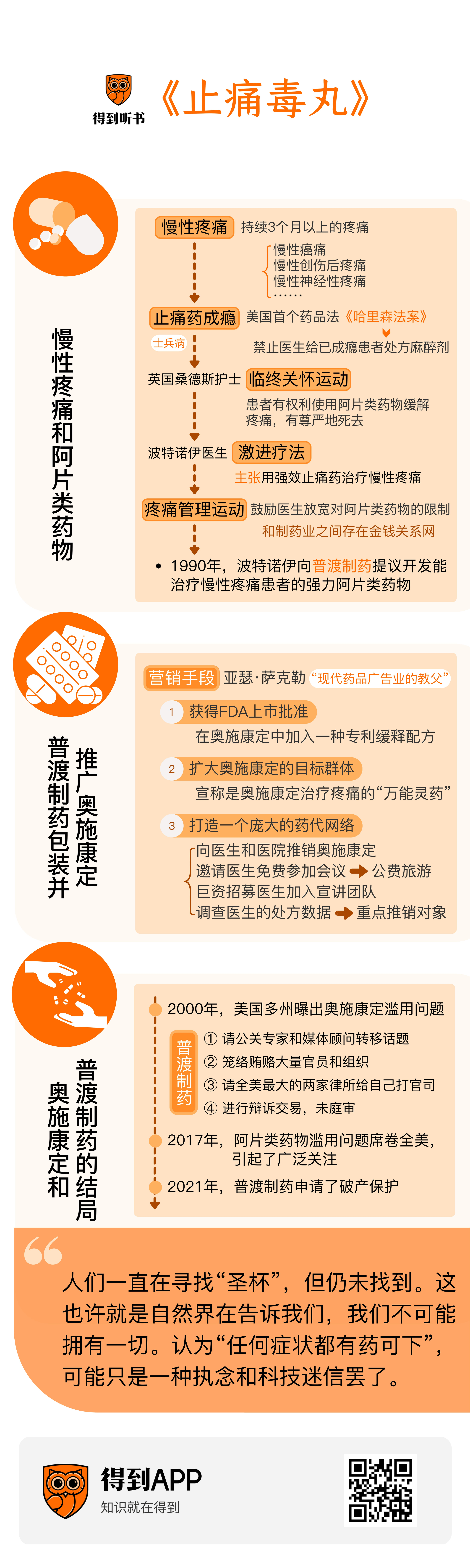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叫《止痛毒丸》,出版于2023年1月。“止痛毒丸”指的是一种止痛类处方药,叫做奥施康定。这类药在美国造成了一场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这本书的作者巴里·迈耶是《纽约时报》的调查记者,曾获得普利策国际报道奖,他也是最早关注到奥施康定滥用问题的记者之一,这本书就是他的深度调查作品。
2021年全年,美国有近10万人死于嗑药过量。他们嗑的,不是什么毒品,而是制药公司生产、医生开处方的止痛药,这类药物也被统称为“阿片类药物”。“阿片类药物”这个词,英语是“Opioid”,和“鸦片”共用一个词根,它们都是用罂粟的提取物生产,或者人工合成的。在这些合法的阿片类药物中,奥施康定曾经是一款明星畅销药,它也是这场阿片类药物危机的源头。
阿片类药物能够治疗疼痛,但有极高风险导致患者成瘾。因此,在医学界,关于要不要给患者开阿片类药物的争论一直没停过。而奥施康定中的麻醉剂含量是其他药物的2倍,甚至还有更高剂量的剂型。因此,它被称作强效麻醉剂中的“核武器”。
对这样一款危险的药物,监管者大开绿灯,制造商的虚假营销铺天盖地。医生开出一张奥施康定处方,药物随即就在街头暗巷中出现,落进青少年和瘾君子的口袋。从美国西部城市到东部发达海岸,从底层平民到上流社会的子女,都卷入了这场奥施康定的毒潮。在一些奥施康定滥用问题严重的地区,犯罪率也上升了,瘾君子们甚至翻墙入室,去偷老人药箱里的奥施康定。
奥施康定的制造商是普渡制药公司,这家公司的控制者萨克勒家族曾经以140亿美元的净资产,位列《福布斯》美国富豪家族榜第19名。而这个家族的崛起,靠的就是奥施康定。1996年,普渡推出这款药物时,创始人雷蒙德·萨克勒就曾慷慨激昂地说,奥施康定就是普渡一飞冲天的翅膀。
如果奥施康定会让人成瘾,那它是如何绕过监管,在全美境内泛滥的呢?2000年时,奥施康定滥用问题就首次曝光了,但直到2017年时,这一问题才被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全美关注。在这十几年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人能及时遏制住这场灾难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奥施康定的故事。为了更全面地还原这段故事的细节,更新书里一些数据,我会结合另一本书《梦瘾: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的真相》和一些相关报道,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这场阿片类药物危机是怎么一回事;接着,我们把镜头对准普渡制药,看看它是怎么虚假宣传、买上瞒下,把奥施康定这款药给推广出去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奥施康定和普渡制药的结局。
好,现在,让我们正式进入这本书。
首先,我们来说说,美国这场阿片类危机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上面说了,阿片类药物是止痛药,能够治疗中到重度的疼痛。但是它很有可能导致患者成瘾,因此,阿片类药物的使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这类药物治疗的,主要是慢性疼痛。
慢性疼痛,和我们平时摔了一跤、刀切到了手感到的疼不太一样。慢性疼痛是持续3个月以上的疼痛,可以分为慢性癌痛、慢性创伤后疼痛、慢性神经性疼痛等等。癌症通常伴随很严重的持续性疼痛,因为恶性肿瘤生长时会压迫敏感神经,甚至挤碎骨骼。因此,癌症患者往往会遭受慢性疼痛的折磨。其他类型的慢性疼痛有各种起因和症状。常见的有偏头痛、慢性背痛、肩周炎痛等等。有些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比如三叉神经痛,就是一种脑神经疾病。有人把慢性疼痛比喻成一种不死的癌症。面对剧烈的疼痛,患者脑海中通常只有一个念头:寻找解脱。
慢性疼痛不仅让患者无比痛苦,它还很难治疗。有时疼痛不仅是生理层面上的,还和心理、社会因素有关。比如有一种“幻肢痛”,患者截肢后,被截掉的肢体部位却传来一种很逼真的疼痛。对于医生来说,治疗慢性疼痛,就像是在解一个谜题。医生喜欢研究的是能诊断、能治愈的问题,但对于疼痛来说,无论是验血、X光片,还是核磁共振仪,都不一定能找到病人的痛因。也没有什么标准的疼痛计算工具,直到现在,我们衡量疼痛的工具,还只是一串从0到10的数字量表而已。
1973年时,疼痛治疗才被列为现代医学的一门专科。不过早在19世纪,化学家就在鸦片中发现了能止痛的物质,给它取名为“吗啡”。到了19世纪中叶,人们开始意识到,使用止痛药是有代价的。直到1900年,美国的止痛药成瘾患者已经超过三十万人,其中很多是参加了南北战争的老兵。战争期间,为了治病止痛,他们要吃止痛药,不幸成瘾。比如联邦军就给它的士兵发了近一千万粒止痛药丸。因为这种情况太常见,止痛药成瘾甚至被人戏称为“士兵病”。
后来美国联邦政府就通过了美国首个药品法《哈里森法案》,禁止医生给已经成瘾的患者处方麻醉剂。因为这样的规定,面对饱受疼痛折磨的患者,医生没法大方地开止痛药。哪怕患者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了,也只能生生忍着。在英国有一位护士叫桑德斯,她在晚期肿瘤医院里看到了临终病人痛苦的样子,决心做点什么。于是她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临终关怀机构,护理临终患者,让他们能舒服地度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时日。她认为,患者有权利使用阿片类药物,缓解疼痛,有尊严地死去。
临终关怀运动影响了医学界对阿片类药物的看法,一些疼痛专家开始支持使用阿片类药物,不过也还有不少坚定的反对者,他们认为疼痛病人不过是想找个借口逃避工作,或者骗取毒品罢了。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中,有个叫波特诺伊的医生入行了。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个人呢?因为在二十年后,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这个新人在一场医学运动中名声大噪,甚至改变了医生们治疗疼痛的方式。他主张用强效的止痛药,激进地治疗慢性疼痛。后来,他的观点也成了普渡制药的宣传武器。
回到波特诺伊刚入行的时候。有一次,他接待了一个得了镰状细胞贫血症的黑人大哥,这个病的症状之一就是剧烈的疼痛。那个大哥告诉波特诺伊,他每次疼痛发作,就得去医院,忍着疼熬上好几个小时,才能从急诊医生手里拿到几片止痛药。于是,波特诺伊给他开了一张止痛药处方,够他买一些药放在家里备用了。大哥当场崩溃大哭,说以前从来没有哪个医生这么信任过他。
后来,波特诺伊出于同情心理参加了一个研究。他们研究了一个癌症中心的38名患者,得出结论说,阿片类药物疗法是一种安全,也更人道的治疗方式。对于没有药物滥用史的疼痛患者来说,用阿片类药物治疗比撒手不管要强。虽然样本只有38名患者,局限性很强,但他们的结论在当时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
波特诺伊开始去各个地区宣讲,随着他名声渐起,支持者也越来越多。接下来,波特诺伊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论文中,波特诺伊说,过去的研究者说的“高成瘾率”是不对的。只要患者没有药物滥用史,他使用阿片类药物就几乎没有成瘾风险。为了支持这一说法,他还引用了三篇报告。后来,普渡制药等公司,就引用了这组报告和波特诺伊的解读作为证据,声称奥施康定的致瘾风险要“小于百分之一”。
多年以后,美国各地毒瘾泛滥,越来越多的人死于服药过量,人们才发现,波特诺伊所引用的这三篇报告要么站不住脚,要么就是被波特诺伊曲解了。在2011年的一次视频采访中,波特诺伊道歉了,说自己之前的研究有些问题。他说,论文依据的“数据非常少”,这是“一篇无足轻重的论文”。他说他当初是想改变人们对阿片类药物的看法,帮助疼痛患者得到更好的救治。“如果当时我能知道一丁点现在的状况,我就不会讲那样的话。”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波特诺伊大肆推广他的激进疗法时,他经常斩钉截铁地公开表示,长期使用阿片类药物是安全的。
无论如何,在波特诺伊活跃的时候,医学界恰好迫切地需要改进疼痛治疗。当时各地的医生都遇到过疼痛患者来求助的经历,面对痛苦的患者,医生就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阿片类药物柜子的钥匙,却不能把柜子打开。想给,却不能给。在这种情况下,波特诺伊说的话,是医生们早就想听到的:你的病人正在受苦,给他们用阿片类药物吧,他们是不会上瘾的。
在波特诺伊等疼痛专家的呼吁下,美国掀起了一场疼痛管理运动。政府权威机构发布了新规,鼓励医生放宽对阿片类药物的限制;新闻媒体也开始大力宣传,攻击那些限制医生尽情开处方的一切法规、机构和监管机制。在他们笔下,法规在添乱,政府缉毒干警也在多管闲事,剥夺患者用药的权利。但是,媒体没有报道的,是这场疼痛管理运动和制药业之间的金钱关系网。制药业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波特诺伊这样的研究人员,还给美国疼痛基金会等团体重金补贴。
就这样,十年之间,一个曾经对阿片类药物避之不及的国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了一阵使用阿片类药物的风潮。在这场运动期间,也零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专家警告说,历史上对阿片类药物的戒心不是没有来由的,没有人做过认真的长期研究,看阿片类药物到底会不会致瘾。但人们对这场运动的热情足以淹没这些声音,特别是那些曾经因慢性疼痛而痛苦不堪的人。现在,解决他们痛苦的方法就在眼前。
1990年前后,波特诺伊拜访了普渡制药总部,向他们提议开发能治疗慢性疼痛患者的强力阿片类药物。而当时普渡制药已经在设计奥施康定了。可以说,波特诺伊为奥施康定的推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普渡制药又将用它疯狂的营销手段,为奥施康定点燃最后一把火。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讲讲普渡制药是怎样包装并推广奥施康定的。
普渡制药的控制者是萨克勒家族。提到萨克勒家族,你可能会想到一些博物馆和画廊。他们捐钱建造了不少博物馆,比如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萨克勒展厅,还有北京大学的萨克勒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但是在慈善光环之下,萨克勒家族是奥施康定的幕后推手,并靠这款药赚了几十亿美元。
要说萨克勒家族的卖药手段,不得不提到的是大哥亚瑟·萨克勒。亚瑟·萨克勒被称作现代药品广告业的教父,他发明了一系列推广药物的手段。比如医药代表这个职业就是他开创的,现在全世界的医药代表都得喊他一声祖师爷。
亚瑟·萨克勒推广药物的手段非常多,其中有些很受争议。比如他有一家双周报《医学论坛报》,向全国十六万医生免费分发,作为他推广产品的营销工具。此外,他还在医生、专家和顾问的身上挥金如土,资助了不少医疗团体。他负责营销的安定,是制药业第一个销售达10亿美元的药品。亚瑟·萨克勒的这些营销手段,后来也都用在了奥施康定身上。
要把奥施康定推广出去,普渡制药首先需要获得FDA,也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批准。普渡制药对FDA说,他们的这款止痛药绝对不会被瘾君子滥用。为什么呢?因为普渡制药在奥施康定中加入了一种专利缓释配方,药片里的有效麻醉剂会逐渐释放,一部分在服用的一小时内就能生效,其余的会慢慢生效。“康定”这个词,就是英文单词“持续作用”(Contin)的缩写。也就是说,奥施康定起效慢,瘾君子不会喜欢的。
理论上看,是这么个道理。但实际上,这点障碍对瘾君子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只要刮掉药片外面的糖衣,捣碎药片,用一点水或者唾液溶解粉末,就能让药片中所有的麻醉剂立马生效。所谓的缓释配方对瘾君子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但是在当时,FDA却接受了奥施康定的这套说辞。最重要的是,FDA允许普渡制药在药品标签里加了这么一句话,说奥施康定作为缓释药剂,它的成瘾风险低于传统止痛药。在它之前的麻醉类管制药品的说明书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话。这句话成了普渡的营销神器、官方背书。当时,FDA的官员们也争论过,要不要允许普渡加这句话,其中,负责审批奥施康定的审查员柯蒂斯就支持普渡。一个月后,奥施康定过审。三年后,审查员柯蒂斯加入了普渡,成为执行医疗总监,第一年的薪酬大礼包有40万美元。其中发生了怎样的利益勾兑,就可想而知了。
接下来,普渡制药的营销动作,是扩大奥施康定的目标群体。
在奥施康定出现之前,瘾君子就已经开始使用处方类止痛药了,比如扑热息痛、泰勒宁等。这些药物中的有效成分都是羟考酮,是一种麻醉剂,每片药通常含有5毫克羟考酮。但奥施康定不一样。奥施康定的成分是纯羟考酮,剂量最低的也有10毫克,是其他药物的2倍。甚至还有羟考酮含量更高的剂型,比如20毫克、40毫克乃至160毫克。因此,奥施康定被称为强效麻醉剂中的“核武器”。只有慢性疼痛患者、癌症患者,才能谨慎地服用奥施康定。但问题就在这,目标人群少的话,怎么卖得出销量呢?
制药公司要想靠一款药挣大钱,必须让更多人认为自己需要这款药才行。于是,普渡公司就声称奥施康定是一种治疗疼痛的“万能灵药”,能用它治疗背痛、关节痛、牙痛,以及所有你能想到的运动损伤。作为一种阿片类药物,奥施康定本应该被小心对待,却成了包治各种疼痛的灵丹,普渡制药就这么成功地扩大了它的目标群体。
接着,普渡开始打造一个庞大的药代网络,向医生和医院推销奥施康定,邀请医生免费参加会议,开会的地点都是度假胜地,就是一种公费旅游。普渡还斥巨资招募了数百名医生加入他们的宣讲团队,在医院员工会议、医护人员的进修课堂等各种场合发表宣讲。奥施康定上市后的几年内,公司大概资助过几千场这样的演讲。
普渡的销售还能调查出医生开处方的数据,找到那些频繁给患者开阿片类药物的医生,作为他们的重点推销对象。疼痛患者们通常是去找全科医生开处方,全科医生的问诊时间比较短,也很少接受过疼痛管理方面的培训,不管是拔了智齿,还是关节炎、严重头痛,他们都会给患者开阿片类止痛药,而这类医生正是普渡制药的推广目标。销售们跑遍了各地的医院和疗养院,手上的医生电话号码从开始的3.3万个,增加到7万个,遍及全美各地。奥施康定的营销是普渡有史以来最具野心的行动,销售人员多达一千多人。当医生问销售,给患者开奥施康定有多大风险会成瘾时,销售们总会给出那个标准答案:低于1%。
1997年,医生们开的奥施康定处方有90多万份,到了2002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700多万份。奥施康定在美国刮起了一场汹涌的药物滥用潮,美国死亡率升高、犯罪率飙升。伪造的、失窃的、空头的支票满天飞,大多数面值40美元,因为在街头买40毫克的奥施康定就是这个价。警察见到这种支票就取笑说:“我明白这40美元你花哪了。”
还有一些医生把诊所开成了“药丸工厂”,每天给几百人开处方,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干。俄亥俄州的朴茨茅斯市就有大量这样的药丸工厂,被称为“药丸工厂之都”。它曾经是一个辉煌的工业城市,后来当地工业走向了衰败,经济下滑,留下了大批失业的工人。这时有一位叫普罗克特的医生来到了这里,受过工伤的工人来找他,无论是腿疼、腰椎疼还是关节炎,只要付200美元见普罗克特3分钟,就能得到一张奥施康定的处方,倒卖给街头的瘾君子。后来,普罗克特的候诊室变得人满为患,人们假装自己很痛,医生也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当地的一位护士说:“我女儿药物上瘾,法官的孩子药物上瘾,市长的孩子药物上瘾,警察局长的孩子药物上瘾。优秀家庭的孩子们也都成了瘾君子。”
朴茨茅斯市的故事,是美国阿片类危机的一个侧面。美国有1亿慢性疼痛患者,其中大部分人都在用阿片类药物治疗,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不会对这类药上瘾,他们乐观地相信成瘾问题已经被新技术解决了。奥施康定上市十年之后,滥用人数已经达到了610万人。
2017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阿片类药物危机成为全国紧急事件。政府官员们承认没能及时遏制这场危机,媒体也纷纷刊发长文,指责萨克勒家族推开了公共卫生灾难的大门,这场危机终于引起了全美关注。但其实早在2000年时,奥施康定就已经开始遭到抵制了,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能及时遏制这场灾难呢?
让我们先回到2000年。这时,奥施康定风头正劲,而美国的多个州纷纷曝出了奥施康定滥用问题,联邦缉毒探员也开始调查一些医生涉嫌非法处方奥施康定的案件。为了应对负面新闻,普渡高管去到这些地方,向当地医生强调这些滥用案件只是各自孤立的意外事件。但民间对奥施康定的抵制变得越来越强烈,主流媒体也进行了报道。这些公开报道震惊了FDA官员,他们催促普渡总部尽快解决问题。同时,美国缉毒局的一些官员也开始对普渡展开调查。
面对这场危机,普渡请了一堆公关专家和媒体顾问。他们计划转移矛盾,把媒体的矛头从奥施康定滥用,转移到泛泛而谈的处方药滥用话题。普渡对外宣称,不应该仅仅因为个别嗑药者,妨碍真正的患者获取药物。
另一方面,普渡利用金钱、职位和各种好处,笼络了大量官员和组织。普渡雇用了一大批缉毒局前任探员,还在奥施康定滥用问题最严重的那几个州雇用了一批地方警官,编织了一张能为它所用的巨大关系网。同时普渡疯狂砸钱给一些组织,比如国家管制物品管理局全国协会,各个州的药品管制人员代表都在这个协会里。接受资助前,在这个协会的年会上,人们呼吁尽快应对这场阿片类药物危机;接受资助后的那一年,年会演讲主题就变成了“谁能幸免于媒体的刀笔”,开始讨论怎么应对媒体的揭露报道了。
同时,面对来自各地对普渡虚假宣传的个人或者集体诉讼案,普渡请了全美最大的两家律所给自己打官司。在法庭上,大多数原告对奥施康定上瘾前曾滥用过其他药物,无法证明普渡要为他们的成瘾问题负责,因此所有起诉几乎都被驳回了。每到这时,普渡就要发一篇新闻稿庆祝胜利。
不过,正当普渡为自己强大的公关机器庆贺时,一张传票寄到了公司。过去几个月,有两位美国助理检察官也注意到了普渡虚假宣传的问题,他们怀疑是普渡高层精心策划了这些营销手段。于是,他们向普渡寄出了一张传票,通知普渡司法部已正式立案,调查普渡推销奥施康定的行为。随后,一群检察官和调查员花了四年时间,深挖了一遍普渡内部几千封电子邮件和文档。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了大量普渡向监管机构隐瞒信息、对滥用问题熟视无睹的证据。
2006年,为期四年的调查结束了。检察官认为,奥施康定危机本不该发生,因为普渡早在1997年,也就是这个药上市的第二年就知道它被人滥用了,普渡却一声不吭;但普渡高管坚称自己在2000年年初才听说有滥用问题,然后就修改了奥施康定的药品标签。检察官提议对三名高管提出严重指控,罪名包括阴谋欺诈美国罪。这个罪特朗普也被指控过,指的是欺骗了政府,干扰了政府的某项职能,或者从政府那里骗取了钱财。一旦定罪,三人就得入狱服刑。于是,普渡花大钱组建了一支全明星律师团队,和检方进行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在法院开庭审理前,检察官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可以进行协商。如果被告人做了认罪答辩,承认了罪行,法官就不再召集陪审团审判,而是直接判处被告人相应的刑罚,并在量刑时从宽处理。在普渡一案的辩诉交易期间,双方达成一致,检方将以“标签不当”、虚假宣传的轻罪指控三位普渡高管,三人也表示认罪。
听证会上,法院里挤满了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因为服用奥施康定过量死亡。他们从千里之外赶来,想亲眼看看法庭是否会接受普渡高管的认罪答辩。他们一个个站起身来,讲述他们儿女的故事,想要说服法官判处三人入狱。有位母亲站起来,痛斥普渡就是个披着公司外衣的大型贩毒集团。但是最终,法院依然接受了普渡高管的认罪答辩。三位普渡高管不用进监狱,做些社区服务,支付6亿美元的罚款就行了。虽然这笔罚款是当时刑事罚款中数额最大的一笔,但是它还比不上普渡3周的销售额。
由于司法部没有对普渡高管进行庭审,检察官团队搜集来的大量证据,也就没能公开,而是封存了起来,这场灾难的真相也被一并掩埋了。
十年后,2017年,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席卷全美,也终于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美国,平均每天就有175人因滥用药物死亡。而据《福布斯》杂志估计,从1996年奥施康定上市到2017年,奥施康定的销售额持续上升,达到了350亿美元。
美国的几十个州、市、镇掀起了一阵巨浪,各地政府立案起诉普渡和其他阿片类药物制造商。如果普渡没有虚假宣传、隐瞒真相,如果2007年时司法部选择进行庭审、曝光证据,如果监管机构有勇气和制药业作对,或许这场危机就不会发生。
2021年时,诉讼缠身的普渡制药申请了破产保护。同时,普渡的一些内部文件也曝光了。文件显示,1996年,在一场奥施康定发布会上,一位普渡高管曾为销售团队打气,声称有了奥施康定在手,“像暴雪一样的医生处方会掩埋其他一切竞品药物”。五年后的2001年,奥施康定滥用问题开始失控,当时的普渡总裁也丝毫不认为这是公司虚假营销的问题,而是受害者的错。他说:“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打击滥用者,犯错的是他们,他们是一群不管不顾的罪犯。”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摄影师叫南·戈尔丁,“私房摄影”就是她发明的。南·戈尔丁也经历过药物成瘾。2010年年末,她发起了一场运动,呼吁各大博物馆停止接受萨克勒家族的捐款,从捐赠墙上凿掉萨克勒家族的名号。2019年时,她带领一群人,在纽约的一家博物馆里进行了一场小型示威。示威者抛洒了几百张仿造的奥施康定处方,纸片从博物馆的中庭上空纷纷飞落,嘲弄着普渡高管二十年前说的那句“像暴雪一样的医生处方”。后来,这家博物馆撤下了萨克勒家族的姓名,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也纷纷把这个名字移下了捐赠墙。
到这里,奥施康定和萨克勒家族的故事就走到尾声了,但阿片类药物危机仍未结束。只不过主角从奥施康定,变成了非法芬太尼。更可怕的是,很多瘾君子从阿片类药物开始成瘾后,又转向了海洛因等毒品。就这样,合法的阿片类药物打开了美国毒瘾的闸门。
好了,到这里,《止痛毒丸》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完了,我们来做个总结。
对于慢性疼痛患者来说,奥施康定是一款有效的药物。可一旦营销战胜了科学,医生的处方权被滥用,它就成了让人上瘾的毒丸。奥施康定造成的灾难,不仅仅是普渡制药的责任,还有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问题。普渡做的一切,都是在美国FDA的批准和监管下发生的。对于各大药企的无序竞争疯狂营销,监管部门也后知后觉,甚至形同虚设。
对医生来说,疼痛是一个无法客观测量,完全依赖个人表述的症状。医生要在满足病人要求和专业判断间取得平衡,这并不容易。在保障患者权益的呼声中,医患关系变得更紧张了。如果医生不积极为患者治疗,还可能会被告上法庭。既然疼痛专家、普渡制药和FDA都说阿片类药物不会上瘾,那尽一切可能为病人止痛,就成了医生的首要选择。
在医疗保健系统的漏洞之外,美国的这场 危机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奥施康定的滥用,就是从像朴茨茅斯市这样的传统工业区,也就是美国的“铁锈地带”开始的。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升级,这些村镇的工厂和矿山纷纷外迁、倒闭,大量蓝领工人失去了工作。他们生活困窘,又往往都患有慢性疼痛,他们要么需要止痛药,要么成了毒贩。医生、病人、毒贩和瘾君子,就这么串在了一条供应链上。就像这本书的介绍里说的那样:“当身体的疼痛被利用,也许,社会的疼痛才是根源。”
奥施康定不是第一种被滥用的麻醉剂。早在20世纪初,医生们就开始寻找能止痛,又不会成瘾的药物了,并且把它称为“圣杯”。麻醉剂的历史,就是不断寻找“圣杯”的过程。这个过程几经挫折,不少药物最初都被误以为不会致瘾,比如海洛因,比如奥施康定。人们一直在寻找“圣杯”,但仍未找到。这也许就是自然界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拥有一切。认为“任何症状都有药可下”,可能只是一种执念和科技迷信罢了。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如果你想听更多关于奥施康定故事的细节,也可以去读一读原书。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要是你喜欢这本书,也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当身体的疼痛被利用,也许,社会的疼痛才是根源。
-
人们一直在寻找“圣杯”,但仍未找到。这也许就是自然界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拥有一切。认为“任何症状都有药可下”,可能只是一种执念和科技迷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