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的民族》 王朝解读
《美利坚的民族》| 王朝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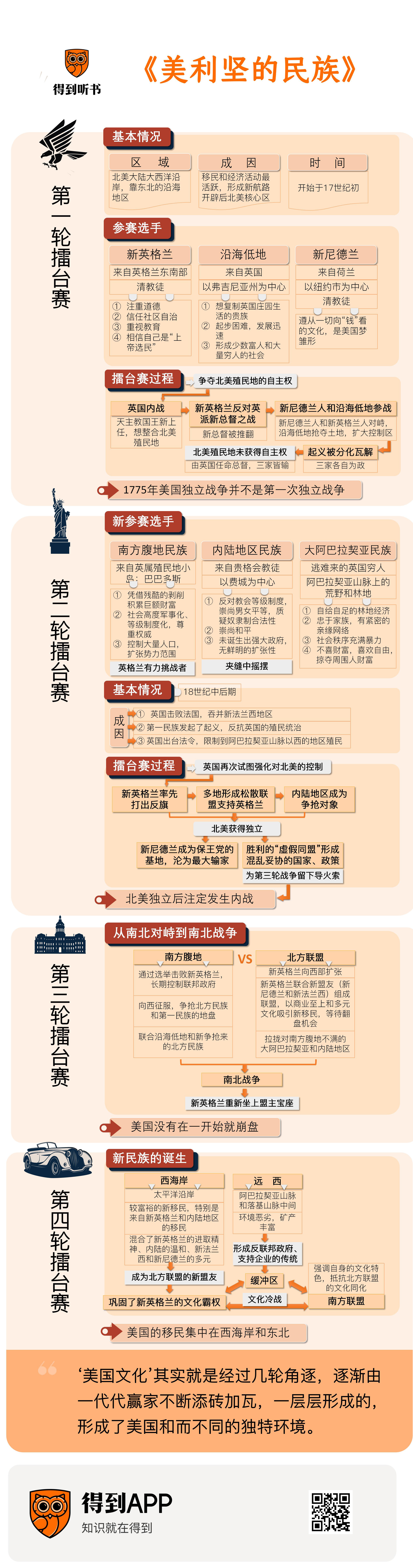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美利坚的民族》,你可能也会有点奇怪,美国都是外国移民,哪里来的美利坚的民族?的确,有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作为一个纯粹的移民国家,他们的民族都是外国输入的。当然,你可能也听说过另外一种说法,说美利坚堪称世界上最奇特的民族,世界各地的移民都能被美式“大熔炉”给熔成一个样子,变成一种差不多的美式口味。这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它既反驳了美国的民族都是外来户的说法,也颠覆了“大熔炉”的说法,认为美国不是浑然一体的一锅,而是一个十一宫格的火锅,由十一个在北美生长出来的“民族”拼在了一起,新的移民不是煮成一个味道,而是煮成了十一种不同的味道。
本书作者科林·伍达德是一名记者兼历史学家,曾经获得过多个历史奖项,也曾获得普利策奖提名,对美国各地的历史文化都有很深研究,听书之前也解读过他的《海盗共和国》。这本书曾经被美国多个主流媒体评为年度好书,临近选举年都会被媒体翻出来讨论和分析各地区的投票倾向。我们现在常常也会在新闻里听说美国现在被撕裂了,这本书反而认为,这些撕裂不是最近才出现的,而是一直如此,而且现在这十一种民族之间的味道差别还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各国移民的文化各有特色,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会发现移民的比例在美国不同区域的分布是不同的,为什么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去的是美国东北?为什么南方的黑人多,西海岸的华人多?
伍达德就提出,这是因为美国内部的差异比我们想象得大得多,大到有十一个民族之多,他们分别占据了美国的不同区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影响着美国的历史。刚刚说过的移民分布差别,就源于更早的移民文化奠定的基础。这些民族是受到最开始的移民文化的影响,个中差异在美国立国之前就存在了。比如南方的黑人多,是因为南方最早的移民本来就是来自加勒比海英国殖民地的种植园主,是奴隶制的支持者,而西海岸华人多,是因为西海岸融合了东北的开拓精神和内地地区的包容精神。
罗振宇老师讲过一本《阿尔比恩的种子》,主题和这本书很像,也是讲美国的内部文化差异,但是《阿尔比恩的种子》只讲了四批英格兰移民形成的四种文化,而本书将时间和空间都大大扩展,对美国现在的状况也更有解释力。不过,应该要提醒,这里所说的民族,其实是一种有地理基础的文化圈层,它们的边界不是完全固定的,彼此之间有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势力范围也会此消彼长。
按照伍达德的分类,我们重新看待北美三百多年的殖民和开发历史,会发现这段历史就像一个擂台赛,不断有新的玩家登场。我把这段历史分成了四轮,每一轮都有不同的目标,选手也在不断增多。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场北美擂台赛上的选手都有谁,你可以配合电子书的地图,更好地理解局势变化。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整个北美看作是一个擂台,主要的参赛选手有十一个。头一个选手,也是最倒霉的选手,就是北美的原住民,俗称印第安人。这里我们用正式一点的名称,叫第一民族。第一民族当然是北美大陆上最早的定居者,也是主场作战,不过实力不强。我们都很熟悉这段不幸的历史,由于欧洲人带来的瘟疫和巨大的技术优势,在早期殖民征服的残酷压迫之下,第一民族虽然不完全是看客,但相较其他选手,可谓是毫无还手之力,长时间没有什么存在感,这里我们先按下不表。
那我们再来看另一位选手,也就是最早的外来选手,书里的叫法是“北方”民族,其实说的是西班牙殖民者,这个北方就是指在西班牙殖民地北方,他们到得最早,但是离主擂台很远,不过,他们的地盘可不小,从加利福尼亚州一直到得克萨斯州,中间的一大片区域都可以算是北方民族的地盘。从全美洲的角度来看,这片区域是西班牙殖民地在征服中美洲之后,往北延伸出来的边缘地区,再往北,就是大片的高山和荒漠,对当时的人来说很难开垦利用。在我们所说的擂台赛初期,他们和第一民族一样,在现在这个阶段,不是主角。
说了半天,主擂台都还没介绍。其实,说的就是北美大陆的大西洋沿岸,尤其是靠东北的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区。为什么说这里是主擂台?这是因为,这片地区后来的移民和经济活动最活跃,形成了新航路开辟后北美的核心区,美国最初的十三个州就在这里,在后来几百年的时间内,仍旧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地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一轮北美擂台赛的选手,就都是在这里登场的。第一轮比赛的时间大约开始于17世纪初,主要有四个选手随着移民浪潮隆重登场,分别是两个来自英国的选手,具有开拓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新英格兰,还有崇尚特权的沿海低地,另外还有两个不讲英语的,崇尚多元的新法兰西和只想多赚钱的新尼德兰,我们来一一介绍。
首先来看一号种子选手,新英格兰人,我们也可以叫他们“洋基帮”。他们是北美早期最有开拓精神、最理想主义的。他们是我们最熟悉的美国早期移民,你可能听过“五月花号”1620年登陆美国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大多数来自英格兰东南部,信仰当时新出现的一个基督教教派,叫加尔文宗。加尔文宗的信徒也被人们称为清教徒,清洁的清。之所以叫清教徒,是因为加尔文宗对信徒的道德要求非常高,清教徒们相信要通过约束自己的欲望,靠大家一起努力奋斗,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符合上帝旨意的乌托邦,并最终获得救赎。新英格兰人的信仰让他们有四个显著特征。首先,他们注重道德,尤其是清教规定的宗教道德,不遵循者可能被视为异教徒并被驱逐。其次,他们信任社区自治,他们的城镇就像一个小共和国,由从教会的成年男性中选举产生的行政委员,来管理法律、学校、房产、税收和民兵等事务。第三,他们重视教育,每个定居点都建立公立学校,并强制所有孩子接受教育。最后,由于清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选民”,他们怀有强烈的使命感,既感到优越,又渴望扩张,以使世界更符合上帝的旨意。可以说,新英格兰是一个由教堂和学校组成、注重道德的民族,由于他们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的势力范围扩张最快,所以是最强的种子选手,但是当然,这样也会让其他选手更讨厌他们。
其中一个对手,就是同样来自英国的沿海低地民族,他们的聚居区比新英格兰稍微靠南一些,以现在的弗吉尼亚州为中心。沿海低地的移民来源和新英格兰人不同,他们并不是清教徒,而是一批想要复制英国庄园生活的贵族,大多数是贵族家庭的小儿子,因为没有继承权,只能来美洲碰运气。他们听了西班牙人的故事,也想来当新大陆的征服者。然而,北美并没有中美洲和南美洲那么庞大的人口,沿海低地的贵族子弟们除了抓一些土著人当苦力,要么得回英国忽悠穷人过来当牛做马,要么就从非洲买黑人过来。由于和英国贵族的关系很密切,沿海低地的起步虽然有点困难,但发展也很迅速。总之,沿海低地很快形成了一个由少数富人和大量穷人组成的社会。处于社会顶层的是一小撮越来越富有的种植园主,他们很快就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和政治事务,比如美国国父华盛顿的祖先就是当地的地主。而处于社会另一端底层的是一支劳工大军,几乎没有任何权利,这种社会结构可能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是种族隔离的基础。
在这两批英国移民的夹缝之中,还有一个地盘不大,钱却不少的新尼德兰。所谓尼德兰,就是荷兰的别称,新尼德兰的核心区域,就在现在的纽约市。可能有些朋友知道,纽约曾经叫作新阿姆斯特丹,就是荷兰早期殖民者所建立的城市。当时的荷兰移民,和新英格兰人一样是新教徒,但他们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民的方法不是靠教育和道德,而是靠自己赚的钱多。最早的新阿姆斯特丹就是一个纯粹的贸易站点,不管哪里的人,只要是来赚钱的,新尼德兰人就来者不拒。有个传教士记载,当时新阿姆斯特丹大约500人,居然能数出18种语言,连其他民族不欢迎的犹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这种一切向“钱”看的文化,让新尼德兰人和英国邻居相比显得非常宽容,而且他们也极度重视私营企业,相信大家都能白手起家,这其实就是“美国梦”的信念雏形。
类似的还有新法兰西,顾名思义,就是始于法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民族,比新英格兰再靠北一些,现在主要是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说起来,法国殖民者抵达北美的时间仅次于西班牙人,比五月花号还早,但新法兰西却没有其他选手那么上进,到殖民地建立一百年后的18世纪,新法兰西最大的城市总人口也只有七万多人,而同时期的新英格兰、沿海低地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将近一百万人。为什么早起的鸟儿没吃到虫?这是因为新法兰西人最开始想建立一个兼容并包的理想社会,特别是要向土著民族学习,最早招来的农民都是契约工人,结果很多契约工觉得耕田太累了,就和土著民族一起跑到森林里过上了自由人的生活,做皮毛贸易。很多新法兰西人就这么维持相对自由的半游牧、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独特的开放包容、悠然自得的文化。
这四个选手一开始各扫门前雪,很长时间内没有相互接触,虽然经历过一些宗主国战争导致的政治控制权易手,比如新尼德兰和新法兰西先后都被英国吃掉,但他们的独特性并没有被消灭。殖民地的新民族相比旧大陆的母国,还是有很高的自主权。不过随着殖民地的不断发展,到17世纪70年代,各个殖民地都初具规模,宗主国就开始眼红了,当时的英国国王就准备强化对殖民地的控制。我们都知道后来在1775年发生了美国独立战争,但其实那不是北美的第一场独立战争。真正的第一场独立战争,发生在17世纪80年代,我们也称为美利坚民族的擂台赛第一轮,目的是争夺北美殖民地的自主权,除了宗主国英国,参赛选手还有新英格兰和新尼德兰、沿海低地两个挑战者,而新法兰西此时还没有被英国兼并,并没有参与。
当时,英国国内发生了内战,新上任的天主教国王想要把北美几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全都整合成一整块殖民地,用自己任命的总督来控制他们,特别是要压制新英格兰的清教。于是在1689年,新英格兰人在波士顿直接起义反对国王派来的总督,没有想到总督不堪一击,一下就被推翻了。本来没有什么主张的新尼德兰人和沿海低地,害怕独尊清教的新英格兰人一家独大,都出手争夺霸权。恰好,英国的天主教国王在英国被推翻了,英国人找来信仰新教的荷兰国王继位,也就是著名的“光荣革命”。新尼德兰人在纽约和新英格兰人对峙,以为荷兰来的老乡国王能让他们获得更大权力,而沿海低地则趁机把附近天主教徒的土地都抢了,扩大了自己的控制区。但最后的结果是,三家各自为政,起义被分化瓦解,北美殖民地的自主权并没有获得恢复,总督还是由英国国王任命,大家都成了输家。眼看第一轮比赛没有分出高下,反而让英国继续骑在他们头上,决出真正赢家的第二轮比赛只是时间问题。
经过一百年休养生息和继续发展,美利坚选手们跃跃欲试,即将迎来第二轮打擂台,这就是我们更熟悉的北美独立战争。
不过,这一百年间,又出现了三个新选手,他们都是说英语的新移民,分别是崇尚奴隶制的南方腹地民族、无法无天的大阿巴拉契亚民族和温和开放的内陆地区民族。
南方腹地的区域比沿海低地地区更靠南,所以叫“腹地”。不过和其他移民不同的是,他们的祖先不是直接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一块历史更为悠久的英国殖民地,也就是当时英语世界最富有且最恐怖的社会——巴巴多斯。巴巴多斯是一个英属加勒比小岛,那里盛行奴隶制,而且极其残忍,巴巴多斯的奴隶死亡率是沿海低地的两倍。当地奴隶主用各种坑蒙拐骗的方法把人骗去巴巴多斯,以至于当时有一个英语单词叫“被巴巴多斯”,意思就是强行绑架。凭借这种残酷的剥削,南方腹地的奴隶主积累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到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当地的人均财富达到令人目眩的2338英镑,是沿海低地的四倍多,几乎是纽约或费城的六倍多。奴隶主们不仅拥有大庄园,还管理着数量极其庞大的黑人奴隶。在同样盛行种植园制度的沿海低地,黑人和白人比例只有1比1.7,黑人还少一些,而在南方腹地,黑人奴隶的数量达到了白人的五倍。南方腹地社会高度军事化、等级制度化,文化上尊重权威,以便管理奴隶和镇压奴隶起义。他们控制了大量人口,而且还积极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是新英格兰的有力挑战者。
相比之下,在北方的夹缝之中,新出现的以费城为中心的内陆地区民族,就显得要温和很多。内陆地区的移民源头主要是一批叫“贵格会”的基督教徒。贵格会教徒反对教会等级制度的权威,认为在精神层面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质疑奴隶制的合法性。他们不像清教徒强调政府控制,而且崇尚和平,认为要自己以身作则感召其他人,结果他们没有诞生出强大的政府,也没有鲜明的扩张性,成为夹缝中摇摆的一派。
与此同时,在更靠内陆的山区,也出现了新的选手,也就是大阿巴拉契亚民族。这些人也被称为“边民”,或者“乡巴佬”,就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逃难来的英国穷人。这些乡巴佬大多数来自英国的苏格兰、爱尔兰地区,为了逃避战争或者饥荒,数以十万计的难民迁入北美,但是此时大多数东海岸方便开发的土地已经被兼并,附近只剩阿巴拉契亚山脉上的荒野和林地,这就成了新移民的地盘。为了在山区生存,他们采用自给自足的林地经济,他们狩猎、捕鱼,很少耕种,以成群的猪、牛和羊的方式积累财富。他们还会把不容易储存的农作物酿成威士忌,当成货币。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间,威士忌在山区都是通用货币。在这种环境下,大阿巴拉契亚民族保持了鲜明的特色。他们忠于家族,表兄妹之间经常相互通婚,形成了紧密的亲缘网络。与此同时,这些乡巴佬的社会秩序却充满暴力,私刑的情况非常普遍,正义主要是通过个人报复来伸张。大阿巴拉契亚人也不喜欢积累自己的财富,而是喜欢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自由,有不少人成群结队组成帮派,不断掠夺周围更加富裕的人们。
到了18世纪中后期,英国再次试图强化对北美的控制。特别是在1763年,北美连续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英国击败了法国,吞并了新法兰西地区,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二件事,一百多年来和法国人相安无事的第一民族发起了大起义,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于是为了安抚第一民族,也为了避免北美殖民地继续坐大,导致了第三件事,英国出台了一道法令,限制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地区殖民,给已经饱和的东部又套上了一道紧箍咒。打碎这套枷锁的第二轮擂台赛,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率先打出反旗的还是新英格兰,但这一次不同,沿海低地、南方腹地、大阿巴拉契亚、内陆地区先后支持新英格兰,形成了一个各怀鬼胎的松散联盟。在战争中出力最多的是沿海低地和新英格兰,在当时的北美革命军中,大多数领袖来自沿海低地,比如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乔治·华盛顿等著名的美国开国元勋,而大多数士兵则来自新英格兰。摇摆不定、反对战争的内陆地区成为双方争抢的对象,他们既有富兰克林这样的支持者,也有很多平民反对独立,选择当听话的好臣民。而新尼德兰则又一次站错了队,成为保王党的基地,最终成为第二轮的最大输家。
在胜利的联盟里,各方利益也不一致,伍达德称之为“虚假的同盟”。对新英格兰来说,他们想一雪前耻,成为新任的北美盟主,推广自己的价值观。而大阿巴拉契亚则是限制令最直接的受害者,他们一边在打英国人,一边也在跟内陆地区、沿海低地以及南方腹地抢地盘。在沿海低地和南方腹地两个选手看来,他们的参与是身不由己,种植园主们担心如果不加入战争,以后会被反对奴隶制的新英格兰打压。于是在击败英国后,胜利阵营内的几个选手三心二意,担心独立会激怒英国,只有最团结的新英格兰人拉拢了沿海低地,一同主导起草了宪法。不过,为了维护北美联盟不至于再次陷入内战,《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实际上是混乱妥协的产物:低地和南方的士绅反对普选,于是总统就是选举人团选举的;内陆民族反对单一制政府,于是美国就成了联邦制国家;新英格兰虽然号称盟主,但是也不得不向其他盟友妥协,允许不平等的奴隶制存在,但是被奴役人口在投票时只能算五分之三票,而且区域也受到限制。
也就是说,第二轮的胜利联盟内部本来就分赃不均,特别是奴隶制的问题没有解决,留下了第三轮的导火索。
在建国不到一百年内,美国就又一次分裂了,这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南北战争”。不过,既然大家都不满意,为什么美国没有在一开始就崩盘呢?
实际上,联邦最开始的确岌岌可危,南方腹地和新英格兰为了争抢领导权差点大打出手。由于新英格兰推举的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表现得太过霸道,南方腹地团结了其他选手,在后来的选举中击败了新英格兰,长期控制联邦政府,联邦才逐渐稳定下来。
但最核心的理由,是内部矛盾的向外转移。美国独立后撇开了英国的禁令,开始向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部扩张,边界靠西的新英格兰、内陆地区、大阿巴拉契亚、南方腹地向西进军,他们恰好也是实力最强的前四名选手。当然,四家争抢的西部并不是完全无人居住,我们最开始说过,还有说西班牙语的北方民族,他们成为新的征服目标。伍达德这么描述当时的局势:“各方都心知肚明,此事关系到联邦政府的控制权。无论谁赢得了最大的一块领土,都有可能主宰其他民族,并像俄罗斯人、奥地利人、西班牙人或土耳其人在各自多元文化帝国中所做的那样,制定其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准则。”
向西开拓的过程短暂地将内部矛盾转向了外部,客观上缓和了内部争议。而靠大海的新尼德兰、沿海低地、新法兰西被隔绝在大西洋沿岸,只能寻找海外的移民来增强实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部腹地联合沿海低地、大阿巴拉契亚、内陆地区,牢牢控制着联邦政府,并且通过战争从北方民族手里抢来了大片新的势力范围。然而,新英格兰找到了新的盟友,那就是新尼德兰和新法兰西,他们所倡导的商业至上和多元文化吸引了大量的新移民来到美国东北部,三家组成了新的北方联盟,卧薪尝胆,等待翻盘机会。
近一百年间,不断向西征服,开始争抢北方民族和第一民族的地盘,南方腹地用武力为奴隶制抢到了更大的地盘,但是以新英格兰为首的北方联盟则吸收了更多移民,越来越有钱。1850年,每有一个出生于外国的人生活在蓄奴州,就有八个这样的人生活在自由州。当扩张已经延伸到太平洋海岸,抵达了大陆尽头,南方联盟才突然意识到,面对新英格兰和盟友的不断扩张,如果他们坐视不管,最终的输家将会是自己,于是最终撕破脸皮,打响了第三轮比赛,也就是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的历史在这里就不赘述了,但值得提醒的是,南北战争实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南方”或者“北方”。前面说过,北方的三个选手组成了一个北方联盟,但他们其实还拉拢了对南方腹地不满的大阿巴拉契亚和内陆地区。崇尚自由的山区乡巴佬们和崇尚平等的内陆人都认为南方腹地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倡导的奴隶制和自己的文化本来也格格不入,于是倒向了北军。北方的领袖林肯,恰好就是一个新英格兰、内陆地区以及大阿巴拉契亚的混种,他的父母是新英格兰人,他却在内陆和阿巴拉契亚山脉生活和成长。
最终,南方腹地的盟友只有沿海低地和新争抢来的北方民族,在第三轮比赛中被新英格兰击败,奴隶制也被取消,这也是目前为止,美利坚民族之间最后一次武斗。经过了两百年的努力,新英格兰终于得偿所愿,名正言顺地坐上了盟主宝座,并在之后一百余年里,定义了何为“美国精神”,而南方联盟则退缩回了自己原本的势力范围,等待下次东山再起。
内战结束后,美国的领土抵达了太平洋,各势力的领土范围基本定型,但是人口的西进却没有结束。这场西进运动也就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堪称北美擂台赛的第四轮。这期间诞生了两个新的民族,西海岸和远西。
西海岸的主要范围就是太平洋沿岸,比如加州,他们的人口主体是比较富裕的新移民,特别是来自新英格兰和内陆地区的移民。由于北方联盟最终夺取了南北战争的胜利,所以他们在富饶的西海岸地区移民也比较多,最终西海岸混合了新英格兰的进取精神、内陆的温和,还有新法兰西和新尼德兰的多元,成为北方联盟在西部的新盟友。
而远西,夹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落基山脉中间,其实比西海岸离东部地区更近,说“远西”,其实是因为气候和地理环境恶劣,所以心理上更遥远,他们是最后形成的美利坚民族,他们的移民比西海岸更穷。虽然环境恶劣,但是这个地方矿产丰富,当地秩序由开矿的大企业维持,形成了当地人反对联邦政府、支持企业的传统。
伍达德说,在这一时期,大多数新来的移民生活在新尼德兰、内陆地区、新英格兰,而其他移民则生活在西海岸。这些移民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门户城市定居,尤其是纽约、费城、波士顿、芝加哥以及旧金山。反观内战的输家们,几乎没有移民定居在沿海低地、大阿巴拉契亚、南方腹地或北方地区。原因非常简单,南方腹地和沿海低地盛行近乎封建的、根深蒂固的贵族制度,即便内战结束后,当地仍以由大地主主导的农业为主,更别提大阿巴拉契亚山区和北方民族所在的穷乡僻壤了。
这个抢移民的阶段,可以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之前,又是一个一百年。在拓荒过程中,西海岸成功成为美国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区,成为这一轮的大赢家,他们巩固了新英格兰的文化霸权,而南方联盟输掉了战争,变得更加警惕,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之内开始强调自身的文化特色,上一轮的输家们越来越团结,试图抵抗北方联盟的文化同化。这期间,各文化地盘基本定型,而远西、内陆地区、北方民族成为内战对峙双方的缓冲区。这一波新移民融入了美国原有的文化圈,充实了北方联盟的实力,也拉大了他们和缺少移民的南方联盟的文化差距。此后,美利坚各民族之间虽然不打仗了,但却出现了文化冷战。
虽然我们都说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但是伍达德提醒我们,人口统计学家计算出,移民只占美国21世纪初人口的一半左右。他说:“如果美国在1790年关闭了边境,那么到2000年美国人口仍将是1.25亿而不是2.5亿。1820年至1924年,移民数量庞大,但从未真正压倒过一切。”
可以说,北美现在是以“文化冷战”为名的第五轮比赛,开始自20世纪60年代,以民权运动为标志,双方开始互相攻击对方的文化。这一轮的两大阵营,分别是远西、山区和南方腹地的“迪克西”联盟,现在的代表人物就是特朗普,与西海岸和新英格兰为首的“洋基”联盟。击败特朗普的拜登,恰好来自新英格兰,这并非巧合。
书里举了一个例子,说美国作为一个两党制国家,可以用一个数据来衡量撕裂程度,那就是看有多少人生活在压倒性支持其中一党的地区,这个压倒性的门槛,就是在大选中以超过20%的优势超过对手。研究发现,生活在这种压倒性选区的选民比例从1976年的26.8%增加至2004年的48.3%,而且近些年的比例肯定还会更高,可见美国的撕裂还在不断加深。未来鹿死谁手?伍达德提醒,说西班牙语的北方民族在过去150年中,并没有从和南方腹地的联盟中得到什么好处,他们正在悄然倒向新英格兰和西海岸主导的联盟。伍达德推测,在未来的选举中,靠近墨西哥边境的这一大帮北方文化区,将会决定美国的命运。而在更遥远的未来,美国可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内部妥协,强化各地自主权,变得更松散,像现在的欧盟;第二种就是直接分裂成至少两个新联邦,一派是强调多元,但总想扩张的“洋基”联盟,另一派则是推崇等级社会,但崇尚孤立主义的“迪克西”联盟。
我们可以从几轮比赛的历史中,发现美国历史的秘密。尽管开始充满了暴力,但竞争本身的大趋势,是越来越不暴力。有了联邦之后,虽然大家心里不满,但大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只要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在联邦政府的框架内解决。伍达德说,中央政府是将美国维系在一起的为数不多的机构之一,所以美国更加需要中央政府廉洁、公开、高效地运作,毕竟大家都盯着。另一方面,美国用文斗取代武斗,不伤筋动骨,打冷战,而不是热战。而我们现在熟知的“美国文化”,其实就是经过几轮角逐,逐渐由一代代赢家不断添砖加瓦,一层层形成的,形成了美国和而不同的独特环境。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也可以点开文末的电子书,对照文中的地图,再梳理一遍美国历史。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这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它既反驳了美国的民族都是外来户的说法,也颠覆了“大熔炉”的说法,认为美国不是浑然一体的一锅,而是一个十一宫格的火锅,由十一个在北美生长出来的“民族”拼在了一起,新的移民不是煮成一个味道,而是煮成了十一种不同的味道。
-
我们现在熟知的“美国文化”,其实就是经过几轮角逐,逐渐由一代代赢家不断添砖加瓦,一层层形成的,形成了美国和而不同的独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