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熟有道》 王朝解读
《生熟有道》| 王朝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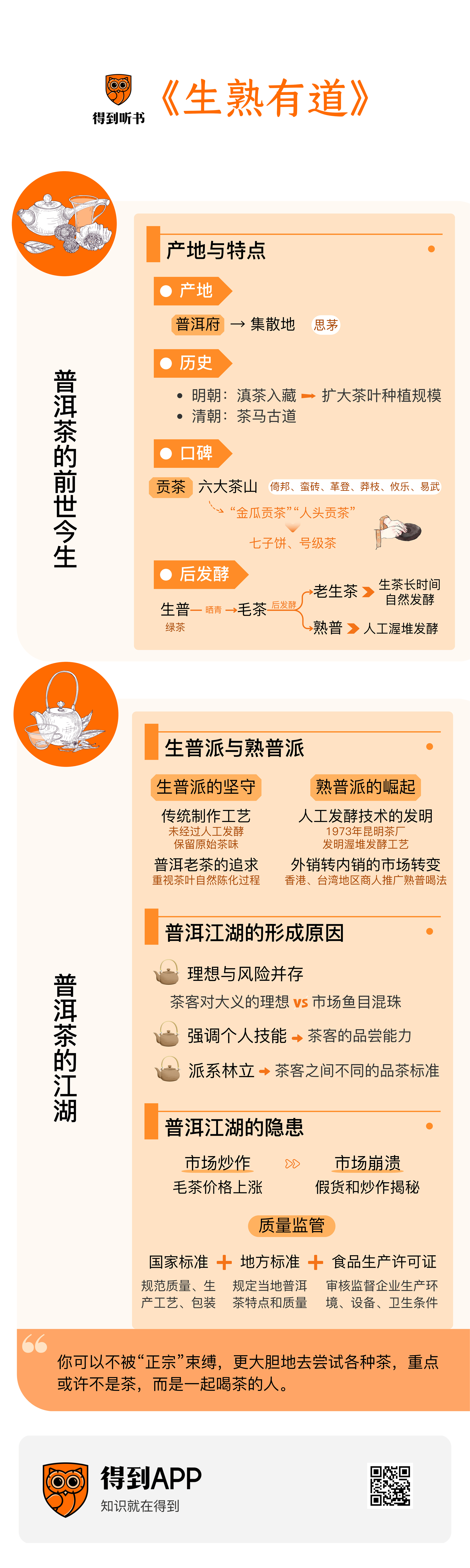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生熟有道》,是一本关于普洱茶的书。说到生熟,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么多种茶叶,好像只有普洱茶,是特别强调区分生熟的?我们都知道,普洱的生熟之分,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发酵。发酵过的,就算熟普洱,反之,没有发酵的普洱茶,就是生普洱。其实,只要是茶叶,都可以有发酵和不发酵的区别,只要你愿意,龙井也可以拿来做成熟龙井,只不过味道就很难说了。本来,茶叶可以按照需要发酵的程度分类,从完全不发酵的绿茶,到完全发酵的黑茶,共有六大类,有人说普洱这种有生熟转化的,应该单独算一类。为什么只有普洱茶搞特殊呢?这涉及特殊的产地、历史等等方面,我们后面慢慢展开。
除了有生熟之分,普洱茶商家在营销的时候还会特别强调一大卖点,叫“越陈越香”。据说,根据存放时间的长短、不同制作技法、不同储藏点的气候特征等等,普洱茶在复杂的发酵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风味。不过,按普洱茶客们的说法,无论生熟,同一批普洱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变得更香,他们认为,随着市场不断消耗,每一批茶都会变得越来越稀有,这让他们称普洱茶为“金融茶”。
当然,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标准,到底是哪个产地、哪种做茶技法、哪个仓库、哪个年份的普洱最香,并无定论。这里也要负责任地补充,在不恰当的保存条件下,发酵过程会有污染,不但不能变香,还会有毒。普洱市场存在鱼龙混杂,以次充好的现象。普洱茶市场中,有些门派各不相让,争相宣传自己的茶才是“正宗”,如果要进入普洱茶的江湖世界,就需要仔细辨别真假。
而今天这本书的作者张静红,堪称这个江湖里的老侠客了。不过,她既不是种茶的,也不是卖茶的,张静红是一个人类学学者,现在是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副教授,研究消费和饮食文化。她自己就是云南人,但一次机缘巧合,让她发现外界对普洱的理解跟本地人似乎并不一样。于是她就抱着疑问,在云南的易武镇,也就是普洱茶的核心产地之一,开始了长期的实地调查,陆陆续续积累了十多年的普洱研究经验。
张静红不仅对普洱茶的生产到销售,都有很深的了解,也跳到圈子之外,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以普洱为代表的商业模式,如何让一个被埋没的地方土特产,成为一个著名的茶叶品牌。实际上,普洱不仅仅蕴含了风味和茶香,也浓缩了市场和江湖的兴衰起落。张静红告诉我们,不管是熟普洱,还是“越陈越香”的观念,其实都不是古来有之的传统,而是近几十年间形成的普洱江湖文化。这本书重点不是普洱这个物品,而是普洱文化背后的人,是普洱江湖所折射的社会万象。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顺着几个问题,来看看普洱江湖。首先,我们先了解几个基本问题,普洱茶是怎么得名的?普洱茶原产自哪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在火起来以前,是谁在喝普洱?他们的喝法和现在有什么不同?然后,我们还是以普洱茶的产地易武为典型案例,结合社会经济变迁,讲讲普洱是怎么被“重新发现”,如何开宗立派,而后,又经历了过热崩盘、起起落落的过程。
好,我们首先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普洱为什么叫普洱?有人可能会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就像龙井茶是龙井村的,以此类推,普洱茶就是普洱产的茶,而且还能说出来云南就有个叫普洱的城市。这个答案只对了一半。普洱茶的确得名于古代的“普洱府”,但普洱府其实并非普洱茶的主产地,而是集散地,位于现在的宁洱县。在2007年前,宁洱就叫普洱,而现在的普洱市叫思茅市。为了有所区别,不至于搞混了,我们接下来还是按思茅来称呼普洱市。以思茅为中心,附近的临沧、西双版纳等等地方,同样是普洱茶的主产区,而且最出名、最贵的那些普洱茶,往往不在思茅,比如现在很火的“冰岛”,当然不是那个北极圈国家,而是临沧的一个村,也很有名的“老班章”,产自西双版纳西南部的班章村。张静红主要调查的易武镇,则在西双版纳东南部。普洱市周边产区,反而没有那么出名。
这片区域的茶叶种植历史悠久,而且是中国其他地方不常见的大叶茶。尤其是在明代以后,西藏大量买入云南茶叶,促使很多汉族人开始移民到这些区域,扩大茶叶种植的规模,这就是历史上的“滇茶入藏”。到清朝,滇茶入藏达到了巅峰,清朝政府专门在云南和西藏接壤的云南西北设立机构管理茶叶贸易,西藏的茶商要拿到许可证,才能继续南下到普洱府去买茶。你可能听说过“茶马古道”,说的其实就是这个路线。不过,这个名字可不是因为用马运送茶叶啊,而是说西藏商人是拿西藏产的良马,去跟云南茶商换茶叶。
不过,当时普洱茶的口碑不靠“茶马古道”,而靠“贡茶”。并不是什么普洱茶都能叫贡茶,而只有所谓“六大茶山”产的茶叶,才能称为“贡茶”。这六大茶山确切地说是哪六座,众说纷纭,但总之是现在景洪市以东的六座绵延相连的茶山,作者采用了一个较为公认的说法,是倚邦、蛮砖、革登、莽枝、攸乐、易武。
这六大茶山的茶叶采摘下来以后,在当地经过粗制,再运到普洱府的总茶店加工成团成饼,经过一路山长水远,送到北京给皇帝品尝。现存最老的普洱茶,就是从六大茶山出产的贡茶,存世只有两砣。贡茶经过长期存放后,茶叶转变成金黄色,又因为造型就像一颗椭圆的瓜,大概也是一个人的脑袋大小,所以有“金瓜贡茶”“人头贡茶”的名称。
有了贡茶的名声,普洱茶的市场也就不再局限于西藏和北京,而是远销到广东,甚至东南亚。由于路线变化,普洱茶的集散地在20世纪初就转到了易武,当地用石磨手工压制成茶饼,七饼为一筒,俗称“七子饼”。很巧,我和易武也有些渊源,易武口音和周边的版纳口音不同,是滇东南的石屏口音,因为当地的汉族人是明、清两代逐渐从石屏县迁移来这里做茶叶生意的,形成了一个方言岛,当地最出名的几个茶号,就是石屏人开的。而我的老家就是石屏,因为易武在我们县的西边,我们管去西边做普洱贸易叫“走西头”,听人说,我的曾爷爷就是在走西头时和人起了争执,不知下落。但总之,近现代的普洱茶就是从易武的商号走出去的,比如“同庆号”,这些近百岁的老茶,也叫“号级茶”,在市场上奇货可居,一度可以卖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价格。
讲到这,只讲了普洱茶的产地历史,那么,普洱只有产地特别吗?当然不是。现在我们说,普洱的特别之处,还在于有一个“后发酵”,也就是从“生”变“熟”的转变。一般的茶叶发酵,是在鲜茶采摘、揉捻后,就进入发酵阶段,最终再制成毛茶。前面说过,按照发酵程度不同,茶叶可以分为绿茶、黄茶、白茶、青茶、红茶、黑茶,也就是传统的六大茶类。其中,绿茶和黄茶基本不发酵,白茶和青茶是部分发酵,种类繁多,铁观音、乌龙茶这些我们也很熟悉的茶类,就属于青茶。而红茶、黑茶和普洱茶都是全发酵茶,区别就在发酵工序的时间不同,黑茶和普洱都是“后发酵”,也有人主张,普洱茶应该独立出第七大类。
那“后发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采摘好的茶叶放在太阳底下自然晾晒,水分慢慢蒸发,这个工序叫做“晒青”。晒青后的茶叶也叫“毛茶”,已经粗制为可以喝的茶叶,然后再去进行发酵。没有发酵过的普洱叫生普,也是可以喝的,算是绿茶。而普洱的后发酵,还能再分两类,一类叫老生茶,是生茶长时间的自然作用下,慢慢发酵。与之相对的就是熟普,是人工专门进行渥堆发酵,把自然发酵过程从几年缩短为几个月。
到这,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普洱茶虽然因地得名,有贡茶、“号级茶”的辉煌历史,但今天茶客们认为地理范围不能定义普洱茶,还有一个必要特征,就是后发酵的特殊茶香。刚才讲的贡茶、“号级茶”,毫无疑问肯定不是熟普,为什么呢?因为熟普的渥堆发酵工艺,要1973年才在昆明被发明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熟知的浓黑的普洱茶汤,对几个世纪以来的老普洱茶客来说,反而是闻所未闻的。就是在产茶的易武当地,他们本来喝的也一直是生普,茶汤颜色清亮、黄绿。
现在的普洱茶共识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从历史的生,变成了现在的熟?没错,生熟的门派之争,就是普洱江湖的缘起了。
我们先用张静红的一个亲身经验,来展现一下生普派和熟普派的江湖分野。
时间倒回到2002年,张静红还没有成为一名学者,当时她参与了一个云南茶叶的纪录片录制,剧组导演是个北京人,为了降血压,路上一直在喝普洱。虽然作为一个云南人,张静红早就接触过普洱茶,但她惊讶地发现,导演喝的跟她以前见过的普洱绿茶完全不同,色红,味浓,不涩,但她觉得有一股“土腥味”。剧组里另一个云南人悄悄跟她说,这就是发霉的味道。剧组一路到了易武,张静红发现当地做的饼茶,冲泡出来也是熟悉的黄绿色,而不是导演喝的红色。当时剧组里有人从茶叶市场听来一个说法,说这种像绿茶的叫生普,要等存放几年以后,到时候冲出来的也是红色的,他们说那种老茶才更有价值。
回到昆明,张静红才注意到,茶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普洱茶饼,茶商们都在宣传自己的茶放了五年甚至超过十年。他们也告诉张静红,那种天价老茶,现在都不在云南,而是在香港、台湾的商人手里。甚至有人说,普洱产在云南,存在香港,藏在台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人不分生熟,更没听过“越陈越香”,本地反而几乎没有老茶库存。
这是为什么呢?这要从熟普的诞生说起。
张静红发现,早在易武售卖“号级茶”的20世纪初,普洱茶就已经在香港茶楼里风靡一时。云南地势险峻,山高谷深,当时的普洱茶从产地要经过几个月的陆路和海路运输后才能抵达香港,早已不是易武流行的新茶。茶叶在复杂的湿度变化中自然陈化,经历了天然的后发酵过程,到香港茶楼时,变成了独特的熟茶味。
随着时代变化,易武的茶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合并为国营茶厂,搬出山里,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易武都没有再做茶饼,而只是生产毛茶,供应给茶厂。在中国香港地区、东南亚乃至欧洲依旧热卖的普洱茶,是这个时期中国的重要外汇来源,云南也修起了公路、铁路,加快了茶叶的运输。很多地方也把采摘困难、平均产量不高的大茶树砍掉,换成了更矮的小茶树,用更科学、更集约的办法种茶。
不过,茶厂很快就发现,运输快了,产量高了,客户反而更不满意。原来,原本几个月的运输,缩短成了几天,缺少自然熟成,就没了特有的风味。为了重新获得发酵的茶香,当时在珠三角就有人发明了“发水”,就是把茶叶上洒上水,堆在一起,改变原有的湿度、温度,人工促进发酵。后来为了重新打开销售渠道,云南的茶厂专门派人去学习,又结合了湖南黑茶的制作经验,1973年在昆明茶厂发明了渥堆发酵,这才真正形成了“熟普”的制作工艺。
但是注意啊,即便是1973年之后,熟普也是由专门的进出口公司作为外汇商品专卖给港澳市场的,当时云南人内部流行的还是绿茶口味的生普。比如普洱茶没有发酵之前的晒青毛茶,也可以叫“滇青”,此外还有“滇绿”等等其他绿茶。当时说起普洱茶,专指那种紧压成型的茶,而那些散茶,就算产自普洱,也更多会被归入绿茶。
等到改革开放,中国内地搞起了市场经济,外汇商品在国内开始销售,老百姓兜里有了钱,各地的人员交流也变多了。从九十年代开始,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商人开始到普洱茶的原产地大举采购普洱,熟普的喝法出口转内销,开始回流到内地,“越陈越香”的说法也是这个时期才普及开来。张静红问的很多老茶客,都会回忆九十年代第一次喝熟普,的确是有一股不同的味道,当时的理解是“霉味”,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接受。
简而言之,虽然早在一百多年前的二十世纪初,普洱就已经有了生熟之别,但是当时一个在西边的山里,一个在东部的海边,很少往来。随着经济发展,各地的时空距离也逐渐缩小,生产和销售两头的人们才开始更加密切地相互交流起来,催生了严格意义上的“熟普”的诞生。无论天然还是人工,后发酵打开了普洱茶的市场,奠定了普洱茶的受众基础,甚至一度有人提出,只有熟普才能叫普洱茶。
由生变熟的发酵带来了千差万别的风味,但现在的普洱茶并没有当年“金瓜贡茶”那样“一茶定音”的权威标准。究竟什么才是好普洱,人们各执一词,难有定论。比如要看是不是大树茶、是不是干仓等等,区别方法数不胜数。与此同时,也有人试图鱼目混珠、以次充好,各种各样的消息满天飞。于是,普洱的江湖就这么诞生了。外边熟普的炒作热火朝天,但张静红发现,在普洱茶的老家,生普派始终在当地顽固地存在着,而这正是理解鱼龙混杂的普洱江湖的钥匙。
不过,先别急,我们在解码普洱江湖之前,先来看看普洱市场和武侠江湖有什么共同点。张静红说,主要是三点,理想与风险并存,强调个人技能,派系林立。
第一点,就是有不少普洱茶的茶客和侠客都一样,心里保持着对某一个江湖大义的理想。有很多茶客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村里能找到一口令自己心满意足的好茶。但正如每个侠客对大义的理解都有细微的差别,茶客对好茶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对茶的品鉴能力更难分高下。更别提偏偏就有那么些小人,在本已复杂的市场中以次充好,以新充旧,更让市场难以评估风险。茶客们一起喝茶时看似其乐融融,一不留神就会变成一场内功切磋:到底谁更懂茶?谁才能把这片好茶收入囊中?张静红特别强调,最重要的是,对方有没有骗我?俗语云,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就算最熟悉普洱的老茶客也会承认,很少有人能完全不被骗,这也是困扰普洱市场的一大顽疾。
这也就联系到了第二点,强调个人技能。就像大侠们行走江湖都必须身怀绝技,武艺高强,茶客们也相信在鱼龙混杂的市场中必须靠自己才能立足。侠客靠功夫,茶客靠嘴上功夫,这不是说他们靠耍嘴皮子,而是靠品茶的能力。茶客们相信,别人说什么山头、用不用农药化肥、是不是纯料,都是别人说的,真不真,一尝便知。
而第三点,就像金庸江湖里总有几大门派,这些茶客也有不同的品茶标准,门派林立。比如根本的生普、熟普,按产地还有版纳派、思茅派、临沧派,再细分还能有易武派、勐海派,还有干仓派、湿仓派,储藏产地也能分化香港仓、台湾仓、云南仓,原料能按茶树种植类型分成大树茶、台地茶,按茶叶用的位置、按用叶芽和叶杆的比例也能分。江湖有名门正派,比如市场监管部门、茶文化名人、大品牌等等,但也并不能“一统江湖”,还是有小门派和游走江湖的独行侠,按自己的理解去追求“最正宗”的普洱茶。
好,那么我们回到易武,来讲讲为什么普洱会形成一个复杂的江湖。
事实上张静红2007年在易武扎根做调查的时候,经过几年间的持续观察,她发现易武人的确依然做生茶、喝生茶,而且拒绝机械化、工厂化,近乎顽固地坚持不做渥堆发酵的熟普。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前面提过,易武当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就不做茶饼了,只给茶厂供应毛茶,也和云南其他地方一样从未接触过熟普。另一个原因,正是易武人意外发现自己在普洱江湖中竟然有一席之地,而外界垂涎的独门秘笈在当地竟早已失传。这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又倒退回上世纪九十年代,普洱的炒作热潮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一帮台湾地区的“茶疯子”决定到普洱的原产地去“朝圣”“寻宝”,他们到的就是易武。张静红找到了当时那批人,也寻访了他们在易武见过的人,揭开了易武茶时隔半个多世纪重新复苏的内幕。早在1994年,那帮台湾茶客到了云南后,却听当地人说普洱茶不在易武,普洱茶都是在昆明、勐海的茶厂里出来的,可他们手里明明就有易武的老茶饼。经过一番曲折和颠簸,他们终于到了易武,发现这就是个穷山村,“号级茶”时代的石磨压制法在当地已经近乎失传。但他们又发现,石磨还是留了几个,而且周围山上仍然有茶树资源,再加上手里还有一些真正的易武老茶做示范,找到一些曾经参与过压茶的老人,还有复苏的希望。而当易武人了解到自己祖上的茶饼,在台湾地区很受欢迎, 比云南本地卖得好多了,更加有了重振祖业的兴趣。
以此为契机,易武马上办了一个临时学习班,模仿老石磨,重新制作了新石磨,重新开始用传统的手工办法制作茶饼,直销给台湾、香港的客户。
正是因为有着特殊的历史,易武人确立了自己的品牌原则,那就是做生茶、做石磨手工压制茶。与之相对的,是邻近的勐海。虽然气候和地理条件类似,但是易武在山里,勐海在平原,易武产生茶,勐海产熟茶。在上世纪初,作为集散地的易武在做手工茶,勐海就已经建立了茶厂,但在茶叶贸易中的地位并不如易武重要。但后来勐海因为有工厂,还在更湿热的平原,适合发酵,易武的毛茶反而送到勐海的茶厂做成熟茶,世人只知勐海,不知易武。
到了现在,易武还是以小作坊为主,遍地个人经营的茶庄,而勐海则到处是茶厂。易武人觉得,易武的制作方法比渥堆发酵更干净,更天然,更传统,味道更柔,卖出天价的“号级茶”老茶饼就是自然发酵,易武味才是普洱茶味的正本清源。他们开始修博物馆、写书,想尽一切办法,证明易武普洱是“正山”,证明易武的普洱也是有历史、有文化的真普洱。
说到这,你可能已经明白了。我们可以说,易武对生茶的坚持,是结合历史打出市场区分度,同样是在用市场的认可反过来为自己正名。普洱除了纯粹的经济价值,还提供了一个文化象征,一个身份认同的符号。对易武人来说,当然是自家的普洱才是正宗的,这也是一百年来与勐海相互竞争的冤家故事的一部分。
而同样的故事,当然也在勐海、在云南各地发生着,比如思茅就为了争取普洱正宗的认可直接改了名字。为了让普洱的历史更受认可,1989年学者们提出了“茶马古道”的名称,生物学家们也发现茶可能起源于云南,还有人提出要把普洱作为新一类茶。2006年时,云南质监局甚至提出给普洱一个官方定义。归根究底,其实都是为了把普洱打造成云南文化的一张名片。
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从物质匮乏中逐渐走出来的人们迫切需要重塑自己的文化身份,恰好普洱又同时蕴含了巨大的经济和文化价值。于是,各派人等争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市场份额,更是一份对家乡、对自己的文化认可。这就是普洱江湖各派的缘起。正是因为普洱不仅仅是关于钱,所以人们更要争夺“正宗”的话语权。这也就是普洱江湖上的麻烦之处,人们争的不仅仅是真假,不是纯粹为经济利益而炒作。勐海和易武产的都是真茶,但是谁更真?更能代表普洱茶?这注定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不过,我们要记得,普洱江湖不仅仅是文化,也意味着许多隐患。
正是在2007年,随着思茅改名普洱,普洱在全国的热度达到了巅峰,到处都有人炒普洱。在易武,毛茶的价格从前一年的一斤一百多元,逐渐上涨到了四百多元。比如广州芳村的茶叶市场,普洱涨价是以小时计的。就在有人后悔自己买的不够多的时候,普洱市场却突然崩溃了。
当年6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档节目,叫《普洱茶泡沫破了》。节目说,普洱正在经历两场地震,一场是当年6月思茅发生的一次6.4级地震,造成数十人伤亡,另一场就是普洱暴跌的市场地震。节目不但揭示了当时市场上最受认可的两个品牌有大量假货冒充,还解释了商家如何制造紧缺,炒作茶价。很多普洱茶商宣称是支持传统文化的举措,比如“越陈越香”的产品宣传,节目批评这是文化炒作的一部分。当时一个月之内,几万元的茶饼就只剩几千元,甚至跌破了出厂价格,有些茶商一下亏掉了几百万元。
张静红总结,普洱茶的起起落落,是因为在普洱的历史变迁中,人们不仅仅把普洱茶当成一种饮品。又因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大众开始有了高于物质享受的文化需求,要有文化的寄托。再加上市场的营销宣传等因素,逐渐形成了如此热火朝天的普洱江湖。在传统文化作为主要卖点的市场中,文化价值与商品价值重叠,既有人们对茶叶文化的需求,也难以撇开商品本身的经济本质,于是一些茶叶从业者和消费者们就都以“正宗”为旗号,展开文化和市场的双重争夺,形成了一种特殊市场形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江湖。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过犹不及”,普洱成为热卖商品后,有更多人认识到普洱茶的好,不可否认有真诚的茶客对更高品茶境界的追求,更无法忽视的是别有用心的炒作,这正是江湖的双刃剑,对文化的不同阐释赋予了江湖多元性,也加深了江湖的危险。
这也是江湖的一个特点,总是有些混乱,这就意味着必须有质量监管。
现在的质量监管标准迭代到了“SC”标准。我国有普洱茶国家标准,对普洱茶的质量、生产工艺、包装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各地普洱茶产区也有相应的地方标准,规定了当地普洱茶的特点和质量。而且,普洱茶生产企业需要获得相关监管部门颁发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接受对生产环境、设备、卫生条件等等的审核和监督,才能合法生产和销售普洱茶。
普洱茶,需要在安全监管和保留市场活力的平衡中,才能获得比较健康的稳步发展。
讲到这,也就到了尾声。
我们做个总结,普洱的变化其实深深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百年来的深刻变迁:存放了百年的老普洱,用茶汤串联起了古人与今人,深居山中的普洱茶翻山越岭到香港,又漂洋过海到宝岛,再回到原先的山村里,印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流动路线。
普洱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能品尝味道、解腻消食、补充营养,还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和文化价值,形成了一个富有味道的市场江湖。这本书并不是要教会人们什么是正宗,而是呈现给我们一段历史,也就是一种茶叶文化,如何围绕普洱茶的“正宗”慢慢形成。对你来说,你可以不被“正宗”束缚,更大胆地去尝试各种茶,重点或许不是茶,而是一起喝茶的人。
这本书还讲了张静红和茶客们一起探索茶的很多故事,我只讲其中一个。一次,她以茶会友,品尝一款2002年产的易武茶,结果尝出有些涩口,反而朋友带来的2007年春天的易武新茶,更加令人惊喜。她这么形容:“花蜜香明显,水路细软,冰糖甜压过轻微的涩苦,回甘生津不断”。大家喝完以后面面相觑,难道越新也会越香?2002年的老茶未来能达到八十年前“同兴号”的口感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交给时间,慢慢品味。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普洱茶,需要在安全监管和保留市场活力的平衡中,才能获得比较健康的稳步发展。
-
不管是熟普洱,还是“越陈越香”的观念,其实都不是古来有之的传统,而是近几十年间形成的普洱江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