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余生》 朱步冲解读
《漫长的余生》| 朱步冲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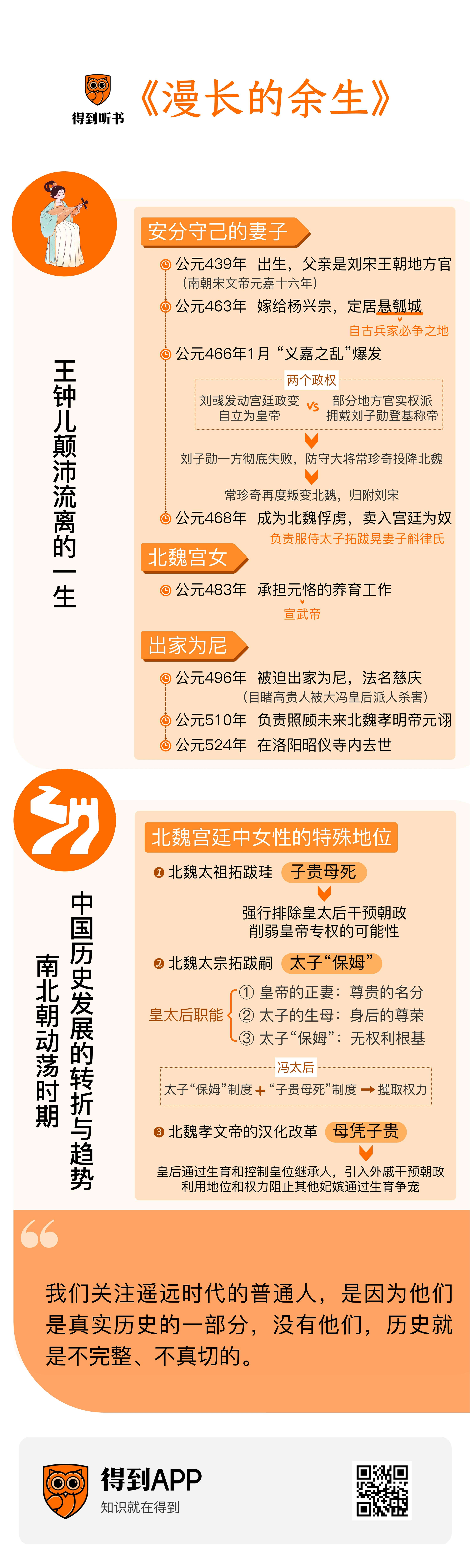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历史学者罗新的《漫长的余生》,副标题叫“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通过书名,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本关于北魏时代历史研究的著作,但它的主人公并不是什么大人物。罗新老师告诉我们,本书聚焦的,是北魏时代中期,一位宫女王钟儿的一生。她原本是一位生活在南朝的官员之妻,在南北朝动荡的大时代背景下,被掳掠至北方,最终在北魏皇城中,度过了长达56年的漫长时光,这也是本书书名“漫长的余生”的来历。今天的我们,通过阅读这本小书,也许能够深刻地理解,历史大变局与个人命运之间那种细微而紧密的联系。
20世纪20年代,王钟儿的墓葬,在洛阳郊区的邙山被发现,并出土了一部保存完好,概括了她一生的墓志铭。如果不是这寥寥七百多字的记载,王钟儿的一生,很可能就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作者罗新老师曾对我说:“为什么要把王钟儿这样一个小人物当作主人公呢?我觉得这是现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新要求,我们有责任把普通人、边缘人和小人物带进历史的聚光灯下。只有这样,我们看到的才是更丰富更立体的历史,而不再只是帝王将相的故事了,因为历史事实上是所有那些活过的人共同塑造的。”
当然,作者罗新撰写这样一本历史著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抽丝剥茧一般地还原1700年前,一位宫女的生平事迹,而是要以这样一个近距离旁观者的角度,去理解当时北魏王朝中一场绵延许久,影响重大的体制改革:它的最终完成,标志着北魏这个由草原骑马民族建立的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而逐渐接纳了中原华夏地区的种种制度与文化。当然,这种接纳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斥着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就连皇城后宫中的女性,也由此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宫斗”。而王钟儿这个历史小人物的命运,也不可避免地牵扯其中……所幸的是,由于自己曾经身为两位北魏皇帝保姆的特殊身份,和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王钟儿幸运地存活下来,得以寿终正寝,并且留下了关于自己的记载,为我们从侧面观察这段历史变局,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新鲜的视角。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解读这本《漫长的余生》的主要内容,在第一和第二部分中,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本书的女主人公王钟儿,在南北朝对峙的动荡时代,分别在南方故土和北魏的宫廷中,度过了怎样颠沛流离、跌宕起伏的一生,见证了北魏皇室内部,哪些刀光剑影的权力斗争与冲突。而在第三部分中,我将带着大家放宽视野,结合王钟儿的经历,谈谈北魏时期的政治斗争,尤其是鲜卑人的草原政治传统,如何与中原文化习俗冲突、融合,并为日后全新的隋唐时代,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王钟儿长达八十六年的人生,如果以她生活起居的地点,以及身份地位的变化为参照,可以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三个阶段:安分守己的妻子、北魏宫女、出家为尼。那么接下来,我就结合这本《漫长的余生》的内容,为大家简要叙述下,在距今大约一千七百年前,适逢南北朝乱世的王钟儿,如何在这种大变局的裹挟下,度过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王钟儿,出生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439年。可惜,由于墓志铭篇幅有限,并没有告诉我们,王家当时居住于何地,只是说,她的祖上籍贯和门第,能够追溯到汉晋时代的名门望族,太原王氏。王钟儿的父亲,是刘宋王朝的一位地方官。墓志铭上说,王钟儿从小就体现出大家闺秀的特质,性格温敏柔顺,举止得体。二十四岁那一年,她离开了父母,奉命成婚。这个丈夫也选得很好,门当户对,叫杨兴宗,在豫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境内做官,官职是主簿,是当地行政长官手下掌管文书的副手,后来也被擢升为一个郡的太守,当了地方上的行政一把手。
婚后,王钟儿就和丈夫一起住在悬瓠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汝南县县城。在墓志铭里,她的生活是很充实又幸福的。她把内外亲族的关系,以及各种家庭事务处理得很好,而且道德方面也无可指摘。当然,古代的墓志铭,主题是要为逝者尽量说好话的,甚至会拔高,所以我们今天也不是很清楚,王钟儿的婚后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不过,即使王钟儿过得和墓志铭里说的一样安宁幸福,那么这种生活也仅仅维持了两年。随后,王钟儿就和刘宋王朝一起,迎来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剧变和灾难。
这场剧变,发源在距离王钟儿一家千里之外的刘宋王朝首都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一场骨肉相残的宫廷政变迅速蔓延到全国,最终把北方的强敌北魏,也卷了进来。
原来,公元464年7月,南宋王朝的孝武帝刘骏去世,登上皇位的,是年仅十六岁的太子刘子业。根据史书记载,年轻的小皇帝刘子业精神可能不太正常,而且凶残好杀,搞得刘宋朝廷上下人心惶惶。终于,在公元466年1月,小皇帝的叔父刘彧发动了宫廷政变,杀掉了刘子业,自立为皇帝,然而这个时候,又有一部分地方官实权派,拥戴刘子业的弟弟刘子勋在寻阳,也就是今天的九江,登基当了皇帝:刘宋王朝一下就陷入了惨烈的内战,史称“义嘉之乱”。
一下出来了两个皇帝,那各地的宋朝文武官员,自然面临一个残酷的站队问题。悬瓠城,位于南朝刘宋和北魏的边境附近,是刘宋王朝在淮西地区防御北魏南侵的重要军事据点,位于汝河的南岸,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属于兵家必争之地。而防守淮西的刘宋王朝大将常珍奇,不幸站错了队,站到了刘子勋这一边。结果,义嘉之乱,以刘子勋一方彻底失败而告终。穷途末路的常珍奇,只好投降北魏,但后来又觉得北魏未必会真心接纳自己,于468年再度叛变北魏,归附刘宋。然而刘宋这边的援军还没抵达,北魏大军就已经杀到,常珍奇全军覆没。王钟儿的丈夫,是常珍奇的下属官员,大概就死于乱军之中,而王钟儿就和千千万万的随军家属一样,成了北魏的俘虏,踏上了北去的漫漫长路,最终抵达北魏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随后王钟儿被卖入宫廷,成了一名奴隶。此时,她刚刚年满三十岁。
在北魏宫廷体制下,宫女分为五等,最高的官位名叫内司,品级为一品,宫女入宫后,都是从最低级的女奴做起,慢慢积累年资,寻求一个向上攀升的机会。在今天考古学家发现的北魏宫女墓志里,有相当一批人,和王钟儿遭遇相似,她们都是在北魏攻占淮西和淮北时,掳掠来的官宦人家女子,大概也都受过一定的教育。这样的背景,显然对她们在宫廷里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相当的优势。
从这时开始,身为宫女的王钟儿,就在平城开始了她人生中的第二阶段。那么,王钟儿在北魏皇宫里负责什么工作呢?墓志铭里介绍得比较简单,就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她负责服侍太子拓跋晃的妻子斛律氏。如果斛律氏长寿的话,那么王钟儿的人生可能就会在这位主子身边平淡而安稳地度过,大概也不会有机会升到高位,享有一篇赞美和追溯自己生平的墓志。然而,命运的齿轮,在不声不响中已经开始转动。虽然对于北魏宫廷高层的权力斗争,王钟儿可能一无所知,但很快,它的影响就将降临到王钟儿头上。
公元483年,也就是北魏太和七年四月,四十五岁的王钟儿迎来了一位新主子,高贵人。这位贵人叫高照荣,她的丈夫,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后来改汉姓为元宏。此时,高贵人已经有喜,为了照顾这位怀孕的贵人,王钟儿这样资深的宫女,就被调配到她身边伺候。很快,高贵人顺利生下了一位皇子元恪,日后顺利登基,成为北魏的宣武帝。 根据墓志记载,自元恪出生后,王钟儿就承担起了相当一部分皇子的养育工作,日子久了,这位未来的宣武帝,自然对王钟儿产生了一种类似亲情的依恋。
然而,如同今天宫斗剧里的固定套路一样,我们的主人公王钟儿刚刚幸福稳定了没几天,就又遭遇了变故和不测。公元495年10月,北魏孝文帝正式下诏,决定迁都洛阳,这是他规模浩大的汉化政治改革的重要举措,直接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反对派在故都平城的势力连根拔起,尤其是摄政多年的冯太后。第二年春天,平城的文武百官、皇室亲贵,连同六宫嫔妃,就开拔动身,前往新都,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南下队伍。但是,当他们走到今天河南新乡,距离洛阳已经不远的时候,一名神秘的刺客就在半夜潜入了营地,杀害了高贵人,而在她身边服侍的王钟儿,估计也曾在第一时间,目睹了这触目惊心的凶案现场。
杀害高贵人的幕后凶手主使是谁呢?原来是孝文帝的另一位宠妃,日后还当上了皇后。这位宠妃也姓冯,是冯太后哥哥冯熙的女儿。冯太后为了让自己家族的荣华富贵绵延不绝,采取了一个策略,就是不停地把自己家的年轻女性塞进孝文帝的后宫;根据史籍记载,冯熙一口气,竟然让四个女儿成为孝文帝的妃嫔,真是保险之上还有再保险。在这四个女儿中,比较有出息的,是二女儿和三女儿,她们都先后坐上了皇后的位置,为了便于记载,历史上就把她们分别称为大冯和小冯;而对高贵人下毒手的,就是姐姐大冯皇后。
大冯皇后之所以要杀害高贵人,是因为自己刚入宫不久,还没享受几天孝文帝的恩宠,就不幸得了传染病,被迫出宫,暂时退出了后宫之争。不过等到她病愈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妹妹小冯,不仅占据了自己的位置,还收养了一个皇子元恂,随即被立为皇太子。不甘心失败的大冯,决定发动后宫之争,赶走妹妹。于是,在她的布置下,皇太子元恂就被塑造成一个反对父皇改革,不求上进,甚至图谋篡位的不孝子。最终,小冯皇后和元恂先后被废黜,而皇太子这个位置,就落到了元恪头上。不过,儿子元恪的天降之喜,对于生母高贵人却是杀身之祸。这是因为,大冯皇后的最终目的,是要效法冯太后,通过控制下一任皇帝,来实现自己对北魏朝政的操纵,所以,她必须迅速让自己当上皇太子元恪的养母。这样一来,元恪的生母高贵人,就只有被肉体消灭这一条路了。
高贵人的死,必然牵连所有依附于她的势力,王钟儿自然也不例外;根据墓志,已经五十七八岁的王钟儿,被迫出家为尼,法名慈庆。不过幸运的是,她并没有离开洛阳皇城大内,而是被安排在皇城内的一所寺院,时间,大约是在公元496或者497年。
然而,大冯皇后志得意满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孝文帝感觉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无可撼动,自然想到要建功立业,在外开疆拓土。于是,他亲率大军,目标直指南方的南齐王朝,目标就是夺取江淮之间南齐占据的战略缓冲地带,让长江,成为北魏和南齐之间真正的疆域分界线,双方划江而治。
孝文帝的军事行动一开始很顺利,但随着战线的推进,北魏军队南下的势头逐渐减慢。此时,孝文帝很可能也在征战中身患重病,在王钟儿曾经生活过的悬瓠城一待,就是五个月 。而正在此时,首都洛阳的宫廷里硝烟再起,孝文帝的妹妹陈留公主等人,给孝文帝送来了密信,称大冯皇后权欲熏心,不仅试图像当年冯太后一样干预朝政,还在后宫作法诅咒皇帝。很明显,这一招非常奏效,它唤起了孝文帝心中最隐秘黑暗的记忆和恐惧,从此疏远了大冯皇后。
公元499年3月,孝文帝再次抱病率军出征,走到今天河南邓州附近,因病去世。临终前,孝文帝做出了一系列人事安排,为太子元恪确立了辅政大臣班子,并且下令让大冯皇后自尽。
皇太子元恪继位后,自然会感怀自己的生母高贵人,同时提拔自己母亲的亲戚,作为一种迟来的补偿。于是,高贵人的兄弟高肇等人,就平步青云,高肇的侄女,元恪的表妹高英也入宫成为嫔妃,后来变成了皇后。但是,高英非常凶悍,嫉妒心强,几乎不让元恪接触其他妃嫔,导致元恪很长时间内没有一个儿子来当继承人,好不容易,有一个后进宫的妃嫔胡氏,偶然怀孕。
见到自己后继有人,元恪非常高兴,但同时生怕高英对胡氏母子下手,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班子,来对胡氏母子进行照顾和保护,其中就有已经七十一岁高龄的王钟儿。元恪之所以选择王钟儿,首先是因为童年的养育之恩,让他对王钟儿有一种天生的信任和依赖。其次,王钟儿出家多年,肯定和现在皇宫里任何派系都没有什么瓜葛。不仅如此,为产妇胡氏选择的休养安胎地点,也高度保密,同时为胡氏选拔的乳母,也都是来自宫外的新人,以便杜绝被人收买,加害婴儿的可能。
终于,这个婴儿在妥善的照看与保护下,逐渐长大,这就是未来的北魏孝明帝元诩。由于办事细致妥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钟儿依旧陪伴在元诩左右。墓志铭上也称赞说,王钟儿虽然年纪老迈,但是对照顾皇太子依旧是尽心尽力,从未懈怠。我们可以想象,这是王钟儿晚年最耗费心力的一件事,元诩这个襁褓中的婴儿,多少也应该在她心里唤起了一些属于尘世间的亲情与活力。
王钟儿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也许就是公元519年,一场在北魏皇陵中举办的迁葬典礼。此时,王钟儿已经八十一岁,宣武帝已经去世,元诩登基,胡氏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临朝听政的胡太后。胡太后为了自己未来的名分,以及满足儿子元诩对于父亲的孝心,宣布以皇后的规格,把高照荣的灵柩迁移到孝文帝陵墓的近侧。
此后的时光,对于暮年的王钟儿来说,如同夕阳,逐渐暗淡下去:曾经的故交,也一个个地去世,宫廷内外的权力斗争,也与她毫无关系,而生命本身,似乎已经毫无值得留恋之处。正光五年,也就是公元524年的四五月间,王钟儿在洛阳昭仪寺内,静悄悄地逝去。为了展示自己对王钟儿的眷恋和恩宠,政务繁忙的孝明帝,在四月底,还特意来到昭仪寺探望这位幼年时照顾过自己的老保姆,并亲自监督医官煎药。 我们不知道,此时的王钟儿,在病榻上逐渐陷入弥留之时,脑海中到底还在想些什么,是否会想起遥远的故乡、早逝的丈夫,或者深居北魏皇城内几十年里,经历过的那些人与事。
好了,王钟儿八十六年跌宕起伏的人生,我就为你基本讲述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再来放宽视角,看看王钟儿在北魏宫廷中的经历,折射出哪些南北朝动荡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与趋势。
如果回首王钟儿在北魏宫廷中度过的后半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岁月充斥着血腥残酷的权力之争,而北魏宫廷中的后妃和其他贵族女性,是这场权力游戏中不可或缺的主角。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参与宫廷斗争,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就是为了生存。所以,要理解这种特殊现象存在的原因,我们就必须了解一下,北魏宫廷中女性的特殊地位,和北魏王朝权力的独特安排模式。
对于草原上的骑马民族来说,部落首领通过联姻来壮大部族势力,是一种常见的习俗,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部落首领的妻子,往往能够凭借自己出身氏族的实力,对部落内的各种政治事务,施加很强的影响力。不仅如此,如果她们能够为部落首领生下男性继承人,那么继位之后,年少的新首领由于地位不稳,威望不高,也会把母后和妻子出身的联盟部落,看作自己重要的外援。
而北魏王朝进入中原后,为了对日渐扩大的领土进行有效统治,就必须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巩固皇帝自身的权力,削弱其他势力的干扰。所以,作为昔日盟友的皇后一族,也变成了皇帝重点防范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北魏太祖拓跋珪,就发明了一种残酷的制度,“子贵母死”——也就是通过先立太子,再赐死太子生母这种血腥的手段,来强行排除皇太后干预朝政,削弱皇帝专权的可能性。
北魏王朝发展到了中期,依靠强大的武力,逐渐统一中国北方。这个时期,也是北魏努力抛弃自己原有的草原游牧文化传统、全面向中原王朝模式转型的时期。拓跋珪的儿子,北魏太宗拓跋嗣,就通过糅合两种文化传统,演化出一套系统性的措施,进一步有效防止皇太子的生母干预朝政,那就是把皇太后的职能和权力一分为三:皇帝的正妻,真正意义上的皇后,不孕育皇位继承人,只有一个尊贵的名分;而太子的生母,则在太子名分确立之后被赐死,新皇登基之后,再被追封为皇太后,享有身后的尊荣。而抚育太子的任务,则给了保姆。保姆的人选,由皇帝本人从后宫妃嫔宫女中亲自选定,被选定的保姆大多身份低微,有的还是由于家族犯罪遭遇牵连,才被迫入宫,在皇城中没有权力根基,所以对日后的新皇帝影响也有限。 所以,本书的主人公王钟儿,之所以最终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篇墓志铭,很大程度上就要归功于拓跋嗣的制度设计,让身为宫女的她,能够以保姆团队一员的身份,参与抚养幼年时代的宣武帝、孝明帝。
不得不说,拓跋嗣这一套顶层设计,确实管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的四任北魏皇帝,都是以皇帝长子或长孙身份继位,地位相对稳固,然而,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冯太后,却一手打破了这个看似稳固的制度。
冯太后从小在北魏宫廷中长大,学习过中原文化典籍,为人精明果断,野心勃勃,最终攀上了权力的顶峰,而她的具体方案,就是利用拓跋嗣发明的太子“保姆”制度,把“子贵母死”变成自己控制未来皇帝,攫取权力的有力武器:在公元467年,未来的北魏孝文帝元宏刚刚诞生,冯氏就急不可耐地除掉了元宏的母亲李贵人和外公李惠,把元宏的抚养权抢到了手。在北魏史书里,对于孝文帝的评价,经常是说他非常孝顺,但是,这个孝顺的对象,却是和他毫无血缘关系的保姆皇太后冯氏,由此可见冯太后的心机缜密和深谋远虑。 而冯太后的侄女,我们在上一部分中提到过的大冯皇后,也效法姑妈,在孝文帝迁都洛阳途中,杀害了王钟儿侍奉的高贵人,成为皇子元恪的养母。
北魏孝文帝,在历史上的最大功绩,就是推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北魏的后宫妃嫔制度,也被这场改革波及。冯太后的两个侄女被立为孝文帝的皇后,不但能生下儿子作为皇位继承人,更不用再担心遭遇“子贵母死”的命运,这预示着拓跋嗣当初苦心孤诣设立的制度,一步步被逐渐破坏:皇后不但可以通过生育和控制皇位继承人,引入外戚干预朝政,同时还能够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阻止其他妃嫔通过生育和自己争宠。 正如我们之前讲到的,宣武帝元恪继位后,善妒的皇后高英就能够施展自己的影响力,让皇帝长期没有后嗣,幸亏妃嫔胡氏秘密生下了皇子,终于解决了北魏王朝的继承人危机,也让本书的主人公王钟儿原本落寞的命运,再次逆转:她对宣武帝的养育和照顾,谨慎细致的性格,以及超然于权力斗争之外的身份,让她得以重返宫中。
刚才我们讲过,王钟儿最后一次出现在北魏皇室的公开活动场合,应该就是宣武帝的生母,高贵人的迁葬仪式。在此之前,那位善妒跋扈的宣武帝皇后高英,就已经和昔日的王钟儿一样,被迫出家为尼,这标志着北魏皇室,已经彻底接受了中原文化传统:所谓母凭子贵,面对身为皇帝生母的胡氏,高英即使拥有皇太后的尊荣头衔,也无法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只能选择退出历史舞台。
当然,对于这些,身在局中的王钟儿,虽然亲历了整个过程,却依旧是当局者迷。在内心深处,她估计只会在落难时诅咒命运的不公,而在局面翻转时,惊诧于自己的幸运。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这一波波的乱局,从根本上说,是北魏从草原部落政体,逐渐蜕变为中原正统王朝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和反复,也是内亚文明和华夏文明在融合中不可避免的冲突与博弈,为日后辉煌的隋唐大一统时代,打下了基础。正如日本历史学家川本芳昭所说,从东晋到南北朝这一段中国历史,虽然充满了分裂和战乱,但一个全新的“中国”也逐渐诞生。从此,中国的疆域,就突破了中原这个狭窄的地理单元,而变成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在接纳了中原文明和制度后,原本中原地区周边的民族,也变成了中国的一员,同时给原本的华夏文明,注入了全新的元素。
好了,这本《漫长的余生》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著名历史学者胡鸿曾说:“历史学家在关注宏大时代脉络之余,驻足体味一下那些远离历史舞台中心的普通人的人生或许能对遥远的时代增加一份了解之同情。” 作者罗新本人,也在本书后记中特意强调: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
本书的篇幅,不到20万字,并不算长,然而读起来却有一种厚重感。罗新老师对我说,为王钟儿撰写一部传记研究著作的念头,早在20多年前,在研究北魏王朝子贵母死制度的形成和流变时就萌生了。最终,他花费了三年时间,断断续续地完成了本书。
王钟儿在北魏皇宫中度过的半个世纪,恰恰是北魏王朝将都城从平城,迁移至洛阳,决定转型为一个中原传统型王朝的关键时期。而在这个动荡的转型期,“子贵母死”这个维持皇权稳定传承的野蛮制度,既被身处高层的宫廷女性用作打击对手,掌握权力的武器,它本身的保留与否,也是北魏政权内部高层斗争的焦点。本书主人公王钟儿自身的命运和见闻,则为我们从侧面观察这段历史变局,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新鲜的视角。
纵观历史,北朝由于建立者的民族特色,让妇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享有前所未有的活跃地位。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唐代中前期,以武则天自立为帝,建立武周朝为标志,达到巅峰。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钟儿既幸运,又不幸。她在30岁时被北魏军队所掳掠,卖为奴隶,原本相夫教子的人生戛然而止。然而,在后续56年,所谓“漫长的余生”中,却因为北魏宫廷政治制度的特色与安排,得以接近权力中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挥了自己的影响,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也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以更加鲜活直接的方式,触碰她的生活以及那个久远的时代。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原书的电子版已经为你附在最后,欢迎你进行拓展阅读。此外,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著名历史学者胡鸿曾说:“历史学家在关注宏大时代脉络之余,驻足体味一下那些远离历史舞台中心的普通人的人生或许能对遥远的时代增加一份了解之同情。” 作者罗新本人,也在本书后记中特意强调: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
-
本书主人公王钟儿自身的命运和见闻,为我们从侧面观察这段历史变局,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新鲜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