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贝与贝币》 王朝解读
《海贝与贝币》| 王朝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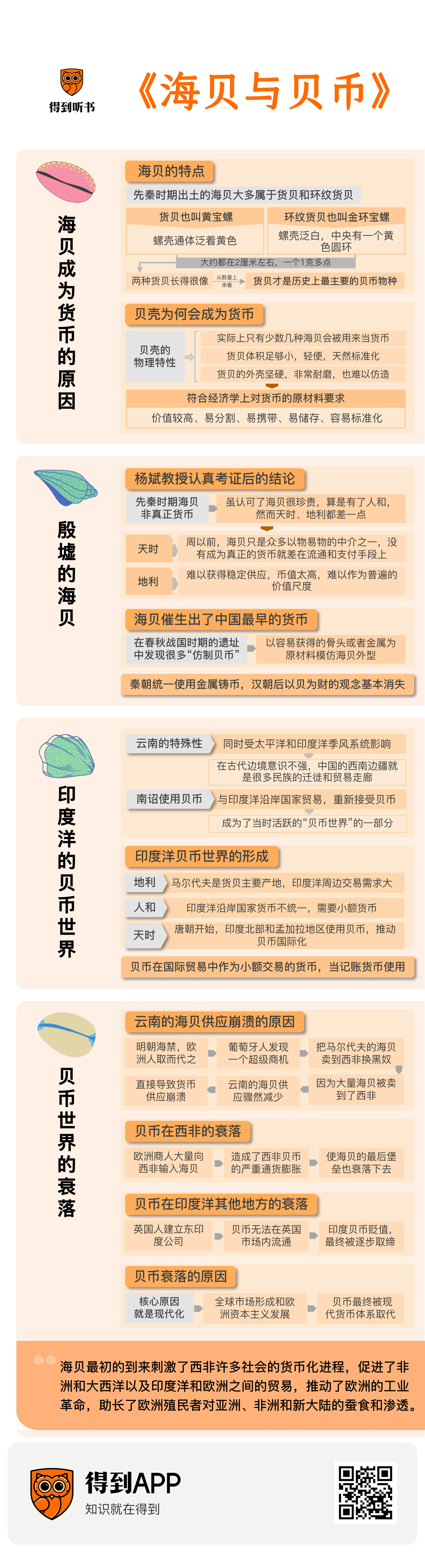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要讲的《海贝与贝币》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和遥远。但是你仔细想想,今天我们还有很多“贝”字旁的字都与财富有关,比如财富的财,还有赚钱的赚、资本的资、货币的货,等等。甚至,我们还会把特别珍贵的东西,直接叫做“宝贝”。你可能也听说过,在金属货币的时代之前,贝壳曾经也被用作货币,而且历史非常久远,连我国商朝的殷墟里都出土过大量贝壳。
事实上,海贝和中国的联系还不仅仅是财富,“中国”这个词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字记载,其实就是因为海贝。你可能听说过“中国”这个词最早是见于“宅兹中国”这句话,但你可能不知道背景。话说西周成王五年,周成王向宗室贵族中的小辈训话,其中有一个叫何的贵族,为了纪念这件事情,铸造了一个青铜尊,后世称为“何尊”,上面的铭文有这么一句话:“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意思就是周武王攻破了商朝国都,就宣布今后要在“中国”住下来,从这里治理百姓。这里的“中国”,指的是当时理解的天下中心,也就是在国都周围的区域。但是,古人不知道“中国”的记载对后世有多么重要,对他来说只是被天子训话,为什么要专门铸造青铜器作为纪念?原来铭文后面还写着,训话完还赏赐了30朋贝壳,让何觉得这事儿特别重要,专门做礼器纪念。所谓三十朋,总共就是三百个贝壳,就这么一些小贝壳,就能让宗室贵族感到意义重大,可见古代海贝价值不菲。
但是,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为什么贝壳能代表财富,甚至成为货币?随随便便就能捡到的货币,不会通货膨胀吗?贝壳当货币的时间持续了多久?为什么后来贝壳不再被用作货币了?其实这些问题,在历史上也曾困扰过不少学者。从西非的几内亚湾,到中国的云南山区,世界各地都发现过不少可能用作货币的贝壳,但是似乎相关的文献却特别稀少。
本书作者杨斌老师,别出心裁地把这些线索串联到了一起,拼凑出了一部以贝壳为中心的全球史。他发现,世界各地的贝币,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属于一个以印度洋为中心的经济和贸易体系,这个体系里的人们虽然距离遥远、人种不同、语言不通,但都不约而同地使用着贝币作为贸易结算手段,可以被称为是“贝币世界”,因此,贝币也可以说是最早的世界货币,而且还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货币。
杨斌老师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师从美国历史学会前任主席帕特里克·曼宁,先前听书也解读过他的讲中国和印度洋历史的《人海之间》,其实这本《海贝与贝币》才算是他的“成名作”,集中体现了他在海洋史,特别是在印度洋历史方面的历史研究成果。本书最近刚刚也是荣获亚洲图书奖在人文、社科、科技领域的年度最佳图书奖,颁奖词中总结了本书的四个特点:第一,资料多,包括中、英、泰、法多种语言文献;第二,时间长,从新石器时期到二十世纪中期,涵盖数千年;第三,空间广,包括四大洲和三大洋;第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海洋史、贸易史、货币史和全球史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贝币世界这一新的概念,为全球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在书中,作者特别强调了贝币虽然曾经在历史上分布极其广泛、存在时间特别长久,但现在却似乎被人遗忘了,书中最后一句,作者直抒胸臆地感叹说:“海贝和贝币,对塑造我们的世界是如此重要,遗憾的是,几乎无人能够欣赏。”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作者一起从历史的海洋里打捞起这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填补这个遗憾。首先我们从中国开始,看着海贝的脚步跨越欧亚大陆、印度洋、大西洋,成为串联起新、旧大陆的媒介,最后又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步步走向消亡。
好,在把眼光投向更远的地方之前,我们先搞清楚我们说的海贝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特点。
相信很多人听到贝壳能当钱用,就会想,那如果我穿越回去,随便到海边捞点花甲、河边捡些河蚌,就能发家致富,成为古代富豪?还真不是这样。先秦时期出土的海贝,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用来当货币的海贝一样,大多属于两个物种,也就是货贝和环纹货贝。
这个货贝,也叫黄宝螺,螺壳通体泛着黄色,而环纹货贝也叫金环宝螺,螺壳泛白,中央有一个黄色圆环,形状和大小都和货贝极其相似,大约都在2厘米,一个也就1克多点,而现在流通的1元硬币都有6克重。这两种货贝长得很像,不过,从数量上来看,货贝才是历史上最主要的贝币物种。这两种海贝分布都很广泛,东到太平洋的夏威夷,西至东非印度洋沿岸的莫桑比克,中间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一大片温暖海洋中都广泛分布着无数小小货贝。
那么,小小贝壳为何会成为货币呢?
首先要看的,当然还是物理特性。经济学上对货币的原材料要求,有这么一段经典结论,价值较高、易分割、易携带、易储存、容易标准化,我们可以一一对标。
价值上,你可能会说,可能贝壳虽然一眼就看得出美观、贵重,海边那么容易就能捡到,岂不是很容易通货膨胀?你会发现,实际上只有少数几种海贝会被用来当货币,而且早期使用货贝的人群,都会从背后再开一个孔,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拿来使用的。
我们再讲易分割。贝壳当然是不易分割的,但是易分割的要求,其实是说在交易中容易使用,方便重新称量出相匹配的重量和价值,而货贝体积足够小、轻便、天然,特别适合应付小额交易的场合。尤其是货贝个体之间的差距特别小,天然地实现了标准化,而不需要再切割、加工、重铸。
还有一项,易储存。在我们印象中,贝壳似乎是轻薄、易碎的,其实多多少少是因为大多数人日常见到的贝壳大多都是海滩上冲上来的碎片。实际上,货贝的外壳坚硬,非常耐磨,表面上的花纹和颜色经久不退,也难以仿造。
可以说,货贝有着得天独厚的生物特性,实在是一种使用门槛特别低的天然货币。当然,这只是物理性质,一种原材料最终成为货币,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等条件共同发挥作用。比如,由于在海边更容易获得,价值不够高,很容易猜想使用贝币的社会应该更多在内陆地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海贝是如何成为货币的。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中国的海贝与贝币。开头讲过,“中国”这个词在历史上的首次记录,就与赏赐贝壳有关。从考古研究中,我们还知道,在殷墟、三星堆等等大型遗址中都有大量海贝出土,也有铭文记载用海贝交易土地等等。有很多学者据此推测,先秦时期的中国大地上,海贝已经成为中国最早的货币之一。
但是,杨斌教授认真考证之后,得出结论,先秦时期中国的确把海贝当成“宝贝”,但是还不是真正的货币。我总结,先秦时期的中国人已经认可了海贝很珍贵,算是有了人和,然而天时、地利都差一点。
所谓天时,更准确地说,在周以前,中国普遍都还未进入货币经济时代,海贝只是众多以物易物的中介之一。我们知道,货币需要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而海贝就差在流通和支付手段上,因此没有成为真正的货币。
如果结合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记录,会发现中国的海贝使用是在西周时期逐渐成熟,开始把海贝作为价值尺度。比方说之前说过的何尊铭文,里面提到过“朋”作为贝壳的数量单位,其实在商朝的甲骨文中就有这个字,意思就是两串贝壳,一串有五个,一朋就是十个。后来两串贝壳就延伸为陪伴,朋就有了“朋友”的意义。很多青铜器铭文写到,天子赐给某贵族多少朋海贝,为了纪念此事,就做了这件青铜器。也有铭文记载,某两个贵族交换一大批物品,其中某物价值多少朋,于是做这个青铜器感谢促成交易的人。
可以说,海贝此时在周朝的传统礼法关系当中有重要的礼仪作用,而且在贵族之间也充当了价值尺度,但是最大的疑点是,如果海贝是先秦时期就广泛流通的货币,按理说应该在当时的生活区遗址中出土,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有学者对出土海贝进行统计之后发现,它们大多都是所谓的“葬贝”,也就是墓葬之中所发现的,而且还有一个时间越晚、随葬海贝越多的趋势,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随葬海贝比较罕见,一次也就几十个,商代墓葬中除了殷墟的妇好墓以外葬贝数量也不多,到了西周墓葬才逐渐变得常见起来,而且数量也多了起来。
换句话说,海贝在西周时期可能是未来货币的最强候选者,但就差一口气。
为什么差这一口气呢?就是缺乏地利,难以获得稳定供应,币值太高,难以作为普遍的价值尺度。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中原地区,算上更加内陆的四川三星堆、云南古滇国遗址,会发现离海也近不了多少。前面说过,中国出土的海贝大多是货贝,黄海、渤海、东海太冷,只有南海适合货贝生存。而奇怪的是,从南海到刚才说的各大遗址之间,中间广大地域居然没有多少海贝遗存,反而是从中原向西,一直到内陆的西伯利亚都有海贝遗址。也就是说,中原海贝很可能并非从南海传入,而是主要从西边传入。
这条路线也被学者称为“海贝之路”,它比丝绸之路更古老,终点在中国,回程一路上绕开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经过欧亚内陆大草原,就来到了印度洋上以出产货贝闻名的马尔代夫。如此遥远的旅途,也注定海贝在内陆价值太高,只能在贵族之间流通,在大额交易中发挥一下功能。
有趣的是,正是因为海贝既是普遍认可的价值尺度,又因为稀缺而无法成为普遍的支付手段,反而催生出了中国最早的货币。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仿制贝币”,以容易获得的骨头或者金属为原材料模仿海贝外形,比如楚国盛产铜,就做了“铜贝”。还有一些不像海贝的刀币、布币,有些上面也会有一个“贝”字。而随着秦朝以来统一使用金属铸币,这种以贝为财的观念,在汉朝之后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就基本消失了。
不过,古代中国还有一个地方后来又重新开始使用贝币,就是云南地区。虽然从秦汉将云南纳入中央政权统治范围以后,古滇国的贝币迅速消失,但根据唐朝时期文人记载,云南地区的南诏政权在近一千年以后又重新开始使用贝币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说到这,我们也得稍微讲讲云南的特殊性。和中国其他地方不同,云南气候同时受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季风系统影响,地形上和东南亚山水相连,地貌复杂,在古代边境意识不强的时候,中国的西南边疆就是很多民族的迁徙和贸易走廊。
前面说到的南诏重新“发现”贝币,不是他们模仿古滇国搞起了“文艺复兴”,而是因为当时的南诏处在中华文明圈和印度文明圈的交界地带,他们在和印度洋沿岸国家贸易的过程中,重新接受了贝币,成为当时活跃的“贝币世界”的一部分。
山那边的印度洋的贝币世界是怎么来的呢?也还是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先讲地利。前面说过,货贝的主要产地,就在印度洋的马尔代夫。别看这个马尔代夫都是些小岛、小环礁,现在以旅游胜地闻名,当年它可是货贝的最主要产地,堪称贝币世界的“中央银行”,是贝币世界中货贝采集和出口的公认主要地区。相较其他地方,马尔代夫群岛出产的货贝除了品种纯、数量多以外,体型还尤其小,特别适合携带。而且,印度洋周边市场有庞大的交易需求,马尔代夫作为中转站,有很大的货币使用需求。不过,可想而知马尔代夫当地不使用海贝作为货币,而是作为维持海船航行稳定的压舱物,顺便运往其他地区,满足当地交易需求。
说到这个交易需求,我们再来讲人和。虽然印度洋沿岸有不少文明古国,但问题就是,有点太多了,不像有统一金属铸币的中国,各个政权之间的货币不同,想要进行国际贸易,往往还得想个统一的结算手段。其中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缺乏金属矿和金属冶炼技术,难以铸造自己的货币,以至于很多地方还会通用中国铜钱。如果是大额交易,使用贵金属货币还算能接受,但在高频、小额的交易场合中,就需要另一种更通用、更容易分割和携带的小额货币,填补这个生态位的,就是贝币。但贝币要想走到这一步,还得先有认知基础,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国家把贝币当作主要货币,使贝币在流通中建立起一定的国际认可。
所以最后,我们说说天时。虽然无法确定具体时间,但是大约在公元5世纪到7世纪之间,距离货贝产地有一定距离的印度北部开始使用货贝作为金银以外的补充货币。在7世纪中叶,唐玄奘西行求法,他对天竺的记录中,就有当地人交易时使用金钱、银钱、贝珠的记载。此时,贝币虽然已经具有小额交易的功能,但还不足以获得国际影响。
真正把贝币推上国际贸易前台的,是印度东部孟加拉地区的两代王朝,波罗和塞纳,他们大约在公元8世纪到12世纪先后在孟加拉地区建立了强大的王国,不仅促进了印度东部、东南亚和中国西藏地区的佛教交流,还使孟加拉地区成为印度洋贸易中的重要环节。巧合的是,波罗和塞纳统治时期都没有自己铸币,原先的铸币名称变成了计量单位,直接折合成贝币,在实际的贸易、税收、政府俸禄等等经济活动中都大量使用贝币。当地人把本地盛产的稻米运往马尔代夫,大量用来压舱的货贝被当成货币流入孟加拉市场。当地的贝币交易如此活跃,以至于出现了专门的海贝兑换商,进一步向周边贸易渗透。
这个时期,恰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开通的时间段,整个印度洋沿岸的跨国贸易在这一阶段空前活跃,周边文明大多也都到了货币经济时代。到这,算是集齐了天时、地利、人和,于是,印度洋沿岸各地,都逐渐接受了贝币,有一些是作为本地区金属铸币以外的平行货币,也有一些直接把贝币当成记账货币使用。比如说在现在泰国区域,13世纪时有一个素可泰王国,当地人留下了很多记录日常生活的碑文,有不少贝币的记载。有这么一块碑,说有一个女施主买了价值500万枚海贝的花园,又捐了20亿枚海贝给寺庙,考虑到数字庞大,实在已经超出了人工清点的能力,也对马尔代夫海底的软体动物的生殖力要求太高,大概就是一种记账方式。在更北一些的兰纳王国,当地法典中也有不少用海贝缴纳罚款的条文,比如辱骂别人的人要被罚款33000枚海贝。元代有一个航海家汪大渊,记录过泰国地区一万枚海贝价值约等于元朝24两中统钞,也就是2.4两白银,是同时期云南海贝价值的两倍,可见泰国白银之稀缺。
之所以要讲泰国的案例,是因为泰国很可能就是云南接触到印度洋贝币的通道。自从元代开始逐渐把云南纳入直接统治之后,朝廷基本上都接受云南贝币、金属货币、纸币混用的现状,不但民间使用海贝进行土地、房屋交易,就连朝廷都直接接受海贝缴税,或者用海贝发放俸禄,关于云南贝币使用情况的文献记载也越来越多。从这些文献中我们会发现不少云南与贝币世界的关联。比如文献记载,当时云南贝币俗称为“巴”,这里的“巴”可以写作两个字,都是左边一个贝字旁,右边一个巴西的巴,或者数字八的八。都取用“巴”这个音,是因为泰语中海贝读作bia。而且云南还有一种特别的海贝计数方式,用的单位是“索”,根据元代文献记载,“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也就是说,一索为80个海贝。云南的这个计算方式,其实和孟加拉、暹罗的海贝计数方式一样,都是以4乘5乘4为基础,被杨斌认为是贝币世界中各地联系的一大有力证据。
但是,在明清易代之后不久,云南通行数百年的贝币体系在几十年内就迅速崩溃了,而同时期的贝币世界非但没有同时衰落,实际上反而前所未有地向西扩张范围,不但涵盖了西非,还接触到了新大陆,迎来了巅峰时期。不过,云南贝币的崩溃其实是整个贝币世界崩溃的预演,马尔代夫人还无法意识到,那些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的人,也会是埋葬他们财富的人。
好,我们把视角从云南转回马尔代夫,讲讲贝币世界衰落前的最后辉煌。从唐朝到元朝,不少中国人都会经过马尔代夫,中国人也曾非常详细地描述过马尔代夫的地理和人文情况,但是从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海禁愈加严苛,中国基本上再也不走印度洋商路。取而代之的是开辟了新航路的欧洲人,特别是热衷黄金、香料和贸易的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留下了很多关于印度洋贝币世界的记录,对当地货币体系的理解也是完整而精准的。比如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节托梅·皮莱资就曾经记录下孟加拉和马六甲之间货币和海贝的详细换算体系,推算出一枚孟加拉银币相当于8960枚海贝,而一单位马六甲锡钱大约等于44枚海贝,也就是一只肥鸡的价格。
事实上,葡萄牙人当时不仅熟悉印度洋,也很熟悉整个环非洲航线。他们凭借自己独一无二的跨大洋贸易知识,发现了一个超级商机:可以把马尔代夫的海贝卖到西非换黑奴。在16世纪之前,就已经有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将海贝卖到西非腹地,比如有文献记载,16世纪西非内陆城市廷巴克图使用“来自波斯帝国的海贝”作为货币,但是他们的路线要经过撒哈拉沙漠运输,数量较少,只有同时了解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的葡萄牙人才能发现可以绕非洲航线,大量运输马尔代夫货贝换取西非的黑奴,而西非黑奴又能进一步被卖到美洲成为廉价劳动力,简直是一本万利。正是因为大量海贝被卖到了西非,云南的海贝供应骤然减少,直接导致货币供应崩溃,恰好当时云南铜矿也开始开采,朝廷可以在云南直接推行金属铸币,导致贝币退出云南历史。
此后,荷兰人、英国人等等欧洲列强也参与到海贝贸易之中,在后来工业革命开始后,西非主要货物又从黑奴变为棕榈油,总之欧洲商人在一百多年间大量向西非输入海贝,贝币世界沿着几内亚湾沿岸向内陆深入,席卷了整个西非。其中一大例证,就是以四和八十为基础的印度洋数贝壳方式,也在非洲的贝币体系中广泛存在,只不过西非的进制更奇怪,比如有些地方60或者80等于十进制的100,更令人困惑。
这种贸易也滋养了当地的王国,比如在贝宁湾,学者估算,出口总价值的20%—35%都是由海贝支付的,这些财富基本上都流入了当地酋长、国王的手中。于是,手握巨额财富的头人们也获得了扩张权力的本钱,一度建立起了让欧洲人头疼的新兴强国,例如达荷美王国。不过,巨额的黑奴和棕榈油贸易最终也造成了西非贝币的严重通货膨胀,比如整个18世纪西非从英国和荷兰进口的海贝总数超过一万吨,合计超过100亿枚,使海贝的最后堡垒也衰落下去。
而贝币在印度洋其他地方的衰落也与欧洲人有关。比如在印度和孟加拉,由于英国人建立东印度公司以后,将印度逐步殖民化,虽然殖民当局一开始也接受海贝作为贸易和缴税方式,但是贝币价值毕竟不在殖民当局控制之内,对殖民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更糟的是这些贝币无法在英国市场内流通,也就意味着没有产生任何能够反哺欧洲的利润,每年还要人工数贝壳,对英国人来说完全是累赘。通过不断调低官方货币与贝币汇率的方式,印度贝币不断贬值,最终也被逐步取缔。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概括贝币世界衰落的核心原因,那就是现代化。这里所说的现代化是全方位的,它包括了全球市场的形成,也包括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发展,出现了更加强大的政府组织形式和更有效的财政控制方式。在现代国家的冲击下,为了适应小额交易的贝币,反而因为面额太小变得低效,原来引以为傲的普遍流通性却在全球市场面前变成了地域局限性,最终被有国家背书的现代货币体系取代。
云南被重新纳入中央的货币体系之中,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中国近现代国家制度发展一部分。当时的元朝和明朝都已经学会了调动货币政策来打压海贝,比如调动外国朝贡和贸易储存下来的巨量海贝进入云南,促成通货膨胀,或者是将没有官方许可、走私进入云南的海贝称为“私巴”,通过严厉打击私巴流入以便控制货币价值。元明两代王朝面对云南贝币的困境和解法,其实和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如出一辙。
然而,16世纪以后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快的,还是欧洲人。在我看来,云南贝币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不是朝廷政策积累的水到渠成,而是可以说云南贝币在世界竞争中的失败,本质上是前现代经济败给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因为欧洲资本主义此时已经走在了前面,通过调动海贝参与更广阔的全球市场,欧洲人和马尔代夫人能赚到更多利润,云南的海贝流通才会逐渐衰落,导致明朝与海洋世界更加脱节。而随着欧洲殖民权力的不断扩张和巩固,马尔代夫人会逐渐发现,自己不仅丧失了海贝贸易的主导权,最终还会丧失主权和尊严。
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贝币在塑造我们的现代世界过程中有巨大的作用,作者总结,“海贝最初的到来刺激了西非许多社会的货币化进程,促进了非洲和大西洋以及印度洋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推动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助长了欧洲殖民者对亚洲、非洲和新大陆的蚕食和渗透。”
如果我们对贝币世界做一个概括,可以说是一种在各国官方铸币的缝隙中出现的世界货币,在一千五百余年的时间里跨越了地理、种族乃至精神上的局限,将三大洋、五大洲连接到一起。正是因为各地货币不统一,发展中的商品经济和跨洋贸易又需要高频结算,才会有贝币的生存空间。它就像比特币一样,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流通只能遵循价值规律,但却是一个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通行货币,戳中了当时国际贸易市场的痛点。要理解货币,光有以国家、文明为基础的传统历史视野并不够,还要到缝隙中寻找那些不擅长写书的商贩、远洋商人的视角,寻找那些不识字的水手视角,才能更好理解海贝与贝币的便利之处,并理解它的流行。从这个角度来说,欣赏贝币的历史,其实也是欣赏历史中那些边缘人物、边缘世界的历史。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书中其他内容还有兴趣,也建议你去阅读原书。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贝币曾是连接古代欧亚非大陆的世界货币,最早。它在中国、印度洋、西非等地区广泛流通,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发展。正是因为各地货币不统一,发展中的商品经济和跨洋贸易又需要高频结算,才会有贝币的生存空间。
2.从西域传入的印度洋海贝,深刻影响了先秦时期中国的经济生活和价值观念,虽然在中原地区未能成为真正的货币,但也催生出了中国最早的货币。
3.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概括贝币世界衰落的核心原因,那就是现代化。欧洲在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利用贝币推动了全球贸易,另一方面又最终导致了贝币体系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