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红票》 王朝解读
《康熙的红票》| 王朝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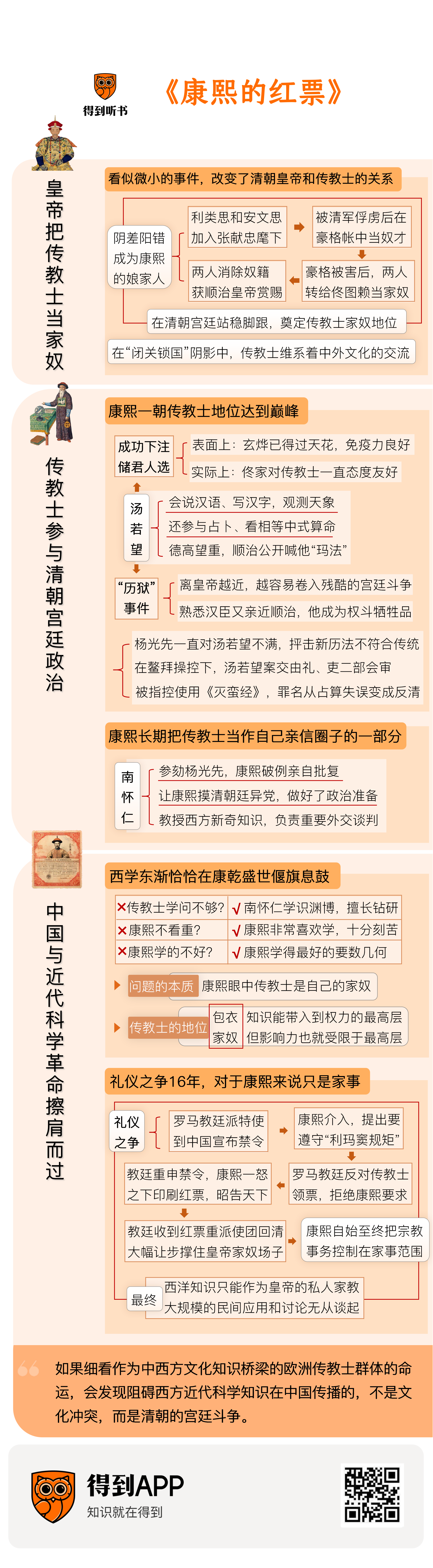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们讲《康熙的红票》,康熙我们很熟了,红票是什么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和收藏家们都和你一样感到困惑。
这个红票,是一封来自康熙的“公开信”,不是康熙亲笔书写,而是一份印刷品,但用五爪龙纹装饰边缘,还用了朱红色印刷,表明这是皇帝旨意,所以俗名叫“红票”。它的存世量仅有十几张,而且都在海外收藏,直到2019年,才在一次北京的拍卖会上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红票上书汉、满、拉丁文3种文字,大概就是说1706年和1708年有两批人奉康熙皇帝旨意去西洋,他们本来都是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士。结果这两批人都没有回来,而且除了到处流传、不知真假的消息,也没有正式文书寄回。康熙担心书信交流不够通畅,所以给西洋来的人都发了这张票,回欧洲的时候,把红票再带过去,表明这是皇帝的意思。最后落款的时候写着康熙五十五年,也就是1716年。而在拉丁文部分,又有十几个西洋传教士的签名。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这封信没头没尾的,为了什么事情派人去西洋?而这些人为什么又没有回来?康熙为什么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情,还要印一张公开信?为什么传教士要集体签名?好像都没有说清楚。最麻烦的是,所有大清官修史书都没有提到过这张红票,也就没有记载来龙去脉,所以这些谜团一直困扰着人们。
直到最近几十年,越来越多清宫档案重新被发掘出来,人们才逐渐意识到红票的意义。红票所说的事情,是康熙年间罗马教廷和中国皇帝的无形“交锋”,也就是后世所称的“礼仪之争”。当时罗马方面认为中国习俗违背教义,要求清朝天主教徒以后不能祭祖、拜孔子等等,而康熙反对这种看法,让传教士当自己的“钦差”,主动去跟教皇交涉。所以这张红票,是全球化之初中西交流留下的重要一页。
我们都听说过的“西学东渐”,在明朝就已经开始,也有很多著名的西方传教士,比如利玛窦、汤若望等等,这些传教士都能跟中国达官贵人们打成一片。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西学东渐这么早,而且这些欧洲传教士的地位都那么高,为什么明清中国还会和西方的科学革命失之交臂?以往我们谈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没有传开,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说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西方科学在近代中国水土不服。
我们再把方向反过来,你可能听说过,当时欧洲的莱布尼茨、伏尔泰等等大科学家、大哲学家都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尤其推崇康熙皇帝代表的“开明专制”,认为他善良仁慈,温和包容,欧洲的君主应该多跟他学学,推动欧洲的启蒙运动。那么,是谁让中国和康熙皇帝在启蒙时代的欧洲留下了这么好的形象?正是那批来华传教士。他们写了不少介绍中国的书,在欧洲出版以后成为畅销书,康熙那个“开明专制”的“人设”,也是他们打造的。
如果我们仔细看作为中西方文化知识桥梁的欧洲传教士群体的命运,会发现阻碍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不是文化冲突,而是清朝的宫廷斗争。这本书讲述的,就可以说是中西方大分流的一个前奏。
本书作者孙立天,是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博士,专精于清初的中西交流历史。这本书也得到了许倬云、罗新等老师推荐,对流传已久的“闭关锁国”“文明冲突”等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抽丝剥茧地把这段被尘封的历史还原了出来,让我们从双方的视角理解这段历史。他提出,传教士当时深深介入了宫廷政治,包括打倒鳌拜、九子夺嫡等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宫廷斗争当中,他们都有深度参与。当时的传教士误以为接触皇帝就能顺利扩大宗教影响,而清朝的几代皇帝却认为传教士只是自己的家奴,没有扩大传播的意思,最终就在西方开始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的关键节点,清朝成了欧洲推崇的模范,而陷于宫廷斗争中的清朝,反倒与近代科学擦肩而过。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几个传教士的经历为代表,重新认识明末清初对外交往和宫廷斗争相交织的历史。
刚刚说到清朝皇帝把传教士当成家奴,也就是所谓的“包衣”,这其实是理解这段历史的关键。
我们再把时间稍稍再往前一些,回到明朝后期。早在1582年,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达澳门,他画了一幅绘有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地图,引起了当时广东官员的兴趣,被破例允许买下一块地皮。于是,利玛窦意识到,想在中国顺利传教,必须得争取到上层精英的青睐。
要怎么样争取呢?利玛窦做了很多尝试,更加融入了中国文化。他开始学习中文,先换上了佛教僧侣的服饰,然后把自己的房子改成中国风。后来他发现中国知识分子都自称儒生,于是他又开始读四书五经,戴上四方巾,自称“西儒”,然后表现自己在数学、地理、天文等等方面的知识。在利玛窦的理解中,中国人的祭祖和祭孔不是宗教礼仪,不算崇拜异教神,和天主教的一神论教义不冲突。利玛窦这套适应国情的做法,后来就被康熙称为“利玛窦规矩”。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在利玛窦之前,基督教已经数次传入中国,比如唐朝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所称的景教,但都没有形成影响,直到利玛窦把天主教中国化,天主教才开始在中国形成规模。
后来,崇祯皇帝才会授意徐光启和西洋传教士合作修订明朝历法,结合了天文学观测,重新安排了节气的分布,奠定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农历”。但不幸的是,这套历法订立时,明朝气数已尽。
在明清之交,兵荒马乱,明朝士大夫们自保都来不及,哪还有心思照顾传教士,各个在华传教士只能各寻出路。其中就有两个既倒霉又幸运的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他们两人本来是在明朝末年来到中国,一直待在成都,但没多久明朝就陷入崩溃,后来他们又加入了张献忠麾下。按他们两人说法,张献忠有精神病,特别喜欢杀人,他们为了活命才不得不听命于他。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神父1648年被清军抓走时,并不是在宫中被俘虏的,而是在战场上中箭倒地,前来补刀的满人士兵一看是两个欧洲面孔,没有杀他们,而是带到了统帅的大帐中,让他们当了奴才。这位统帅,正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别看只是奴才,在满人八旗世界中主奴关系是最基本的阶层关系,努尔哈赤曾经说过,要形成“奴才爱主子,主子爱奴才”的社会,所以能够成为重要人物的家奴,实际上是很有利的身份。
然而,豪格打败张献忠后不久,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就以谋反的罪名逮捕了他,而豪格当月就在狱中被多尔衮害死。刚刚抱上大腿的两个外国神父,又一次失去了靠山。不过,他们的好日子马上就来了。
豪格死后,两位神父被转给了佟图赖。佟图赖是正蓝旗汉军都统,辽东佟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佟家是汉化的满人,还是满化的汉人,尚存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能兼顾满、汉两方,有学问,又有地位,比如努尔哈赤娶的第一位夫人就来自佟家,顺治帝后来也娶了佟家女儿。更重要的是,佟家统领的汉军旗大炮部队给清军立下过汗马功劳,陈寅恪称之为“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
在后金和明朝的战争中,西洋来的“红衣大炮”发挥了巨大作用,努尔哈赤就被红衣大炮炸伤,几个月后去世了。而红衣大炮的技术由传教士带入中国,先卖给了明军,后来又到了清军手里。佟家的佟养性,当时正是仿制欧洲大炮的负责人,后来成为汉军旗首领、炮兵司令。因为有了红衣大炮,清军火器技术实现了“弯道超车”,逆转了辽东战事的局势。恰恰是因为满人普遍知道外国人和大炮等等外国先进技术有关,两个满人小兵看到两个外国人的时候才知道不能再补刀,而是献给了豪格。虽然传教士们在自己的书中把这次死里逃生说是上帝显灵,其实该感谢的恐怕是大炮。豪格死后,和传教士关系密切的佟家,就把两个传教士接到了自己府内,当作佟家的家奴兼家教。经过佟图赖上下打点,两个神父先在1653年消除奴籍,又在两年后获得顺治皇帝赏赐,终于修建了自己的教堂。
作者认为,正是这个看似微小的事件,改变了清朝皇帝和外国传教士的关系。先前说顺治娶的佟家女儿,正是佟图赖的女儿,两人生有一子,就是未来的康熙帝。辅政大臣里没有佟家,但佟图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康熙的舅舅,佟国维和佟国纲都被安排进了侍卫处。这个侍卫处都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有随时能上达天听的特权。顺治定下的四大辅政大臣,原先就都在侍卫处有职位。佟家能进入侍卫处,代表的是康熙把佟家人当作自己的心腹,也不难推测,他对佟家府内的传教士们也不陌生。
如此,传教士阴差阳错地成了康熙的娘家人,在清朝宫廷中站住了脚跟,奠定了传教士在皇帝身边的家奴地位。在“闭关锁国”的阴影中,北京宫廷内的传教士们,维系着那个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不过,这份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如果说两个“思字辈”传教士比较陌生,那接下来这位就算大名鼎鼎了,他就是汤若望。早在利类思和安文思还在四川和他们口中的“精神病”张献忠周旋时,汤若望已经在北京入朝为官了。
与利类思和安文思的奴才路线不同,汤若望保持着明朝传教士的士大夫路线,他还担心这两个张献忠的罪臣入京,会影响传教,拒绝在自己的教堂中收留利类思和安文思,所以后来他们才不得不向顺治乞求土地修自己的教堂。
汤若望早在明朝就进入钦天监和徐光启合作编修历法,后来在李自成入京后、清军入关后都能获得礼遇,靠着成功预测1644年日食的准确时间,被清廷任命执掌钦天监。
可别小看钦天监,天象有时甚至能够影响朝廷决策。汤若望当时已经非常中国化,说汉语、写汉字,不仅观测天象,还参与占卜、看风水、看手相之类的中式算命,比如多尔衮想新修皇宫,满朝文武都阻止不了,反而是汤若望最后写了一道奏疏,说明代皇宫上合天文下顺地利,风水很好,而新的选址风水不行,占卜也不吉利。多尔衮听了之后居然回复说“你说的是”,沿用了故宫,可见汤若望意见之重。当时安文思反对汤若望算命,写信给罗马教廷告状,但最终罗马方面也选择了默许。
顺治皇帝在位期间,汤若望和安文思分别靠着自己的人脉向顺治展开“攻势”。不过十几岁的顺治皇帝自幼修习佛教,只对两人带来的知识和技术有兴趣。不同的是,汤若望算是德高望重,顺治会公开喊他“玛法”,就是满语的爷爷。相比之下,安文思只是当西洋器物的管家。但总之,清朝初年的传教士比明朝待遇好了很多,能够直接影响皇帝,像本书作者所说,“顺治皇帝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符号,反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可以一起谈话聊天的皇帝。 ”
不过,在清朝的政治制度中,离皇帝越近,权力的光环就越强,传教士因此很快就卷入了清朝残酷的宫廷斗争之中。
1661年,年仅二十三岁的顺治帝因天花病入膏肓去世。在驾崩前两天,顺治曾经召见汤若望,咨询储君人选,汤若望推荐了玄烨。虽然汤若望的理由是玄烨已经得过天花,有足够免疫力,但汤若望曾经在书信中写过,安文思和利类思归入佟家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佟家和自己的关系也很不错。这说明,汤若望一直清楚佟家对传教士的友好态度,所以他推荐玄烨的理由也可能是,他要推动一个利于传教士在清朝活动的皇帝即位。我们无法确定真正的理由,但这次成功下注,让康熙后来更加信任汤若望和他代表的传教士们。
然而,顺治宫廷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满人贵族担心过度汉化。顺治驾崩后,主张强化满洲传统的鳌拜得势,他甚至不准康熙学习汉字。而熟悉汉臣又亲近顺治的汤若望很快就成了权斗牺牲品,这就是有名的“历狱”事件。
当时有个叫杨光先的文人,也擅长占算,一直对汤若望不满。在1660年,也就是顺治十七年就上书抨击汤若望的新版历法不符合传统,甚至狭隘地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但当时顺治皇帝并没有理会。3年后,也就是康熙二年,杨光先再次上书,此时把持朝政的鳌拜敏锐地意识到,有了杨光先的技术意见,可以趁机除掉汤若望。
于是,在鳌拜操控下,汤若望案交由礼、吏二部会审,而且前后历经八个月。虽然常有人说汤若望案是中西文化冲突,但当时给汤若望定的罪名是认为他算命算错了,导致顺治宠妃董鄂妃的孩子下葬的时间、位置不对,八字不合,所以董鄂妃和顺治帝才会年纪轻轻却在两年以内先后去世,而不是因为他代表西洋文化。
审理过程中,汤若望和杨光先进行了极其专业的占算技术讨论,两人难分高下,而十几年前的下葬事宜又难以追究细节,最终汤若望被杨光先指控使用《灭蛮经》,传说中这是一本专门写给外国人的历法书,有意搞乱五行,以便使蛮夷“断根绝后”。这下罪名就从占算失误,变成了反清。最终汤若望和当时参与占算的人被判“大逆之罪”,要全部凌迟处死。
很巧合,不久后北京突发地震,人们纷纷议论说是判汤若望极刑激怒了上天。于是在孝庄太后和佟家的努力之下,汤若望最终免于凌迟,原本要被拆毁的北京教堂也获得了保留,但此时他已经中风,不久就去世了。
对少年康熙来说,这是一次绝好的宫斗启蒙,后来还利用此案扳倒了鳌拜。在汤若望中风以后,他的助手南怀仁负责辩护,而南怀仁又与安文思等人私交不错。1668年,年仅十四岁的康熙派人找到安文思、南怀仁等人,让他们找接替汤若望执掌钦天监的杨光先有什么历法错误。不久后没有任何官职的南怀仁参劾杨光先,而康熙破例亲自批复,发给议政王大臣会议审理,绕开鳌拜势力控制的礼部,这是他亲政后主持的第一案。更巧的是,就在此案前两个月,康熙安排了一队练摔跤的小伙子入宫,半年后这队人马把鳌拜捉拿归案。虽然杨光先案最后没有牵出鳌拜,但是康熙摸清楚了朝廷内谁支持鳌拜,做好了政治准备。而从南怀仁的信中也能看到,他很了解“杨”的背后是鳌拜,而少年康熙正在准备夺回权力,南怀仁还解释说,之所以给议政王大臣会议审理杨光先案,是因为康熙在那边有自己信赖的人。
此后,康熙长期向南怀仁和一众传教士学习西方的新奇知识,还让他们负责重要的外交谈判,比如中国与欧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尼布楚条约》。1689年,康熙让自己的心腹索额图和舅舅佟国纲负责谈判,实际和俄国人谈判的其实是名义上的翻译,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徐日升是南怀仁推荐进宫的葡萄牙传教士,当时已经是康熙一家的熟人,而法国人张诚当时年仅三十四岁,刚到中国不久,但是熟悉欧洲政治,所以康熙非常器重他。张诚知道俄罗斯此时和瑞典与奥斯曼帝国争夺出海口控制权已经焦头烂额,坚持更为强硬的谈判态度,拒绝了索额图的让步建议。此次谈判之后,俄国的彼得大帝觉得自己吃了亏,迁怒于两个传教士不帮欧洲基督徒,反而帮异教皇帝,一怒之下把张诚、徐日升所属的耶稣会驱逐出了俄国。
种种迹象表明,康熙长期把传教士当作自己亲信圈子的一部分。有了汤若望和顺治的君臣关系在先,再加上佟家传教士还是娘家人,康熙一朝传教士地位达到巅峰,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故事说到这里,我们来看时间,康熙一朝,从1662年至1722年,共61年,那时的欧洲,是路易十四、彼得大帝的时代,也是牛顿、莱布尼茨、伏尔泰的时代。然而,我们都知道,此后一百余年,欧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将清朝远远甩在了身后。传教士既然如此靠近康熙,不仅是利于他们传教,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说,更重要的是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占据了极好的身位,为什么西学东渐恰恰在康乾盛世偃旗息鼓了?
是传教士学问不够吗?不是。南怀仁学识渊博,不仅会天文,也会机械、数学等等。比起权斗,南怀仁其实更加喜欢钻研学术,他曾经设计过一辆蒸汽驱动的小车,比牛顿、瓦特都要早,而且还在清朝工部的帮助下造出过原型。
是康熙不看重吗?不是。康熙非常喜欢学习西学。比如1690年,除了九月、十月,每个月都要叫好几个传教士来教书。南怀仁甚至感叹,给康熙教书太累了,几十年第一次见到这么好学的人,就连平定三藩之乱期间都要学习。而且,他也会用西学,比如勘测疆域、绘制地图等等。
那是康熙学得不好吗?不是。他学得最好的要数几何,他还找了传教士一起重新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有代数学,我们现在说的“二元一次方程求根”,这里的元、次、根,都是康熙学习时确定下来的翻译。而且,后来传教士入华有些还经过他“面试”,他会考传教士熟不熟悉欧洲的音律,是六音还是七音,会不会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之类的。
问题就在于康熙眼中的传教士,是自己的家奴,是直属内务府的家人和亲信,他不想让他们的影响力扩大到满族贵族、汉族大臣们组成的外廷,而是留在内务府管理的内廷,也就是把“国事”办成了“家事”。包衣家奴的地位让传教士能够把欧洲最新的知识带入中国权力的最高层,但也让他们的影响力受限于最高层。
的确,有北京传教士打头阵,清朝出现了成规模的天主教信众,康熙年间全国估计有数十万。然而传教士的目标,是让清朝皇帝皈依天主教,像古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一样,一下子把整个帝国都转向基督教。可是康熙没有这样的想法,这在导致他发出红票的“礼仪之争”之中最为清晰。
前面简单说过礼仪之争的背景,是罗马要禁止中国教徒拜祖先,也正是康熙介入此事以后,他提出了传教士要遵守“利玛窦规矩”。以往我们看这件事情,可能二元地认为是两个文明碰撞的过程,导致天主教被排挤,其实仔细看过程,更准确的说法是康熙皇帝要给自己的家奴撑腰,避免自家的传教士被排挤。
实际上,这个礼仪之争在欧洲教会内部一直在争议,反而是中国这边的传教士很少理会。公平地说,中国人祭祖祭孔,心里不仅表示尊敬,多少也带着“求平安”的祈祷成分。如果非常刻板地理解天主教教义,这一点确实应该是存在争议的。不过,从利玛窦开始,来华的传教士基本上都来自耶稣会,这是一个专注往异教地区传教的团体,一般更看重天主教在中国存续,而不是所谓“纯洁性”,所以他们也更容易接受教义的本地化。
但到了康熙四十四年,也就是1705年,罗马教廷决定直接派特使多罗到中国宣布禁令。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所谓“圣教特使”突然来访,康熙知道其中有蹊跷。他一方面安排内务府接待多罗,当作家人的宾客来宴请,不强求三跪九叩,没把他们当成外国使节,另一方面直接问多罗和传教士有什么要交代,结果双方都不愿意直接把康熙卷入宗教内部争议,康熙也没有再问。然而实际上,当时两方私下矛盾非常直接,多罗当面贬低徐日升是“手艺人”而不是传教士。
在多罗辞行前一天,他向康熙请求写一封信,让他回欧洲的时候有面子,康熙比较迟疑,让他第二天再来。后来多罗回忆,当天下午,徐日升去见了康熙。第二天,康熙主动提起了礼仪之争,直接说如果天主教觉得教义可以和中国传统共存,就照样传教,调和不了,以后别传了,反正康熙自己认为可以调和。多罗以不懂中国规矩为由,两人没有继续深入讨论。从后来的记录来看,康熙没觉得这件事多大,还跟多罗索要了巧克力和西药,没有进一步强调礼仪问题。
作者认为,康熙介入礼仪之争,很可能就是耶稣会找上了皇帝,要皇帝给自己撑腰。实际上,后来耶稣会教士记录说,康熙知道耶稣会和教廷有冲突时曾对他们说,“我们就是养一条小狗,也不允许别人欺负,更何况是这些我小时候就在我周围,跟了我四五十年,我信任的人。”
后来他又接见了一个传教士颜珰,此人入华二十多年,被罗马教廷当作代表。结果,康熙刚聊两句,发现颜珰在中国那么久,中文还非常差,远比不上北京的传教士,勃然大怒,认为教皇被这种不学无术的人误导了,而且不知道中国地方上还有多少这种人,于是决定以后传教士都要经过他面试,宣誓遵守利玛窦规矩,永不离开中国,才能领传教证件。这个证还不是六部颁发,而是内务府,也体现了康熙把传教士当家奴的思路。
“领票”往往被认为是想要限制天主教,作者则认为,是康熙想要维护耶稣会,就像给司机发驾照一样,不是限制,而是规范。康熙就跟传教士宣传说,你们拿了这个凭据,地方官知道你们来历,这样百姓才会多多皈依。
然而,1707年罗马教廷让多罗传话,反对传教士领票,而且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反驳了康熙的要求,就连陪伴身边三十余年的老传教士徐日升也说自己因为多罗犯了头痛病,这下国事真变成了私事。康熙之后一边派人宽慰传教士,让他们不用担心,另一方面让人带话给多罗,说他“生事不已”,万一皇上生气了把传教士全赶走了怎么办?所以还是赶紧“悄悄回去罢”。
此时,康熙也决定把握主动权,1706年挑选了两个传教士当自己的洋钦差,代表他去罗马传达意见,结果两人都遭遇了海难。第二年,康熙见罗马态度强硬,又惦念起两位神父,询问为何不见消息,然后又派出两个传教士出使。其中有一个叫艾若瑟,后来的确见到了教皇,但教皇反对康熙意见,还要求他留在欧洲,不准返回。从1708年开始,康熙一边忙着立储大事,平息废立太子的混乱,一边也不忘叫沿海地方官员上报西洋来的人和物,敦促他们打听洋钦差们的下落。
到了1715年,教廷重申禁令,康熙觉得自己派出的使臣要么死了,要么不给回国,一份亲笔手谕都没有,还再发禁令,太不给面子。一怒之下,嘱咐内务府印刷“红票”,昭告天下,让往来中国的欧洲人都带去,让教皇给个说法。从教廷文件来看,1717年教廷收到红票以后,赶紧就见了艾若瑟,让他随新使团回清。不幸的是,艾若瑟途中染病去世,没能回朝复命。
不过,康熙对这次使团更上心,亲自和教皇特使拉扯了几个回合。先放重话说要禁止传教,还缉拿潜入北京的神父,吓住使团,然后一眼看穿对方有两手准备,直接让他们拿出妥协条款来,之后还让他们在北京吃喝玩乐,给足好处。1721年,在康熙的操作下,教廷大幅让步,变相同意了中国教徒继续维持传统做法,撑住了皇帝家奴的场子。
礼仪之争16年,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算得上“兹事体大”,而对于康熙来说,这却只是家事。作者认为,康熙自始至终都非常精准地把和天主教有关的事务控制在了内务府职责范围内。在清朝政治中,宫廷实行严格的内外分离,内务府的事情外人不得插手。所以,即便是实质上两朝互派来使,康熙都没有让外廷官员参与,最终,传教士带来的西洋知识,只能留在宫中作为皇帝私人学习的家教,大规模的民间应用和讨论也就无从谈起。
说到最后,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教士们后来都去了哪里?这就要说到九子夺嫡的大戏,大多数教士都把赌注压在当时比较热门的皇八子和皇十四子一派上,还有个传教士因为在京城给他们通风报信最后被处死。结果最后皇四子意外即位,是为雍正皇帝,他即位后立刻着手清除异己,打击其他皇子势力,他专门撤换了内务府人马,将传教士们赶出内廷。即位一年内,也就是1724年,雍正颁布禁教令。他的理由,可能是因为自称佛教居士,爱好参禅,也可能是因为传教士们太亲近其他派系,引起猜忌,也有可能雍正真的觉得教堂里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但总之只是皇帝家事,外人难以得知。
而同时期的欧洲已经是另一幅光景。在康熙在纠结废立太子和礼仪之争时,牛顿在1707年出版了《算术原理》,将代数应用了各种实际问题求解之中,而那时康熙在学习代数时还怀疑代数没用,让传教士搞清楚再跟他讲解。二十年后,雍正终于熬死了软禁中的皇八子,开始推行摊丁入亩和改土归流,而英国出版了《科技百科全书》,激发了流亡在英国的伏尔泰参与修编法国《百科全书》,宣言理性的时代终将到来。传教士和皇帝们都还没有意识到,就在紫禁城内宫红墙之外,历史的风向已经悄然改变。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书中其他内容还有兴趣,也建议你去阅读原书。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红票所说的事情,是康熙年间罗马教廷和中国皇帝的无形“交锋”,也就是后世所称的“礼仪之争”。
2.康熙眼中的传教士是自己的家奴,他不想让他们的影响力扩大到满族贵族、汉族大臣们组成的外廷,而是留在内务府管理的内廷,把“国事”办成了“家事”。
3.“领票”过去被认为是想要限制天主教,作者则认为,是康熙想要维护耶稣会,就像给司机发驾照一样,不是限制,而是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