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革命》 刘怡解读
《帝国与革命》| 刘怡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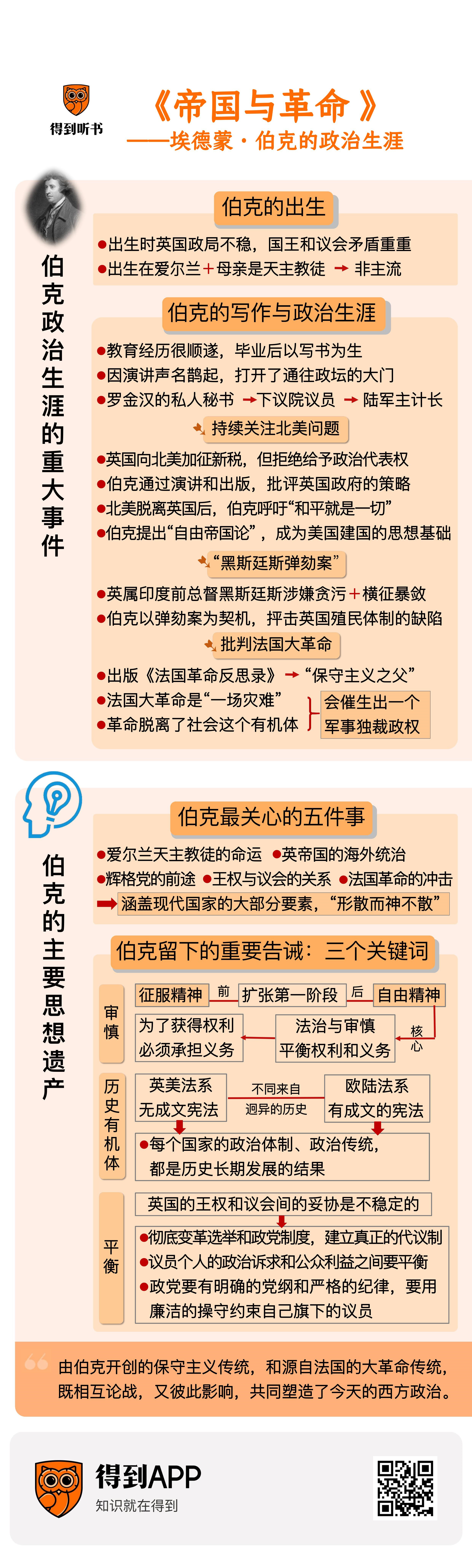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怡。今天我要为你讲的书,叫《帝国与革命》。这是一部1300多页厚,整整109万字的人物传记,可以说是鸿篇巨制。它的传主是谁呢?副标题里交代了,是埃德蒙·伯克,一位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伯克这个名字,你可能不太熟悉。但他在欧美国家,地位可是太高了。今天,你翻开任何一本英国或者美国出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里面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康德、马克思这些名字外,必提的就有伯克。伯克的姓氏后面,通常还会跟一句评语,说他是“政治保守主义之父”。英美两国的政治家,对伯克也非常推崇。丘吉尔尤其爱引用伯克的文章和演讲,他甚至说过这么一句话:“在英属爱尔兰诞生过的名人里,伯克是最伟大的一位。”
问题来了:“保守主义”在我们的印象里,可不是个褒义词啊。它总是跟因循守旧、抗拒变化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伯克这位“保守主义之父”,却备受景仰呢?原来,伯克的“保守”,不是说抵制一切改革和革命。他对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就持肯定态度。伯克真正反对的,是法国式的激进革命。他讲:要是一场革命不顾既有的规则和传统,完全按抽象理念来推行,那它一定会招来惨烈的后果。我们今天常说的“多数人的暴政”这个概念,最早也是伯克提出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克倡导政治审慎,批判法国大革命。“保守主义之父”的名声,就是这么来的。
那伯克的思想遗产,是不是只有这一项呢?当然不是了。本书的标题“帝国与革命”,可以说精准概括了伯克思想的两大支柱。为了应对18世纪末的新变化,他深入剖析了美国和法国的两场革命。为了让自己的祖国英国可以稳固统治下去,伯克还把目光投向国内,对议会政治、自由贸易和政党体制发表了大量见解。今天我们熟悉的“代议制”这个概念,它的思想基础就是伯克奠定的。伯克关于自由市场的论述,更是直接启发了哈耶克等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果你想了解西方政治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它的一些特殊规则有什么玄妙之处,那你绝对绕不开伯克这个人。
但是,伯克的思想,又相当难解读。他不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而是身体力行的政治行动者。在68年的人生里,伯克做过国会议员、大学校长和首相秘书,经历非常丰富。他虽然也写过几本书,但更喜欢发表演讲。这些演讲,往往引经据典,辞藻华丽,不过一旦脱离具体语境,就会非常难懂。所以,要了解伯克的思想,必须回到他的政治生涯,回到他那些演讲的时代背景。而这本《帝国与革命》,讲的就是伯克的政治经历。学完这本书,你不仅能系统地了解伯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你还会发现:近代以来的英美政治,其实一直受到伯克的影响。他可是太重要了。
巧的是,本书作者也姓伯克,他叫理查德·伯克,不过跟传主埃德蒙·伯克没有亲戚关系。理查德·伯克教授是剑桥大学一流的政治思想史学者,也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为了写好这本《帝国与革命》,他做了将近十年的准备,不仅重新研读了伯克生前的手稿,还追溯了伯克政治思想的缘起。本书英文版在2015年出版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还被英国《卫报》和《旁观者》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图书”。可以说,它是了解埃德蒙·伯克其人的最权威专著。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伯克曲折的政治生涯里,他经历过哪些重大事件,从中获得了哪些心得。在第二部分里,我会为你分析,伯克有哪些重要的思想遗产,这些遗产对我们理解今天的西方政治,又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开始讲述本书的内容以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伯克出生于1729年,你知道那个时候,英国的政局是什么样的吗?
这个问题,不是专业的世界史研究者,还真答不上来。我们对17世纪的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多少还有点印象,也知道英国从此走上了君主立宪之路。但你可能不知道,“光荣革命”之后的60多年里,英国的政局并不稳定。1714年,英国王位出现空缺,继承权落到了王室的德国亲戚、汉诺威的乔治手里。从此,英国进入了汉诺威王朝时代。这个王朝的国王,在当地没有根基,但非常希望效仿欧洲大陆的君主,掌握实权,这就和英国议会产生了矛盾。议会自己呢,内部也不团结。“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实际上只剩下一个执政党,就是辉格党。这个党的大多数国会议员,并不是通过真正的选举产生的,而是来自一些人口稀少、位置偏僻的世袭封地。由于缺少竞争,辉格党逐渐变得腐败不堪,内部也是派系林立,被几个贵族寡头把持了大权。可以说,当时的英国,正在酝酿新的政治危机。
埃德蒙·伯克,就是在这样一个微妙的历史节点登场的。他和我们熟悉的亚当·斯密、洛克、康德,属于同一辈人。但伯克的家庭背景比较特殊:他出生在爱尔兰,母亲是天主教徒,这两点在当时的英国都属于“非主流”。要知道,爱尔兰并不属于英国的核心统治区,它要到16世纪,才被彻底征服,可以说是英国内部的一块殖民地。天主教徒呢,在“光荣革命”之后,也成了政治上的边缘人,倍受怀疑和歧视。虽然伯克本人和他父亲一样,信仰主流的新教,但他从小就感受到了“边缘人”特有的恐惧与不安。伯克对“多数人的暴政”的反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不过,家庭出身并没有给少年伯克带来太多负累,他的教育经历还是很顺遂的。1748年,当伯克从爱尔兰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毕业时,已经精通希腊哲学、古代史和文学,文章也写得很好。伯克的父亲是位律师,他希望儿子能子承父业。但伯克自己,偏偏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法律工作。他性格奔放,爱好又广泛,更愿意当职业作家。于是,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伯克就待在伦敦,以写书为生。他写的可不是小说、剧本这样的通俗读物啊,而是讨论哲学、历史和政治问题的小册子。像这样的民间文人,在启蒙运动时期特别常见。伯克这个人呢,又有个特点,就是擅长引经据典。不管书的主题是宗教、美学还是欧洲史,他都能从遥远的古希腊开始说起,把线索理得清清楚楚,这很快让他声名鹊起。伯克在著书立说时积累的名声,还为他打开了通往政坛的大门。1765年,英国新任首相罗金汉侯爵任命伯克为自己的私人秘书,随后又帮助他获得了下议院议员的席位。伯克的政治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为什么民间文人伯克,能在政坛赢得一席之地呢?这和英国当时的风气有关。现代政党制度诞生以前,英国议会里的博弈,除了靠核心政治家在幕后运作外,主要是以演讲取胜。伯克自己就是天才演说家,又能帮其他人写讲话稿,这是很重要的加分项。伯克前前后后当了28年议员,最出彩的就是他的演讲。到了18世纪80年代,去议会听伯克跟人打“嘴仗”,已经成了伦敦上流社会的重要消遣。就连不懂哲学的贵妇人,也会为伯克的口才击节赞叹。
但是,伯克登上政坛的时间,又相当不理想。首先,英国在1760年,刚刚迎来了一位新国王乔治三世。这是一位年轻气盛,喜欢插手实际事务的国王。他不甘心做议会的傀儡,决心利用辉格党的派系矛盾和民间情绪,挑起政治争斗,这给政坛增加了许多变数。另外,伯克的“老板”罗金汉首相,根基也不稳固。罗金汉领导的派系,属于辉格党里的传统派,人望不高。他和国王的关系又很紧张,上任刚满一年就被赶下了台。直到1782年,罗金汉才再度受命组阁。等于说在中间15年里,罗金汉和他的秘书伯克,在政坛扮演的一直是反对派的角色,手里没有实权。
没有实权,不代表不需要表态。进入18世纪70年代,英国摊上了一件大事:它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当时的英国,刚刚赢得对法国的“七年战争”,海外殖民版图迎来了大扩张。但战争造成的财政紧张,也使英国政府变本加厉地搜刮财富,特别是对出口到北美的日用品征收新税。在北美当地的政商精英看来,自己已经在英国对法国的战争中,承担了繁重的义务,如今非但得不到回报,反而成了英国人的“提款机”,这绝对不合情理。因此,北美居民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这句话的意思是,英国要想从北美征收新税,就得承认北美和英国本土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允许他们选出自己的国会代表。乔治三世和他的政府,当然不肯答应。于是,北美的抗争逐渐升格为要求独立的运动,最后在1775年爆发了战争。
在北美问题发酵的几年里,伯克一直通过演讲和出版,批评英国政府的策略。他讲:英国自己的政治史,就是围绕征税问题和代表权展开的。北美会提出类似的要求,一点也不奇怪。毕竟,英国当初在北美开辟殖民地时,是承诺要给当地精英选举权的。现在大踏步后退,这是自毁形象。更何况,过去100多年间,英国政府已经从垄断北美的进出口贸易里,获得了巨额好处。现在要加征新税,这是贪心不足,会直接把北美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伯克反复强调,像英国这样的18世纪大帝国,跟曾经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它需要获得殖民地人民的接纳,才能使统治长期化。而接纳的前提,是宗主国对殖民地只有监管权,没有不受约束的强制权。这种模式,叫做“自由帝国”,是伯克的原创。站在今天的角度,这当然属于帝国主义思维,需要批判,但在当时却有一定进步性。北美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也很认同伯克的理念,后来还在首都华盛顿给他立了铜像。
但是,伯克一个人的口才,终究改变不了英国政府的决定。北美十三州还是在激烈的独立战争后,脱离了英国。这个时候,伯克又开始为收拾残局出主意了。他本人虽然不完全赞成北美独立,但明智地指出:继续战争,对英国有百害而无一益,“和平就是一切”。在伯克的呼吁下,英王乔治三世被迫在1782年重新任命罗金汉为首相,并在第二年签订了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条约》。伯克作为罗金汉的秘书,也获得升迁,当上了陆军主计长。这个官职是英国政府掌管陆军财政的首席大臣,地位不算高,但“油水”很足。不过,伯克并没有顺势大发横财。因为罗金汉上任刚满3个半月,就得了流感去世。辉格党随后正式分裂,陷入长达40多年的内讧,连带影响了伯克的仕途。伯克自己呢,注意力也不在升官发财上。1786年,他向下议院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查办涉嫌贪污的英属印度前总督黑斯廷斯。这就是英国政治史上有名的“黑斯廷斯弹劾案”。
伯克不是一直在关注北美问题吗,怎么又开始对印度上心了?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得回到本书标题里的第一个关键词:帝国。在伯克看来,像北美和印度这样的海外殖民地,虽然远隔千里,但战略价值重大。能不能治理好它们,是英帝国存续的关键。北美已经出了问题,印度绝不能重蹈覆辙。而黑斯廷斯这位总督,一贯横征暴敛,还企图把英国的法律制度强加给印度,这在当地引起强烈不满,已经损害到了英国的利益。伯克把自己视为印度人权利的化身,他要公开声讨黑斯廷斯以及长期把持印度事务的东印度公司,好让所有英国人认识到现行殖民体制的缺陷。
1788年2月,黑斯廷斯弹劾案在议会第一次开庭。伯克准备了厚厚一摞材料,做了整整四天的主题发言。许多英国贵族和普通市民都涌进会场,就为了一睹伯克雄辩的风采。有意思的是,黑斯廷斯自己也回忆说:“我盯着伯克看了半个小时,听他滔滔不绝地控诉我,内心觉得好像还挺有道理,我就是世上头号大罪人。”伯克的论点呢,还是他那套“自由帝国”学说。他讲:之所以要弹劾黑斯廷斯,不光因为他有贪污嫌疑,还因为他对印度的统治是不道德的。他随意勒索金钱,根据个人喜好制定政策,这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还会让英国的统治丧失公共性,沦为私欲的附属品。如果英国人再这么肆无忌惮下去,再不对黑斯廷斯采取惩戒措施,印度迟早会揭竿而起,变成下一个北美。
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伯克对黑斯廷斯的弹劾,不是一个简单的司法案件。他是把开庭变成了宣传个人主张的讲台,要跟他眼中那个不完美的殖民体制隔空对决。但这种做法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理论太多,证据太少。黑斯廷斯的盟友,马上抓住这个漏洞,硬是把弹劾事件变成了琐碎的司法审查。结果,整起案件居然拖了7年才做出判决,黑斯廷斯最终被上议院宣告无罪。那个时候,伯克已经退出政坛,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了。
不过,在去世之前的8年里,伯克还做了另一件大事,就是激烈批判法国大革命。正是这场批判,为他带来了“保守主义之父”的名声。1790年11月,伯克出版了酝酿一年多的专著《法国革命反思录》,在欧洲引起轰动,10个月里就再版了11次。在这本书里,伯克一反十几年前对美国革命的推崇,痛骂法国革命是“一场灾难”。注意了,伯克可不是在维护腐朽的波旁王朝啊。他讲:革命前夜的法国,像一座破败不堪的城堡,既不公正,也不仁慈。问题在于,满腔激情的革命者,除了拆掉城堡,把所有居民赶出去外,并没有能力建造一间新房屋。伯克宣称,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博爱”,只是一些抽象原则。它们脱离了法国社会这个有机体,也没能发展出相应的法律体系。这就像一个病人,明明最需要吃药,但革命者只强调“人人都有吃药的权利”,却开不出药方。更糟的是,抽象原则还会被野心家滥用,最终催生出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在这里,伯克提前好几年就预言了拿破仑的崛起。
《法国革命反思录》的出版,使伯克的政治声望再度回到高峰。一向不喜欢伯克的英王乔治三世,甚至提出要封他当伯爵。但伯克拒绝了这份恩赐,他退回自己的庄园,在写作中度过余生,直到1797年去世。伯克的好朋友、牛津大学教授劳伦斯哀叹说:“当他倒下时,欧洲乃至整个文明世界,都失去了最后的支柱。”
好了,以上就是本书记录的,埃德蒙·伯克的主要政治经历。听完这些故事,你可能还是很难理解,为什么伯克那么重要。他不就是一个唱了几十年高调,却没办成一件实事的书生嘛!论仕途,他没做过首相,也没能把辉格党改造成一个现代政党。论政见,他关于北美问题和印度殖民地的建议,基本没有被英国政府采纳。在法国革命问题上,伯克的许多主张,更是和他早年的论断完全冲突。马克思对伯克的评价就不高,觉得他一辈子都在见风使舵。
但是,同样有着曲折的政治经历,也同样擅长演讲的丘吉尔,一直在为伯克辩护。他讲,伯克的缺点,就是太一本正经,也太面面俱到了。他想对18世纪的英国政治来个大改造,连方案都拟好了。只可惜,四分五裂的辉格党给不了他全力支持,同时代的其他人也理解不了他的苦心。否则,伯克“本来会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
丘吉尔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得从伯克的主要政见来理解。终其一生,伯克最关心五件事,它们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命运、辉格党的前途、王权与议会的关系、英帝国的海外统治,以及法国革命的冲击。这五件事,刚好对应西方近代国家的五项基础:宗教和民政事务、政党制度、国内权力分配、海外殖民地,以及政权合法性。换句话说,伯克的思想,涵盖了现代国家的大部分要素,“形散而神不散”。后世的政治家,在琢磨其中任何一项问题时,都可以向伯克的著作求教。这就是为什么,伯克在生前壮志难酬,但进入19世纪之后,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推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伯克在阐述自己的主张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把它放在历史和法律的维度下展开。比如,在讨论“政治平衡”这个概念时,他会回顾英国历史上君主、贵族和平民三大势力的博弈过程,详细解释“平衡需要哪些条件才能达成”。在研究英国对印度的征服时,他会追问:除去暴力以外,英国政府和印度人之间,还形成了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里,英国要承担怎样的义务?像这种层层推进的探究,逻辑严密,当然也更有说服力了。
那么,伯克在他关心的五大问题上,留下了哪些重要的告诫呢?我们还是回到《帝国与革命》这本书的内容,为你做一下归纳。伯克的思想遗产,可以概括成三个关键词。第一个词叫“审慎”。这个词听起来很稀松平常,其实却大有深意。伯克从孟德斯鸠那里借来了一个概念,叫“征服精神”。它指的是:完全依靠武力兼并土地、奴役人口,放纵国家的占有欲。伯克认为,这种现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可以容忍的。像罗马帝国的扩张,还有英国早期的殖民历程,都是“征服精神”的化身。但他随后又强调,一旦扩张的第一阶段结束,“征服精神”就得让位于“自由精神”,要让帝国的每一个臣民,发自内心地愿意为帝国的利益服务。而“自由精神”的核心,不是放纵,是法治和审慎。
自由意味着审慎,这听起来跟我们的一般印象,差别很大吧。为什么伯克要这么说呢?原来,伯克说的“自由”,不是个体层面的精神自由,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他讲,“自由”这个词本身很抽象,不好界定。它只有在跟具体的权利联系到一起时,才有可行性。为了获得权利,必须承担义务。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就需要审慎。比如,北美殖民地承担了纳税义务,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利,那它的反抗就是正当的。英国政府则犯了不审慎、不节制的错误。反过来,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首先就是它不审慎。它倡导的政治自由,是漫无边际的,势必会引起动荡。哈耶克对伯克的这种自由观,评价就非常高。
伯克留下的第二个关键词,叫“历史有机体”。这个词听起来很抽象,但放到18世纪英国的语境里,就好理解了。我们都听过“英美法系”和“欧陆法系”这两个概念,也知道英美法系更重视判例。其实,这种区分不仅存在于司法领域,在宪法问题上也是一样。英国就没有成文的宪法。像议会的重要法案、大法官的判例,甚至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都可以发挥宪法的作用。欧洲大陆呢,恰好相反。从18世纪末开始,以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为标志,制定成文宪法变成了一种潮流。那英国要不要追随这种新潮流呢?伯克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伯克看来,英国和欧陆宪法形式的不同,来自它们迥异的历史。在英国的不成文宪法背后,是13世纪以来王权与贵族的漫长斗争。斗争的结果,又塑造了英国的社会结构。换句话说,不成文宪法,在英国是一种集体选择。它来自英国历史的有机发展,又跟当前的社会现实相匹配。同样,欧陆国家选择成文宪法,是为了对抗专制王权在16到18世纪的急剧扩张。英国没有经历这段历史,当然也不用盲目效仿。伯克认为,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都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所谓国家,既包含领土跟人口,也是历史演化形成的有机体。国家之间可以有基本的共识,但盲目移植其他国家的理念,特别是抽象的口号和目标,一定会遭到来自历史的反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克再度批评法国大革命,认为它光喊口号,不研究历史,无助于解决法国社会、经济暴露的矛盾。
伯克留下的第三个关键词,叫“平衡”。这个词针对的是18世纪英国的政局。伯克讲,“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王权和议会表现上形成了妥协,但这种妥协是不稳定的。首先,国王虽然不能否决议会的法案,也不能擅自颁布新法,但他可以间接干预人事安排。比如,封哪些人当贵族,挑选哪些贵族进上议院,就属于国王的权力范围。像乔治三世这样的强势国王,还会主动挑起议会内部的斗争,好把自己心仪的政治家推上首相的位子。议会呢,看上去可以制衡王权,运作机制却非常粗放。辉格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内部有老派土地贵族和新兴工商业主之争,经常被国王利用。辉格党的议员,名义上要对公众负责,其实也不存在像样的授权关系。在当时的英国,选举权是跟财产门槛挂钩的,全国只有不到4%的人有投票权。选区划分呢,又是在15世纪就提前定好的,300多年都没有变过。拥有大片土地的贵族,只需要在某个小选区拉拢几十个选民,就能扶持一个新议员上位。像这种由不到100个选民选出的议员,在英国下议院里要占到一半。连伯克自己也是按照这个模式,在罗金汉的封地上当选的。
但是,伯克并没有因为曾经受益于裙带关系,就替旧制度说好话。他讲,议员作为立法权的化身,要是只用对几十个选民负责,或者受制于大贵族,那他的眼光会越来越狭隘,越来越脱离公共性。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得彻底变革选举和政党制度,建立名副其实的代议制。代议制的基础,首先是明确公共利益,要把国家和民众放在第一位。这需要在议员个人的诉求和公众利益之间达成平衡。另外,政党也要有明确的党纲和严格的纪律,要用廉洁的操守,而不是赤裸裸的利益收买,去约束自己旗下的议员。只有这样,议会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去平衡王权乃至其他行政权力的进攻。到了19世纪,当英国和美国政坛开始形成两党制时,就大量参考了伯克的主张。
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伯克其实既不属于典型的“右派”,也不属于“左派”。他的政治理念,是以均衡为导向的。真实的伯克,并不反对变革。他只是担心,过于激烈的革命,会颠覆整个社会结构以及历史形成的共识,最终导致自由本身受损。这样的观念,当然有局限性。但它提供的反思视角,至今没有过时。
好了,关于这本《帝国与革命》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我们在评判一位政治家的历史地位时,主要是看他建立了哪些现实功勋。从这个意义上说,伯克的政治生涯不算成功。但如果把伯克定位为政治思想家,评估他的长期贡献,那他称得上厥功甚伟。在18世纪这个西方历史的转折期,伯克提出的“自由精神”、代议制政体、“历史有机体”等概念,深刻影响了英美等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其中虽然也有糟粕,但瑕不掩瑜。由伯克开创的保守主义传统,和法国大革命开启的革命传统,既相互论战,又彼此影响,共同塑造了今天的西方政治。当我们对大革命的激情和理想主义报以敬意时,同样不能忘记,还有伯克这位倡导审慎与平衡的思想先驱。
另外,我们普通人,从伯克一生的经历里,也能获得不少启示。伯克自己是政治裙带关系的受益者,但他并没有把私欲放在第一位,而是从公众利益出发,倡导廉洁、超然的政治伦理。这无疑是真正的独立人格的体现。伯克对“抽象”和“具体”的辨析,同样可以服务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我们对一种抽象的新思维、新观念抱有好感时,不妨想一想:它能直接套用到自己身上吗?是不是还要考虑具体的外部条件?重温伯克的教诲,就能给你敲响这样的警钟。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此外,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由伯克开创的保守主义传统,和法国大革命开启的革命传统,既相互论战,又彼此影响,共同塑造了今天的西方政治。
-
伯克自己是政治裙带关系的受益者,但他并没有把私欲放在第一位,而是从公众利益出发,倡导廉洁、超然的政治伦理。这无疑是真正的独立人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