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与国王》 王朝解读
《大象与国王》| 王朝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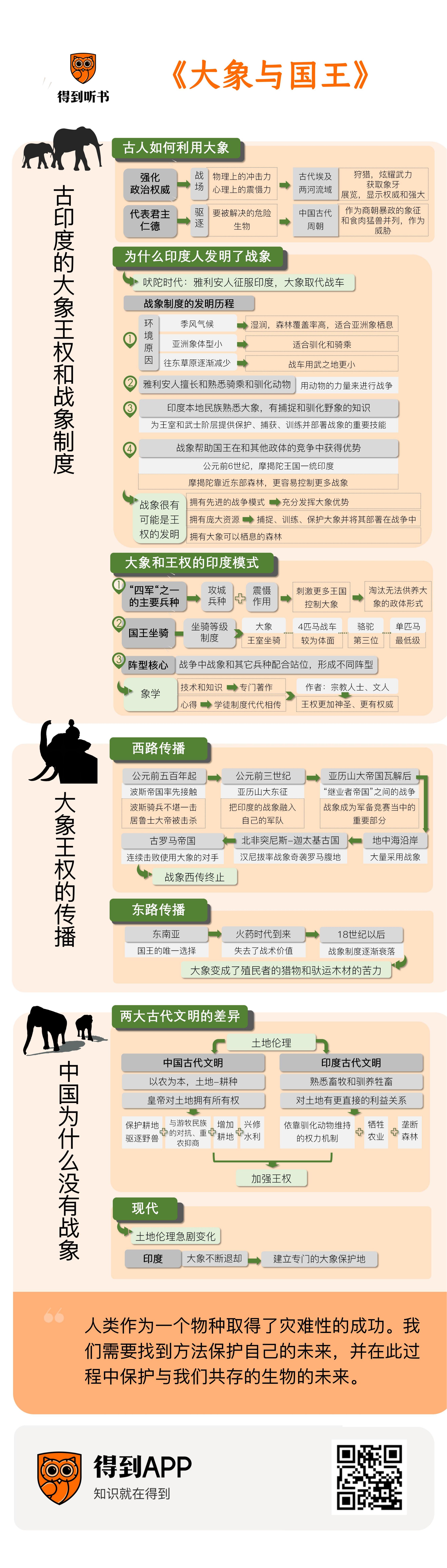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讲的书,标题叫《大象与国王》,听起来有点像寓言故事,这说的是哪里的大象?哪里的国王?其实这本书的主角,主要是印度的大象与国王,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模式,我称之为“大象王权”,而且传播到了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好几个古代帝国,而且还维持了三千年。你可能以前就注意过,印度人喜欢大象,连印度总理莫迪谈到印度崛起的时候,也用大象比喻自己的国家,“这头沉睡的大象已经苏醒”。你可能也听说过,印度教虽然崇拜牛,但印度教最受欢迎的神,是象头神。这本书,就会为你解答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印度人那么喜欢大象?
这个问题再进一步,你可能知道中国古代也有大象,甚至连北方黄河流域都曾盛产象,甲骨文有“象”字,而且河南沿用至今的简称“豫”,原来也就是指体型庞大的象。但是,听书之前解读过一本《大象的退却》,里面说,中国虽然和大象接触的历史悠久,却没有形成印度类似的战象文化,而且中国大象的分布还随着森林的退化,不断向南退却。为什么大象在中国没有那么受欢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比你想象得还要复杂一些,牵扯到了环境、物种、王权、土地等等,能够让你更好地认识中、印两大文明的深层区别。
本书的作者托马斯·特劳特曼是美国的印度历史专家,密歇根大学历史与人类学荣休教授,曾任密歇根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精通古印度的梵语,堪称印度研究的大牛。他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直接引用了很多古印度的梵语经典,为我们原汁原味地呈现了古代印度人如何看待大象、利用大象,更好地理解印度王权与大象的关系。他在本书的首尾,都非常直接地与《大象的退却》对话,试图比较中、印两国古代历史的不同发展方向,如何塑造了今天不同的自然面貌。
简而言之,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曾经都试图驯养大象,利用大象来强化君主的威严,但是只有印度,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王权制度,让国王、大象、森林三个概念,绑定在了一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古代“更环保”,相反,从大象的历史来看,你会发现就连庄严而威力无穷的大象,都是被人类利用的对象,始终是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输家。
接下来,我们就以大象作为切入点,回顾三千年间人类与环境的历史。首先,我们先解答,为什么古代文明中,是古印度首先发明了“大象王权”和战象制度?然后,我们把视角移出印度,看看“大象王权”为什么能传播那么远。最后,我们再回答,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战象,这又反映了两大古代文明的深层差异。
先慢着,你不妨想象这么一个场景。此时正是三千年前的战场,你是前线最勇敢的战士,身披盔甲,手执利剑,冲杀于敌阵之中,无往不利。突然,你的脚下能清楚地感受到大地都在震动,从两旁的树林里冲出几头巨兽,还发出骇人的咆哮声,长着长长的獠牙,像楼房一样高大,腿像柱子一样粗壮。战友试图用长枪阻止它的前进,但它受伤以后更加狂暴,人一下就被“降维打击”,踩扁了。你很清楚,自己根本无法阻挡它的冲锋。此时和战场上其他丢盔弃甲的战友们一样,你的脑海里只剩一个答案——跑。
没错,我们要解释对大象的喜爱,其实要从对大象的畏惧开始。古代战象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和他们天然的威慑力有着很大关系。这种庞然巨兽在战场上的效果,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冲击力,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很早就认识到了大象的这一特点,都试图用大象来强化政治权威。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古代的埃及和两河流域,这两片地区的大象现在已经灭绝,而在三千多年前,那里的古代国王们通过狩猎大象来炫耀自己的武力,并且也能获取稀有的象牙。有时,他们还会捕捉大象用来展览。特别是古代亚述王国的国王,特别喜欢举行声势浩大的王室狩猎。他们的目标猎物主要就是大象、狮子等等体型大,又很危险的野生动物。捕杀猛兽当然是国王勇气和武力的证明,动物的毛皮和爪牙则被做成奢侈饰品,成为高人一等的地位象征。他们还到处展览捉到的活象,对参观的民众来说,国王的战利品如此庞大,那么他的权威和强大也就不言而喻了,也正因此,亚述国王们也热衷于让被征服的附属国上贡活象。事实上,叙利亚地区的亚洲象到公元前500年前基本灭绝,和人类的过度捕猎脱不开干系。
同时期的中国,也很熟悉大象,比如之前说过甲骨文上有“象”字。不过,在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中国人并不是很热衷于利用大象。虽然在战国时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对武王伐纣的记载中,有说“商人服象”,并且用这些大象进攻东夷地区,还说周公把大象都赶到了江南地区,不过考古上并没有发现商朝训练大象打仗的证据。同时期的孟子也记载了周公帮助周武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可以看出,对中国古代的君王来说,大象是要被解决的危险生物。特别是为了彰显周朝实行仁政和礼治的时候,大象要么作为商朝暴政的象征,要么和食肉猛兽并列,是一种威胁。换句话说,在中国,大象本身并不能强化王权,反而是驱逐大象更能代表君主的仁德。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古代对大象利用最彻底的模式,也就是出现在三千年前的印度的战象模式。这个故事要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开始,当时中亚地区的雅利安人大举入侵印度河流域,彻底改变了当地的文化。这里要补充几句,这个雅利安人,跟后来纳粹德国的“雅利安人”不是一回事。历史上的真实雅利安人是中亚的游牧民,民风剽悍,善用战车,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驯化马的民族之一。他们说一种古老的印欧语,后来分化成了伊朗的波斯语和印度的梵语。
最早的梵语文献《梨俱吠陀》讲述的就是雅利安人的征服故事,里面描述了很多作战英勇的武士阶层,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种姓制度中的“刹帝利”阶层,他们要么骑马,或者驾着双马战车,而不是战象。这个“吠陀”,就是雅利安人的史诗,所以他们入侵印度的时代也被叫做“吠陀时代”。有趣的是,随着雅利安人逐渐在印度定居下来,大象很快就在各种吠陀史诗中取代了战车,比如代表“天帝”和诸神军事统帅的因陀罗,他的坐骑就从战车,变成了一头大白象。在后来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部更加出名的史诗中,大象就成为常见坐骑,后来的佛教也吸纳了大象的坐骑形象,我们可以看出,“大象王权”正在逐渐形成。
在解释印度的“大象王权”之前,先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其他古代文明都认识大象,但没有驯化和骑乘大象?书里描述了战象制度的发明历程,我从中概括出了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比较基本的环境原因。印度次大陆大部分是季风气候,比当时的其他古代文明更湿润,森林覆盖率要更高一些,更加适合喜欢吃叶子的亚洲象栖息,而不适合更适应草原的马。不仅如此,亚洲象体型更小,比非洲的草原象更加适合驯化和骑乘。雅利安人越往东深入,草原就越少,战车的用武之地就更小,而且要一直进口马匹,不如干脆骑大象。
第二,是雅利安人本来就很擅长和熟悉骑乘与驯化动物。雅利安人和其他早期南欧及西亚的印欧语部落一样,早就学会了驯化牛、马、山羊、绵羊等等,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一批使用车轮的人。用动物的力量来进行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而且他们很可能从近邻的古亚述帝国学到过大象对王权的加强作用。为了驾驭大象,他们发明了一种“驭钩”,也叫“象钩”,就是在一根棍子的末端有一根尖刺,然后在稍微往下的地方有一根向下弯曲的尖钩,骑在背上的驭象手就用这个钩来扎大象脆弱的皮肤,以此控制大象。这个钩子后来还慢慢变成了权力的象征。
第三,是印度本地民族就很熟悉大象,也有自己的捕捉和驯化野象的知识,他们被称为森林民族。对于雅利安人来说,这些人为王室和武士阶层提供了保护、捕获、训练并部署战象的重要技能。
第四条有一些复杂,是因为战象帮助国王在和其他政体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古代印度小国林立,有不同的政体,包括王权制、共和制和森林部落制。因此,作者也提出了战象的具体发明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也就是印度历史上的晚期吠陀时代。
尤其是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当时出现了佛教和耆那教两个新兴宗教,他们都反对吠陀教的种姓制度,也带来了一个印度版的战国时代,被称为“十六雄国”。最终,摩揭陀王国脱颖而出,一统印度。原本,摩揭陀只是一个靠东的小国,靠近被认为没有文明的森林民族。但作者认为,正因为他们靠近东部森林,也更容易控制更多战象,让摩揭陀人才能最终一统天下。王国的军队有多强大呢?我们可以从同时期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记载中,找到证据。当时印度有很多共和国和小城邦,他们连一头战象都养不起,从而被轻松打败。而亚历山大在印度打得最硬的一场仗叫杰赫勒姆战役,是和一个有三万步兵、四千骑兵,还有战车300辆以及战象200头的印度小王国进行的。最后这个国王还被重新任命为当地总督。
用作者的话来总结,“战象很有可能是王权的发明——王权既拥有先进的战争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大象的优势,又拥有庞大的资源,可以从森林中捕捉、训练、保护大象并将其部署在战争中;在印度,王权还拥有大象可以栖息的森林。”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到底印度人的“大象王权”是什么样的。作者说,在这种模式下,大象拥有三个主要功能:作为“四军”之一的主要兵种、作为最高等级的坐骑,以及作为作战时的阵型核心。
首先,古印度王国建立了一个叫“四军”的军队体系,由步兵、骑兵、战车、战象四部分构成,像猛兽的四条腿一样各司其职又密切合作。这个四军不仅是一种现实的军队体制,而且在宗教上也被认为是更完美的体系。比如在《罗摩衍那》中描写了古印度人认为最理想最完美的城市阿逾陀,里面就充满了充满斗志的武士和最好的战马及战象。值得补充一句,在四军之中,战象是被当作攻城兵种的。马只能提供机动性,但是大象已经足够撞毁那个年代的简单工事,甚至还能直接冲击城墙。如果再加上震慑作用,可以说在当年的印度,战象简直就是核武器,这也反过来刺激了更多王国去控制大象,逐渐淘汰了无法供养大象的其他政体形式。
后来战车逐渐退出战场,四军变成了三军,但是这个四军概念一直流传下来,变成了国际象棋的雏形。印度最早的象棋被称为“恰图兰卡”,是梵语音译,直译过来意思是四条腿,也是“四军”的同义词。里面除了四军的四个兵种,还加入了国王和身边的文官。这些棋子通过波斯和阿拉伯传到了西方,原本代表战象的棋子也因为失去文化背景而被改得面目全非,在英语里变成了主教,法语则叫小丑。
但是大象可不是小丑,我们接下来要讲大象的第二个功能,就是作为国王坐骑。前面也说过,原本的史诗是把战车当作最高等级坐骑的。实际上,印度人除了人有等级制度,也就是种姓,坐骑也有一套等级制度。最开始的最高坐骑是战车,而骑马地位则要低一些,大象后来居上,取代了战车的地位。有古希腊学者记载,“大象在印度属于王室坐骑,其次较为体面的出行工具是由4匹马牵引的战车,排在第三位的是骆驼,最低级的是骑单匹马。”《罗摩衍那》中有一个故事,很有象征意义。故事中,王子罗摩被母亲放逐到森林中之后,他的弟弟带着四军去森林里请他回来,但是罗摩不愿意违背母亲的命令,执意留在森林里。弟弟没有办法,只能答应以摄政的身份代理监国,但是他把罗摩的凉鞋放在大象的背上,带回王城,以示真正的国王还骑在大象背上。当然,这么大一个动物,也得被国王骑着,非常直白地宣示了谁是真正的老大。现在很多印度和东南亚的宗教仪式中,会请出大象来表演,比如向僧人下跪,源头就是大象作为国王坐骑,就代表了王权。
大象还有第三个功能,就是作为阵型核心。这就是说,在作战中,战象会和其他兵种配合站位,形成不同阵型。在印度传统中,有四种基本阵型,棒形、蛇形、环形和散形,根据具体站位,还有几十种变化。比如前面提过亚历山大东征的印度战役,当时那个小国王就使出了棒形阵和亚历山大对峙,也就是大象打头阵,大象之间间隔30米,步兵在其后,骑兵和战车在两翼。
围绕这三种用途,古印度发展出了一整套关于象的实用知识,后来又形成了抽象的理论研究,叫做“象学”,还有专门著作,比如《象论》《象经》《象学之海》等等。这些象学的基础,源自于大象管理人员长期积累的知识,他们可以分为猎象师、驯象师、驭象师和医师,有些人会同时兼任几个职责,另外还需要割草工人为大象提供饲料。仔细一想,也只有王权这样高度集中权力和资源的政治体制,能够在古代维持如此庞大和复杂的大象管理团队。
但是,虽然这些人的技术和知识对国王至关重要,但他们的心得基本只能通过学徒制度代代相传,不能成为“显学”。国王用更加“高雅”的学说撑场面,这就是象学。象学的主要作者都是宗教人士或者文人,让大象和相关联的王权更加神圣、更有权威。比如象学有一个大象起源神话,故事说原先大象都长着翅膀,但有一只大象压断了一个仙人修行的菩提树,这个仙人就诅咒大象,除了八个大神的坐骑,地上的大象再也飞不起来,只能当人类的驮运工具。这个故事就抹去了那些森林民族和底层大象管理者,把大象的驯化归功于婆罗门。
作者认为,《政事论》和《阿克巴则例》是有关大象知识的两部最好的文献。有意思的是,这两本本来并不是纯粹论述大象的象学著作,而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政治论述,因此它们才结合了大象的实际政治用途和宗教意义,在象征和实用两方面都体现了大象的价值。
特别是成书于大约公元前4世纪的《政事论》,大约和中国的《韩非子》同时代,是一本关于治国、经济政策和军事战略的经典。书中论述了理想的王国应该是如何运行的,除了要怎么管理村庄的农业土地,还指导国王要怎么管理非农业用地的森林。森林要分成两种,也都属于国王,一种是对应某种物产的资源林,里面生活着森林民族,还有一种是国王专门预留管理的大象森林,由森林民族和大象管理人员守卫和管理,任何人都不准捕捉或者杀死大象,否则直接处决。对于国王和大象的关系,《政事论》说:“一位君王的胜利由大象决定。因为大象的身躯庞大,冲击力强,它们能突破敌人的部队、作战阵型、堡垒和军营。”书里还非常具体地讲述了怎么保护大象森林、什么季节抓象、一顿喂多少饲料等等,堪称事无巨细。
《阿克巴则例》则是17世纪莫卧儿王朝的作品,记录了阿克巴时期的统治概况。其中记述的很多战象知识,比如捕象、养象技巧,和一千多年前的《政事论》几乎一模一样,反映了大象知识的高度稳定。同时,莫卧儿时期的养象知识又和蒙古人带来的养马知识形成了互补关系,描述了详细的产地和供养标准,确保帝国拥有能够维系强大军队的稳定供应。其中有一大原因,是因为莫卧儿王朝的祖先就是蒙古人,他们和雅利安人一样,是来自中亚的骑马民族。
在漫长的历史中,印度不断遭受外来的侵略,但是从吠陀时代开始形成的大象王权,一直在印度屹立不倒,甚至同化了那些入侵者。简而言之,这种大象王权将大象视为国王在军事力量、宗教神权和政治权威等方面的代表,赋予国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国王理所应当地垄断了森林的所有权,也就控制了大象的供应,并且用强大的组织能力形成花费不菲的一套大象管理班子。如此一来,印度的森林阴差阳错地就被国王保护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国王、大象、森林的三角关系。但是这里要强调,这不是说印度王权更环保,其实国王要控制森林里的大象,就要驱逐其他野兽,而且他们还不断举行皇家狩猎。实际上,在印度发明战象制度后,他们的大象知识不久后也开始向外传播,在最鼎盛时期,从地中海到太平洋都能看到大象的“印度模式”。
事实上,世界各地战象传统的发源地,基本都能找到印度源头,就连带着大象翻越阿尔卑斯山突袭罗马的北非国家迦太基,很可能也是从印度学来的。这种向外传播有两个方向,一个向东,进入东南亚,现在我们去泰国、柬埔寨旅游还能看到很多大象崇拜;一个向西,向西亚和欧洲传播,就不那么持久了。
先说这个西路传播。从公元前500年开始,印度西部的波斯帝国率先接触到了战象制度。当时有个给波斯皇帝当医生的希腊人写了一本《波斯志》,成为印度以外第一个记述印度战象的人。他亲眼看见印度象夫指挥大象拱倒了一棵棕榈树,大为震撼。书里记载,创建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就是被印度人的战象埋伏,之前所向披靡的波斯骑兵变得不堪一击,居鲁士本人也被印度士兵用标枪击杀。不过波斯帝国沿用古亚述的大象利用模式,把印度进贡的大象用来炫耀,只有他们的印度盟友使用战象。
向西传播的关键历史阶段,是亚历山大东征。在公元前3世纪的东征期间,印度战象的实际战果向西传遍了整个西亚地区。但亚历山大还没有打到印度核心区,也就是摩揭陀的难陀王朝。据不同历史版本记载,难陀王朝的战象至少也有四千头,并且还有二十万步兵、两万骑兵、两千辆战车。打完了前面说过的杰赫勒姆战役,士兵们听说东边这么恐怖,纷纷哗变,大帝只能班师回朝,但他一路上抓了两百头大象回去,还封了个大象指挥官,把印度的战象融入了自己的军队。亚历山大去世时,他的棺材四面展现了帝国军队的四个部分:步兵、骑兵、海军和战象,可见战象已经成为王权的一部分,形成了新的“四军”。后来,西亚地区就留下了战象的传统,一直到公元11世纪的穆斯林帝国都还在使用。
之后,亚历山大帝国很快也土崩瓦解,史学家把这些分裂出来的国家叫做“继业者帝国”。他们相互发动战争,一直持续了几百年,战象自然成了这场古代军备竞赛当中的重要部分,并且进一步向西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在这些王国中,虽然大量采用战象,但是他们还是把象夫直接称为“印度人”,可见也是从印度直接进口的。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他们试图模仿印度人实行大象森林制度,禁止森林民族猎食大象,还会从非洲埃塞俄比亚抓森林象,让印度象夫来训练这些非洲象。不过,亚洲森林象比非洲森林象更庞大、更强壮,所以还是原装的印度战象更受欢迎。
大象往西传播,最远到现在的北非突尼斯一带的迦太基古国。最著名的战役,就是汉尼拔率领三十七头战象翻越阿尔卑斯山,奇袭罗马腹地。迦太基虽然能接触到野生大象,但是北非的草原象体型庞大,性情更加凶暴,很难被驯服,所以他们采用的主要还是来自印度的战象。据记载,汉尼拔本人的坐骑战象,就是一头亚洲象。
不过,地中海沿岸的古罗马帝国对战象嗤之以鼻。在罗马连续击败使用大象的对手之后,他们也干扰了战象向西传播的步伐。他们认为大象容易受惊,不好控制,而且饲养成本太高,性价比太低,古罗马可以用高超的工程学知识取而代之。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在远离印度和缺乏森林的条件下,想要稳定供应熟练的印度象夫和顺服的印度战象,代价确实太高。而且古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也不需要战象再来撑场面,战象的西传也就到此为止了。
相较之下,战象在东南亚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东南亚丛林比印度更多,而且当地甚至没有分布适合马的草原,某种程度上来说,大象是东南亚国王的唯一选择。东南亚经历了长期的印度影响,现在到印尼的巴厘岛上,还能见到非常兴盛的印度教传统,就是印度化年代的遗存。从公元1世纪左右开始,东南亚地区出现了大量信奉印度教、实行印度王权模式的王国。柬埔寨的吴哥窟就是那个时代的遗迹,那里的雕像上有很多大象和骑着大象的国王,而且用的都是印度式的象钩。
不过,随着后来火药时代的到来,大象的战略威慑力暴跌,缺乏机动性的作战方式也让它失去了战术价值,最终从18世纪往后,战象制度和印度的王权一样逐渐衰落,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先后被欧洲人征服,大象从国王的核武器变成了殖民者的猎物和驮运木材的苦力。作者批评说:“印度诸国王一千多年来为了战争捕捉大象,但它们的数量却不曾减少。然而,根据如今印度政府大象问题工作组的相关报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大象的栖息地在急剧缩小。”
最后,我们也来讲讲中国。前面说过,中国虽然曾经有很多大象,和大象的关系却并不和谐。为什么中国人不用大象来强化王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会勾出两大文明更深层次的差异。
在《大象的退却》中,那本书的作者认为野生大象代表了自然环境是否健康,大象的退却也是人类过度开发自然的过程,中国人虽然有“天人合一”等等利于环保的思想,但是为了开垦土地的利益,造成了环境退化。这本书觉得,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印度人重视大象、重视森林,但印度也没有更环保。大象森林的制度,实际上可以说是掏空了森林,让森林从自然的栖息地,变成了国王的自留地。
作者认为,两大文明差异的地方不是利益,而是“土地伦理”。对古代中国文明来说,土地伦理有两点,第一,以农为本,土地是用来耕种的,产出粮食才能喂饱人。第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从根本上来说是皇帝的。如此一来,皇帝对土地的责任就是要保护耕地,最早的表现是驱逐野兽,而后来和游牧民族的对抗、重农抑商等等,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而且君王还要增加耕地,多开垦土地,喂饱更多人。相比用大量劳役看守森林和供应大象,古代中国的皇帝更倾向于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改善耕地的灌溉和跨区域的水运条件。
而在印度,牧业和农业从未成为相互竞争的关系。古代雅利安人本来就是牧民,而在印度的定居农业发展中,耕种也没有成为第一要务。印度的王权落于城市和庄园,没有大一统的王权,也就没有普遍的所属权,只会控制部分土地和森林。比如前面提到的《政事论》,理想的乡村被划分为经济区域和生态区域,包括农庄、牧场、贸易路线、原木林、大象林和矿区;所有区域都通过经济交换和税收与王权所在的城市之间建立联系。而那些负责看护大象的森林民族,不少其实是森林边缘的牧民,和农民长期共存。此外,各个土邦的王公和被统治的臣民的关系比中国更加靠近,也更具体,因此大象的直观震慑效果也会更大。
相比之下,我们就能发现,两个文明不同的土地伦理,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观。古代中国皇帝对土地的控制往往是抽象的所属权,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修建大型工程,为全国提供保护。而古印度的王公们则对土地有更直接的利益关系,也因为熟悉畜牧和驯养牲畜,倾向于建立一种依靠驯化动物维持的权力机制,不惜牺牲农业。古中国修建水利,古印度垄断森林,都是为了加强王权,是不同土地伦理下两个古代文明的殊途同归。
也如作者所说,到了现代,这种土地伦理在急速变化。曾经专门供养大象的印度,现在也和曾经大象不断退却的中国一样,都要建立专门的大象保护地。如作者最后写的,“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取得了灾难性的成功。我们需要找到方法保护自己的未来,并在此过程中保护与我们共存的生物的未来”。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古代战象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和他们天然的威慑力有着很大关系。这种庞然巨兽在战场上的效果,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冲击力,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
2.古中国修建水利,古印度垄断森林,都是为了加强王权,是不同土地伦理下两个古代文明的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