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 朱步冲解读
《大分离》| 朱步冲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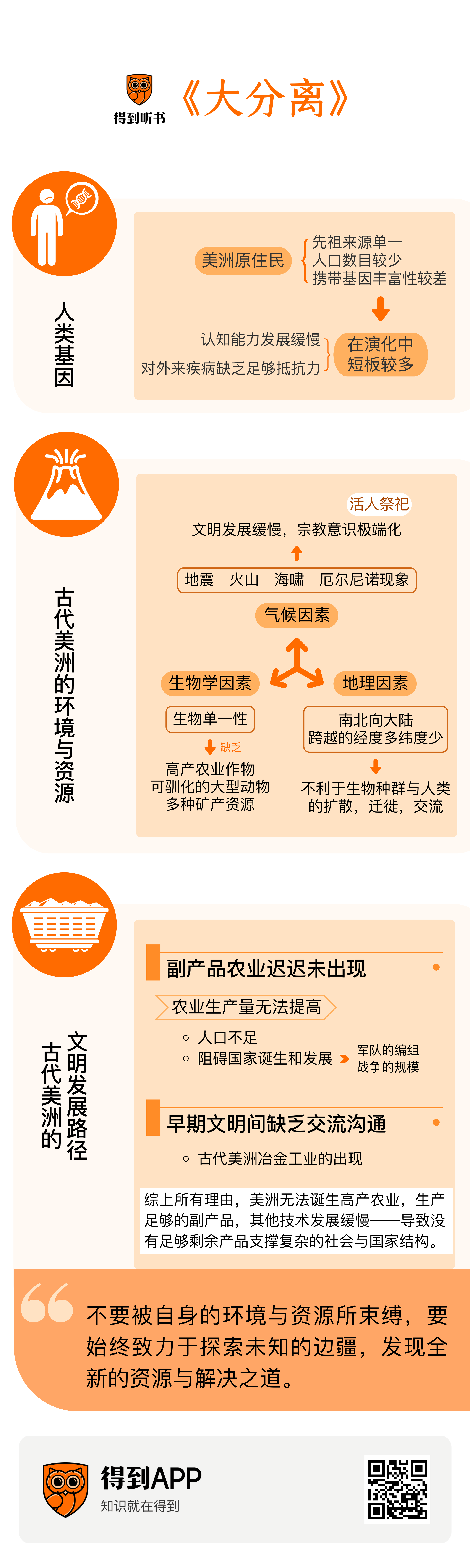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彼得·沃森的《大分离》,副标题是“新旧大陆的命运”。
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新旧大陆,分别指的是被称为“新大陆”的美洲,以及“旧大陆”的欧亚大陆。而所谓“大分离”,是指这样一段历史,以及社会发展态势,也就是:15000年前,一部分人类先祖从西伯利亚踏上美洲大陆这片相对与世隔绝的土地,开始独立发展演进,直到15世纪末以哥伦布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抵达,强行把美洲纳入全球殖民经济秩序为止。
作为当代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的巨擘,沃森擅长剖析人类物质文明进步与观念进化之间的关系。而他之所以要撰写这样一部600页,几十万字的巨著,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简单为读者再现这样一段历史,而是试图回答一个宏大而复杂的问题:人类认知与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与外部世界的环境和资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文明进步的快与慢,到底有多少归咎于环境,又有多少归咎于人类的认知与努力上的差距?
咱们“得到”的用户大概都知道,沉迷于这种“人类大历史”以及“差异性研究”的大师,还有一位贾雷德·戴蒙德,他的著作,比如《崩溃》《枪炮、病菌与钢铁》,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沃森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让他看起来非常像戴蒙德的同门师兄弟。他在前言中说,写这本《大分离》的直接目的,就是想回答一个重大问题:新大陆与旧大陆,也就是美洲和欧亚大陆,为什么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文明发展之路?用他自己书中的原话说,就是:新旧大陆人类的各自发展,是地球自然界最伟大的平行发展实验。那么,从科学的角度,看这场试验里,究竟有哪些外部因素影响了这两个人类早期文明的决策和发展,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再从这个原点往外延伸,这两块大陆之间的“发展之争”,还可以引出许多有趣而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而不是别人? 人类进入高度文明时代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地理环境和资源,如何塑造人类社会的形态,影响人的思维模式和经济模式?
不仅如此,沃森撰写本书的目的,更是想建构出一套关于人类生活、习俗、思想的演进架构。如果把本书浓缩成三段式的结构,那么本书的结构就是,首先来为我们分析,远古时期,美洲与欧亚大陆上的人类先祖,分别在文明“开局”时,身处什么样的自然环境,手中被赋予了哪些资源,强调的是“硬环境”对两个不同人类群体发展路径选择的限定。在第二部分中,则反过来探索,人类对于环境和自身的理念,是怎样在探索、征服周边环境中形成的。而在第三部分中,沃森则比较了古代美洲与欧亚大陆上,这两种渐行渐远的,关于自我与自然的理念,反过来又会如何影响这两种社会形态下一步的发展趋势与具体策略。
说到这里啊,相信你已经对这本鸿篇大作产生了相当的兴趣。那么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大致内容。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美洲原住民祖先的来源与人种基因特征。接下来,我们再来系统比较一下,欧亚大陆与美洲在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气候上的不同,以及对人类祖先文明发展路径的影响。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由于这些先决条件的影响,美洲的原住民文明如何在艰难的发展中,逐渐落后于欧亚大陆。
大约在15000年前,美洲原住民的先祖,从今天欧亚大陆的最东端,位于西伯利亚的楚科奇半岛,通过白令海峡,来到了被称为“新大陆”的美洲。而今天,依旧生活在西伯利亚的楚科奇人,就是这些美洲最早定居者的直系后代。他们是坐船过去的吗?并不是。当时正是地球上最后一次冰川期,海平面比今天要低几百英尺。所以,白令海峡并不存在,而是一片充满灌木和沼泽的陆地,如同一座连接西伯利亚和北美阿拉斯加的“浮桥”。所以,这些勇敢的开拓者,就是通过这道狭窄的浮桥,步行抵达新大陆的。
近几十年来,人类学和基因生物科学研究者,不断获得越来越多的新证据,来支持这一结论。从2005年开始,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IBM合作,利用强大的人工智能算法,对人类基因数据进行储存和分析。这个长期研究计划,被称为人类“基因地理工程”。到沃森写作本书时为止,这个研究计划已经收集了全球五大洲大约15万人的基因样本。
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中,科学家们有了很多有趣的新发现。比如,楚科奇人属于蒙古人种,而很多美洲土著部落的婴儿,在出生时,脊椎底部也会带有所谓的“蒙古斑”。这是一种蒙古人种独有的基因,而导致的浅蓝色胎记,随着婴儿的发育成长,会逐渐消失。
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发现,今天的美洲原住民在基因上高度相似,大多数独特的基因标记,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六千到一万五千年这段时间内,与推测中早期人类首次从西伯利亚大规模迁移到美洲新大陆的时间契合。到了距今9500年前,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导致陆桥永久消失,美洲从此变成了隔绝于其他大陆的“孤岛”,大规模的人类与陆地生物输入也就宣告停止了。所以,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由欧亚大陆向美洲进发的移民潮,也发生了两次左右。这两批不畏艰险的先驱者,几乎包括了美洲原住民全部的祖先。
由于祖先数量较少,种群单一,所以科学家发现,美洲原住民体内的基因丰富性,远不能与欧亚大陆与非洲人体内的相比。那么,这种遗传基因多样性上的有限性会导致什么后果呢?作者沃森直言不讳地说,这就导致美洲古代人类在演化中,短板比较多。比如认知能力发展相对缓慢,以及对外来疾病缺乏足够的抵抗力,诸如此类。这些在不同地区文明的发展竞争中,是不可忽视,而致命的劣势。比如,戴蒙德就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举过一个例子:1902年,一艘捕鲸船来到了加拿大北极圈内的南安普顿岛。在停留期间,有个船员不幸得了痢疾,结果传染了岛上的原住民因纽特人,直接导致全部56个因纽特人中,有51人因病去世。这场惨剧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因纽特人的基因序列过于单一,也是因为南安普顿岛长期与世隔绝,生物交换性过低。而不幸的是,由于地理结构,整个美洲大陆都有类似的问题。
在简单回顾了北美洲原住民人类的起源和基因特征后,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所居住的环境,与欧亚大陆相比,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从广义的自然环境上说,新大陆与旧大陆之间有三个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分别是:气候因素、地理因素和生物学因素。三者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制约。
如果你玩过地理类游戏,尤其是战略模拟类游戏,也许知道:你在地图上落脚的位置,周边资源的丰富度,直接决定了你自身的安全性和建设发展速度。然而不幸的是,美洲这块新大陆,表面上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实际上对落脚在这里的早期人类文明并不友好。套用游戏术语说,美洲原住民祖先在从西伯利亚风尘仆仆赶来之后,却遗憾地发现,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Hard 模式”。
为什么这样说呢?作者沃森从气候学角度,给我们做出了一个详细的解释。简单来说,整个美洲西海岸,都饱受极端气候的折磨,具体来说,就是大家熟悉的厄尔尼诺现象。
太平洋,是操控全球气候的枢纽。当赤道纬度附近东西向的固定信风,遭遇东南亚到澳大利亚附近的温暖海水区,就不断形成厚重的雨云,周期性地持续降雨。夏季降雨区域持续北移,冬季南移。如果看看地图,这股太平洋制造的季风气候区,从非洲中部、印度次大陆一直绵延到我国东南部,以及澳洲北部,包括了世界上几乎三分之二的农业人口。可以说,全球农业是否能稳定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全都仰赖这股稳定的季风。
然而,再稳定的气候,总会出现反常。赤道附近的信风,会时而减弱,甚至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反向强风。这时,温暖的海水就会向东流向美洲,于是灾难降临:从东南亚到澳洲,干旱降临,而美洲太平洋沿岸,却迎来了剧烈的飓风和海量降水。这就是著名的厄尔尼诺现象。
从历史文献来看,最早记录这一灾难性反常气候现象的,是19世纪末的一位秘鲁船长,叫卡里略。他在一份报告中抱怨说,南美洲太平洋沿岸出现了一种周期性的气候波动,过暖的海水在持续损害近海地区的凤尾鱼捕捞业,还引发了其他异常天气。由于它总是在圣诞节之后降临,所以被这些水手称为“厄尔尼诺”,也就是西班牙语中“上帝之子”的意思。
虽然全球各地的气候,都会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但美洲西海岸,这个美洲人口稠密区,却是不折不扣的核心重灾区:干旱、暖冬、暴雨与飓风同时降临。更糟糕的是,从大历史维度来看,厄尔尼诺现象,在最近六千年中越来越频繁。在进入21世纪后,频率更是加速到每2到7年就会发生一次。相对于富裕、文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极端气候给贫困落后地区造成的损失更大,例如中美和南美地区。
除了厄尔尼诺现象,整个新大陆美洲,尤其是中美和南美地区,还会面临另一种频繁的自然灾害,那就是火山喷发。整体来说,美洲大陆西海岸,都被囊括在“环太平洋火山带”之中。作者沃森在书中说,尤其拉丁美洲,是迄今为止火山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自1532年以来,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已经经历了超过500次的火山喷发,累计有超过两万五千人丧生。同时,由于处在美洲大陆板块和南极洲板块的交界处,拉丁美洲也不幸位于地球上最为频繁活跃的地震带。更为频繁的自然灾害,是对地区人类文明发展的明显阻力,其造成的突发或者周期性破坏,不仅造成了当地人类社会的重大财富与经济损失,同时也对本地区文明发展的底层逻辑和意识形态,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就追随作者沃森的叙述,来具体看一下。宗教,是一个了解不同早期人类文明意识、道德与世界观的有效切入点。简单来说,人类的世界观,是通过对自然世界的观察与经验积累,而逐渐塑造而成的。而在早期人类意识中,灾难,是一种神灵与人类“沟通”的极端方式。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文明本身就起源于对灾难的回应,而宗教,就是人类试图与神明“沟通”,达成祈福消灾目的而建立的。
简单来说,每种人类宗教里,都有神明和对应的祭祀活动。祭祀就是人类试图“弥补罪行”,希望神明“息怒”,转而保佑自己的仪式。而在美洲新大陆,尤其拉丁美洲地区,频繁的暴雨、地震和火山喷发,让栖息在这里的早期人类觉得,如果神真的存在,那么他的性格肯定是暴虐凶残,喜怒无常。所以,祭祀活动必须频繁举行,而献上的祭品不仅要数量多,而且珍贵,才能让神明息怒,维护世界脆弱而短暂的稳定。
那么,在美洲原住民心中,什么样的祭品是能够长期大量供应,同时足够珍贵的呢?沃森给出了一个血淋淋的残酷答案,那就是人本身。说到这里啊,可能大家就会想到:14到16世纪,在中美洲兴盛一时,以残酷的活人祭祀出名的阿兹特克人。宗教历史学家卡拉斯科分析说,这种残酷野蛮的活人祭祀,归根结底是来自阿兹特克人,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文明中,对自然世界和宇宙秩序的焦虑。
实际上,在新大陆美洲的历史上,确实有文明因为恶劣的天气原因而灭绝。比如公元100年到800年左右,位于秘鲁境内的莫切文明。和许多拉美地区的原住民文化一样,莫切文明宗教气氛浓厚,城市的中心是高耸的金字塔,也是举行祭祀典礼的所在。莫切人崇拜外形如同美洲豹的神明,拥有古代美洲一流的农业种植灌溉技术,擅长制造金属工具。但残酷的人祭也同样盛行。今天的科学家相信,莫切文明的突然消亡,就是因为一场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这场厄尔尼诺现象也许持续了18个月之久。根据考古发掘显示,在莫切文明的最后阶段,金字塔神庙里还在举行残酷的活人祭祀仪式,许多牺牲者的遗骸表明,他们是在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狂风暴雨中,惨遭杀害的。
到了阿兹特克人时期,由于极端气候发生的频率逐渐上升,从而导致活人祭祀的规模越来越大,举行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是因为,由于当时知识结构无法升级迭代,所以主持宗教仪式的祭司们,只能把一切都归咎于神明的愤怒或者力量的虚弱。例如,当日食,或者火山爆发出现,让太阳的轮廓和光芒在天空中被遮蔽时,祭司们就只能解释说:人祭的规模不够,导致太阳神因为缺少营养而虚弱,无法现身。所以,只有贡献更多的活人祭品,才能让太阳恢复活力。这种狂热,就导致阿兹特克人被迫频繁举行规模更大,距离更远的战争,捉来更多的战俘作为献祭的祭品。代价就是,无数壮年劳动力被夺去了生命,从而引发了致命的人口坍塌:既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也没有足够的适龄人口繁衍下一代。沃森认为,即使没有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阿兹特克文明也已经走到了濒临崩溃的临界点。
反过来,让我们再随着作者沃森的分析,看看与美洲相对的欧亚大陆。
沃森说,与美洲相比,欧亚大陆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它有富饶的黑土地,但也有贫瘠的沙漠。然而从地理大结构上,欧亚大陆与美洲的不同点在于:美洲本质上,是一块南北向的大陆,跨越的纬度多,而经度少。而欧洲大陆却是东西向的,涵盖的经度多,纬度少。在美洲出现过的古代文明,比如莫切、印加、玛雅、阿兹特克等等,都分布在南纬18度到北纬25度之间,在一片总范围大约375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内。
反过来,让我们再看一下欧亚大陆。各个文明分布的地区范围,比美洲广阔得多,大约是2550万平方英里。
那么,东西走向的地理结构,和更广阔的文明分布范围,能够带来哪些优势呢?沃森就解释说了,生物物种的扩散与迁徙,在东西向上进行,远比在南北向上来得容易。这是因为,东西向的迁移,会让你一直在大致相同的气候条件与自然地理环境中旅行,而南北向的旅行就不一样了。相信热爱旅游的朋友都有经验,秋冬季节,你在我国北方城市上飞机时,穿得很厚,然而在南方城市一下飞机,会因为意想不到的炎热,立刻就要换装。剧烈的温差变化,会带给我们明显的身体不适感。
自从人类定居以来,欧亚大陆上就逐渐形成了两条东西向,相对便捷的文明传播与迁徙路径:第一条就是平坦的欧亚大草原,也就是日后的陆地”丝绸之路”。第二条位于海上,中间由河流连接,被称为“东西大走廊”,日后也演变成了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地中海出发,经红海、两河流域、阿拉伯半岛海岸线,直到印度洋与中南半岛,最终抵达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最便捷的路线可以缩短到一万英里左右,并且可以借助有利于航行的季风,轻松而顺畅地走完。
贾雷德·戴蒙德测算过一些人类历史早期,主要粮食作物的传播速度。比如,粮食作物在西亚地区最早种植以后,就开始以每年0.7英里的速度,向东传入印度河流域,向西传入欧洲。在东南亚地区,由于气候宜人,水运发达,所以粮食作物在这里向东传播的速度最快,速度达到了每年3.2英里。作为对比,农作物在美洲的南北向传播速度,就明显要慢。比如,中美洲原住民在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种植玉米,而玉米作物在美洲的传播速度,基本是每年0.5英里。而美洲最主要的牲畜羊驼,在被驯化之后,传播的速度更只有每年0.2英里。最终导致,源自中美洲的玉米和豆子,分别花了3000与4000年,才抵达今天北美大陆的东部。
不仅如此,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就意味着更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和数量更多的资源与腾挪的空间。比如,关键性的肉用与劳动用大型哺乳动物。在欧亚大陆上,早期人类可以从牛、羊、马、鹿、骆驼甚至大象等各类动物中进行选择。反过来,由于美洲在地理位置上的相对隔绝性和东西方向地理跨度的狭窄,从而导致美洲的物种相对稀少,原住民的选择非常有限。
更温和的气候、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与更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文明竞赛中的综合优势。作者沃森举例说,比如欧亚大陆上的早期文明摇篮之一,繁荣的地中海地区,这里简直是集中了各种有利条件:围绕地中海沿岸,集中了岛屿、半岛、丘陵、平原以及海湾等各种地形,不仅带来了生物多样性,还因为温和湿润的气候和便利的海运,鼓励不同地区的居民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这里出产的贵金属、陶器、橄榄油、葡萄酒、乳酪等产品,既是人类生活的刚需,又容易储存,不易腐败,简直天生就是为了贸易而诞生的。
然而,曾经的美洲,其实和欧亚大陆一样,遍布着各种大型哺乳动物,物种丰富度非常好。刚才我们提到,人类是趁着最后一次冰期,踩着白令海峡陆桥来到美洲的。实际上,在恒久的地球历史上,这条陆桥一直时断时续地存在。无数动物曾经利用这条陆桥,在新旧大陆间迁徙。比如,马、鹿与长毛象等动物,可以通过这种迁徙来保存种群或者躲避危险。然而,几乎在人类进入美洲同期,美洲就不幸经历了一次物种大灭绝,绝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都死亡了。原因可能是早期定居人类的过度狩猎,或者冰期结束之际的气候剧变。更悲惨的是,距今9500年前,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导致陆桥永久消失,美洲再也无法迎来全新的大型陆生动物入驻。这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导致美洲原住民可以驯化的大型动物少之又少。
根据戴蒙德的统计,欧亚大陆上,一共产生了13种大型家养哺乳动物,而拉丁美洲只有1种,就是羊驼。然而羊驼不能用来当坐骑,也不被驯化用作拉犁等生产用途。不仅如此,如果从肉用牲畜的角度衡量,羊驼的料肉比,也就是饲料转化成体重的饲养效率值,也不如猪牛羊。当然,北美还有数量丰富的野牛。但是,猎杀这种速度快,凶悍的大型动物,对于缺乏金属武器和战马坐骑的早期原住民来说,实在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戴蒙德更是大开脑洞,提出了一个观点:如果不是上面提到的美洲物种大灭绝,那么1519年,当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带着自己那支小小的殖民远征军来到美洲时,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数量众多的阿兹特克骑兵,骑着驯化的美洲马,胜算不高的西班牙殖民者很可能惨败而归,从而大大推迟欧洲殖民美洲的历史进程。
说完了可驯养的大型动物,再让我们来看看,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要素:农业粮食作物。在这一点上,美洲原住民也吃了地理环境的亏。
农业发达与否,直接决定了一个文明能支撑的人口总数,以及有多少剩余农产品能够用来饲养牲畜,用于贸易交换,以及供应军队、工匠、贵族等非农业生产人员。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里直截了当地说,美洲原住民文明之所以发展缓慢,就是因为拿了一手“烂牌”。在美洲,由于没有小麦、水稻、粟等欧亚大陆常见的食用作物,所以长期以来,原住民的基本口粮来自玉米。然而,比起小麦和水稻,玉米的蛋白质含量不高。同时,美洲原住民手头还没有帮助耕作的大型动物,也缺乏来自动物排泄物的肥料,这一切都限制了美洲文明所能承载的人口总数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
不仅如此,这样的温和气候和稳定宜居的自然景观,也让欧亚大陆的早期人类,发展出一种和美洲原住民截然不同的宗教,以及世界观。沃森总结说,如果说美洲原住民宗教的核心,是安抚喜怒无常的神明,也就是自然世界;那么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的宗教,就很快从安抚,变成了祝祷。也就是说,气候和自然环境的稳定,证明神明的“情绪”是稳定的,对人类的态度总体上是善意的。所以,人类可以大胆地和神明沟通,向神明许愿,要求神明给自己以恩惠和保佑。另外,由于神明和人类的“沟通渠道”是固定的,反应是可以预测的,所以在欧亚大陆上的宗教里,神明很快就变成了道德的化身。要想取悦神明,残酷的活人祭祀是完全无效的,最重要的是,人类必须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比如诚实、忠心、自律、节制、关心他人,诸如此类。这样一来,宗教就变成了一种建构社会和国家的黏合剂,帮助欧亚大陆发展出了超越美洲的复杂社会结构和稳定的社会道德共识。
好了,刚才我们顺着作者沃森的叙述,详细观察比较了新旧大陆,也就是美洲和欧亚大陆之间自然环境与气候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如何影响了两块大陆上,早期人类文明发展在资源与底层逻辑上的差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些案例,来具体看下,这些先天条件,如何让美洲早期文明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文明发展路径。
在本书中,沃森专门开辟了一个章节,叫“新大陆上从未发生的四件事”,利用直观具体的案例来解释,美洲大陆的文明总体发展程度,是如何受制于资源和环境,在这场漫长的竞赛中逐渐落后的。所谓“从未发生的四件事”,实际上指的是犁铧、车轮、奶制品生产与骑马。这四项彼此关系密切,对于文明发展、经济生产来说至关重要的技术,无一例外,都没有在美洲诞生。直到16世纪末,才在欧洲全球殖民浪潮中,从欧洲引入。
沃森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副产品革命”,它结合了犁的使用、饲养大型牲畜,以及用肉蛋奶、羊毛等副产品去换取其他必需之物,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犁,意味着人类在农业生产时,对土地进行深耕,充分使用土壤的肥力。如果你还能够用驯化的大型牲畜来拉动犁铧,这就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耕耘更多的土地。如果驯服的大型牲畜在为人类提供副食品的同时,再为人类拉动装上车轮的车厢,就形成了一场运输革命。人可以利用车辆进行迁徙,运送剩余的农业副产品去远方进行贸易,甚至作为战场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然而,在美洲,由于动植物的物种丰富性远低于欧亚大陆,农业主粮依靠玉米,能够驯化的动物几乎只有羊驼与狗,能够食用的饲养动物则只有鸭子和火鸡。所以对于早期美洲原住民来说,农业定居生活模式,看起来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副产品革命迟迟没有出现在美洲,美洲原住民进入农业定居时代的时间,也比欧亚大陆要晚。直到公元前1500年,美洲原住民还在保持那种相对原始的狩猎加采集的生活模式。
迟迟不能提高的农业生产量,除了无法支撑足够的人口,也进一步阻碍了国家的诞生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案例,就是军队的编组和战争的规模。之前,我们得到听书解读过一本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的《战争》,里面有个观点就是:农业剩余产品的增长,直接支持了军事技术的变革。比如青铜武器和盔甲,然后是用马匹拉动的战车。这些技术,让维持军队和发动战争的成本迅速膨胀。哪个早期国家可以有效集中生产中的剩余产品,维持一支长期训练、脱离农业生产的军队,就能够在竞争中握有优势。所以莫里斯认为,国家的两个最基本功能,军事组织和财政,都是要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而本书作者沃森,也在书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没有金属盔甲和兵器,再加上缺乏足够的粮食盈余,从而让美洲原住民的战争模式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不仅如此,即使到了哥伦布抵达美洲时,例如阿兹特克这样的文明,已经能聚集一支上万名士兵组成的军队。但战争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捕捉战俘作为献祭的祭品,而不是把战俘当做可以利用的劳动力来源,还停留在低端的破坏性战争层面。
沃森和戴蒙德都强调,人类要想发明出突破性的新技术,手里的自然资源固然是一个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发明,往往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人类相互交流,互通有无的产物。美洲各个文明中心之间,分别被各种险峻的地形分别隔开,比如沙漠、瘴气弥漫的沼泽、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和高山峻岭,无法像欧亚草原或者地中海周边的人类一样,利用便捷的道路或者航运相互沟通。沃森说,在中美洲,轮子的雏形确实出现过,但作用仅仅是玩具的部件。如果中美洲的早期文明,能够和驯化了羊驼和骆马的安第斯山区文明有所交流,那么说不定,类似马车一样的运输工具,也能在美洲诞生。虽然比不上欧亚大陆上的牛车或者马车那样高效,但也会对经济生产和贸易,起到相当的推动作用。
同样,美洲原住民没有发明出工业和农业所必需的金属工具,以及精细化的金属兵器,也不是因为缺乏自然资源。实际上,从北美到南美,高品质的铜矿分布广泛,储量巨大。有些高品质矿脉实际上是裸露在地表的,同时还有黄金、白银、锡和铁矿。但在哥伦布抵达之前,如此多的金属矿藏资源,却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少数金属,主要被用来制造贵族与祭祀佩戴的饰品。这是为什么呢?不同的研究者给出了许多种解释。比如,戴蒙德还是把原因归咎于早期文明中心之间缺乏交流沟通。冶金业要发展,至少需要三种技术元素,也就是对金属矿的发现和利用,燃料和鼓风技术,以及冶炼炉。而它们不大可能被某个早期人类文明单独创造。
另外,英国学者佩西,在《世界文明中的技术》这本著作里提出,由于美洲传统宗教的世界观,认为金属是神的恩赐,所以必须使用在神圣的场合和身份高贵的人身上。同时,美洲盛产一种坚硬的黑曜石,说白了就是火山喷发而形成的天然玻璃,敲打之后,断裂面就形成锋利的刃口。所以美洲的古老原住民,比如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就在木棍上安装各种形状的黑曜石断片,来作为工具与兵器。可以说,黑曜石这种相对低端的替代物,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美洲古代冶金工业的进步。
好了,这本沃森的《大分离》的主要内容,就基本为你介绍到这里。本书可以说是作者沃森的一个雄心勃勃的宏大构思,那就是试图解答这样一个复杂问题:为什么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上,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路径如此大相径庭?气候、资源、物种和地理环境等先天条件,对人类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塑造,到底起了什么样的影响作用?
具体来说,沃森说的“大分离”,是指这样一段历史,也就是大约15000年前,一部分人类先祖从西伯利亚踏上美洲大陆这片相对与世隔绝的土地,开始独立发展演进,直到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美洲被强行纳入全球殖民经济秩序。
沃森总结说,15世纪,当欧亚大陆与美洲大陆初次碰面时,文明演进的差序格局表露得淋漓尽致。一方拥有战马、金属盔甲、火器,利用发达的航海技术,远涉重洋而来,背后是近代化国家与资本的支持。而另一方,则还停留在工具金石并用,信奉原始图腾,国家社会组织粗陋的阶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为了解答这个复杂问题,沃森在书中综合运用了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与生物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努力为我们复原了一幅实时动态的综合图景:原本共同走出非洲的早期人类祖先,如何在两块截然不同的大陆上,走上了殊途命运。
简单来说,美洲看似资源丰饶,但却因为独有的地理与气候,以及资源特征,让早期来此定居的人类先祖进入了“Hard 模式”。首先,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限制了生物物种的迁徙、交流,使得美洲总体生物多样性逊色于欧亚大陆。来到这里的人类祖先,可驯化利用的生物资源较少,而自身的基因丰富度也大大降低,延缓了演化速度。不仅如此,单个物种一旦遭遇突发性生态灾难,很难重建。另外,由于美洲处于板块交界处,火山、地震频繁,而太平洋上诞生的极端气候厄尔尼诺现象,也频繁侵袭人口稠密的美洲西海岸。
沃森分析,极端气候,与世隔绝,以及自然资源选择的有限性,三大不利条件一起,限制了美洲早期文明发展的速度和上限,导致这里无法迅速发展出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从而也无法建构足够复杂的社会和国家组织。更糟糕的是,极端气候和严苛的自然环境,给美洲原住民的精神世界蒙上了一层悲观消极和不可知的色彩,从而直接导致美洲原生的宗教长期停留在原始的自然崇拜阶段,经常发生掠夺战争,获取战俘作为活人祭祀。这些理念没能进化到更高的阶段,起到构建社会道德与共识的作用。这样就让古代的美洲国家,无法有效发展技术与经济。美洲陷入了人口数量和社会停滞不前的局面。
当然,作者沃森之所以做出如此详细和宏大的分析,并不是想简单地得出某种种族文化优劣的定论。他首先表达了自己的痛惜:在15世纪殖民时代,面对独特而别具一格的文化,欧洲殖民者并没有给予尊重和珍惜,而是毫不留情地毁灭了它大部分的文化记载与积淀,并把美洲大陆纳入了一种不平等的经济政治秩序,持续加以剥削和掠夺。而在积极引入近代先进技术之后,美洲本土经济也有了迅速和持续的发展。例如,今天的美洲已经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粮食与肉类出口地区。美洲本地居民,也在坚持不懈地探索一条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其次,沃森反复强调,自己的研究是在以古代美洲的教训,提醒今天全球所有人类: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要想持续生存发展,就必须做到三点:时刻针对身边社会与自然的各种危机与问题,迅速做出感知,进行分析。其次,努力与不同的人群和文明进行交流,取长补短。第三,不要被自身的环境与资源所束缚,要始终致力于探索未知的边疆,发现全新的资源与解决之道。只有这样,古老的美洲悲剧,才不会重演。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原书的电子版已经为你附在最后,欢迎你进行拓展阅读。此外,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新旧大陆人类的各自发展,是地球自然界最伟大的平行发展实验。那么,从科学的角度,看这场试验里,究竟有哪些外部因素影响了这两个人类早期文明的决策和发展,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
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要想持续生存发展,就必须做到三点:时刻针对身边社会与自然的各种危机与问题,迅速做出感知,进行分析;其次,努力与不同的人群和文明进行交流,取长补短;第三,不要被自身的环境与资源所束缚,要始终致力于探索未知的边疆,发现全新的资源与解决之道,只有这样,古老的美洲悲剧,才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