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魂汉神》 朱步冲解读
《和魂汉神》| 朱步冲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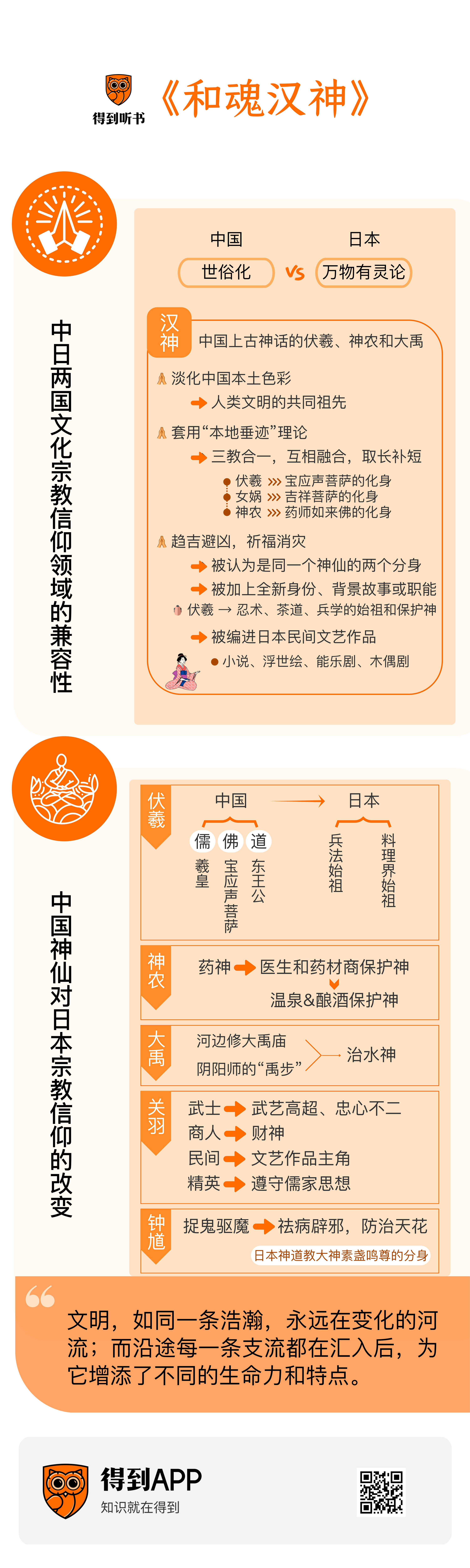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历史学家吴伟明的《和魂汉神》,副标题是“中国民间信仰在德川日本的本土化”。
对中国民间神话传说感兴趣的朋友,估计都听说过“八仙过海”的故事。而我们今天想要介绍的这本书,研究的,正是一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八仙过海”:意思就是,随着中日两国间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持续深入,很多中国民间信奉崇拜的神灵,也东渡日本,并且顺利扎根,成为日本民间宗教信仰的一部分。
作者吴伟明,是中国香港大学日本研究学系教授,专研中日文化交流史。他在本书序言中说,撰写这样一本研究著作的动力,是基于自己在日本游历,访学时萌发的兴趣:传说中受命出海,寻求仙药的方士徐福,变成了日本沿海地区的守护神;而中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神灵伏羲,大禹也在日本民间被崇拜,这种文化现象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随着研究的深入,吴伟明发现,中国民间信仰从12世纪初,至17世纪初,已经陆续传入日本,而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中日经济文化交流迎来黄金时代,这种宗教信仰上的融合也迎来了高峰。
直到今天,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烙印,在日本民俗文化中,依旧清晰可见。在日本各地的庙宇里,依旧供奉着关羽、钟馗、妈祖等来自中国的神仙,也被称为“汉神”;他们的故事,也一再被写入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搬上舞台;不过,这些外来神仙的形态,职能乃至背景故事,已经不同程度地本土化了。作者吴伟明,就形象地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和魂汉神”,这也算是本书书名的来历。
吴伟明在本书一开头就说,宗教信仰的传播和演变,是观察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有趣切入点。早在距今大约1700年前,随着中国逐渐向周边国家地区系统输出文化与技术,增强经济与政治交流,东亚地区,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东亚汉字文化圈”。正如日本历史学家气贺泽保归所说的那样,当时的东亚,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有四大共同元素:汉字、儒学、律令制国家体系,以及宗教。
然而,日本无疑是东亚“汉字文化圈”里,最具个性的一个成员。对待中国文化,日本在吸收的同时,都会做出改造和调整,以便配合日本的政治社会现实,作为对日本传统价值观和本土文化的增强和补充。所以,来自中国的历史人物、鬼神精怪、概念,甚至语言词汇,都会被日本在引进之后,赋予更多的内涵,或者做出全新的解读。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读完这本薄薄的小书,相信你一定会对一年多年来,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互动模式,以及中日两国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产生更深刻、丰富的理解。接下来,我就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中日两国融入“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大背景,以及中日两国文化上的兼容性,如何反映在宗教信仰领域。而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再随着作者吴伟明的讲述,来具体看看伏羲、神农、关羽、钟馗等中国民间神灵,是如何扎根日本民间,并且被重新改造为日本本土宗教信仰的一部分的。
一说到古代的中日交流,可能大家想到的,是隋唐时代,日本多次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前来中国系统学习引进各类技术、商品、书籍,甚至典章制度等等。但实际上,从宋代到明代,由于中国东南沿海经济不断发达,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文化往来,就攀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峰。
中日之间的海洋贸易,被称为“唐船贸易”。由于德川幕府时代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中国与荷兰商船,只留长崎一个港口开放 ,所以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船,都把货物先运送到长崎,与当地德川幕府指定的进口代理商,叫“唐方”来进行贸易,而“唐方”为了应对蜂拥而来的中国商船,也必须雇佣在日本定居的中国移民来处理沟通翻译和事务性工作,这些翻译被称为“唐通事”。
日本出口到中国的,除了铸造货币急需的铜,还有海参、鲍鱼、鱼翅等高端海产食品,以及雨伞、纸扇、刀剑等手工业商品,而中国向日本出口的,主要有药材、瓷器、丝绸、砂糖等副食品。1800年12月,有一艘从浙江乍浦出发,原本驶往长崎的“唐船”,叫“万胜号”,因为遇到风暴,漂流到日本静冈县附近搁浅,船上装载的货物,居然有将近70吨,包括药材、砂糖、水晶、染料等等。中日之间海洋贸易的兴盛,可见一斑。
在长期的中日交流中,来自中国的各类书籍经典,也随着其他技术和商品,持续输入到日本。由于汉字是当时东亚地区的通用语言,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取向、价值观,以及浩繁的人物典故,都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形式,传入日本等周边国家,而宗教信仰,也是中国文化输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中日两国虽然在文化特质上截然不同,但在宗教信仰领域,却拥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得到听书曾经解读过许倬云先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书中说,中国传统宗教的一个特征,则是世俗化,不仅各种自然力量会被人格化体现为神仙,历代帝王名人、忠臣良将,也会被民间封为神灵。这既是中国人惯用的感恩情绪在推动,也是盼望这些人对苍生的贡献,可以持续长存。同时,神仙的功能性设定,也非常具体,必须要照顾到日常生产起居中琐碎的方方面面:比如专门保佑远航水手的妈祖、伏魔捉鬼的钟馗等等。
巧合的是,中国这种世俗化的宗教信仰崇拜,和日本传统精神里的“万物有灵论”,十分契合。所谓“万物有灵”,说白了就是,古代日本人相信,自然界中万事万物,从山川河流,到动物植物,甚至人间的建筑器物,都可能成为人格化的神灵。而一些生前作恶多端或者含冤而死的人,死后会变成厉鬼或者怨灵,危害人间。人类要想平平安安,就要和它们搞好关系。
在我们解读过的《发现阴阳道》里,曾经提到过,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和相应的占卜、相面、巫术等等,从六世纪开始,传入日本,被天皇朝廷和宫廷贵族看重,所以间接也促进了中国传统宗教思想在日本的普及。
早在佛教进入日本的同期,这些林林总总的中国神仙,也进入了日本,被统一称为“汉神”。
早期被引入日本的中国神明,就有来自中国上古神话的伏羲、神农和大禹。原来,自从公元8世纪奈良时代起,来自中国的儒家经典就逐渐进入日本,由于日本当时也跟随中国,认为中国上古时代,是治理良好、圣人辈出的理想时代,所以伏羲、神农和大禹也被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所崇拜。为了让日本普通民众能够顺利接受这三位外来的大神,日本当时的儒学家、佛教高僧和贵族公卿费了不少脑筋,宣传的调子不外乎两种,一是利用儒学“天下一家”的精神,淡化这三位神仙身上的中国本土色彩,强调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祖先。
另一种宣传口径,是强调,他们和日本本土的神仙,其实是一家人。其实早在奈良时代,为了把经中国传入的印度佛教本土化,日本佛教僧侣就吸取了东晋时期,一位中国高僧,“僧肇”的理论。僧肇提出一个什么理论呢?就叫“本地垂迹”; 就是说,佛教中的神明,也就是各位佛祖和菩萨,为了普度众生,早就分出了很多化身,前往印度之外的各个国家、地区。这些化身到了目的地之后,为了搞好本土化,吸引当地老百姓来听自己的宣教,就以当地人熟悉的本土神仙面目出现:比如,日本神道教的最高神,天照大神,就变成了佛教里大日如来,在日本列岛上的分身。
所以,当看到中国来的鬼神之后,日本人就灵机一动,说,也可以套用这个“本地垂迹”理论,把这些中国神仙,也收编进佛教和神道教的神仙系统里,比如日本的僧侣就说,伏羲和女娲,就是佛教中的两位菩萨,宝应声菩萨和吉祥菩萨的化身;而神农呢?因为他勇尝百草,首创了医学,所以就被中国佛教僧侣,称为药师如来佛的化身,这个观念,也被日本人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这样一来,日本的民间宗教信仰,就出现了一种三教合一,互相融合,取长补短的局面:比如在日本至今还被信仰崇拜的“七福神”,就包括三位来自中国的神仙,三位佛教菩萨和一位日本本土神仙。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一些日本历史和文化学者就总结说了,奈良时代,日本的自我定位,是东亚的偏僻边陲地区,困难户。从整个东亚地区来看,经济文化中心是唐代中国,宗教信仰的中心是印度;佛教寺院的金碧辉煌、佛教经典的博大精深、佛像的精雕细琢,以及佛教做法事的宏大排场,加在一起,让简陋的日本神道教自惭形秽。所以,让日本神道教、印度的佛教,和来自中国的民间信仰合流,也算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自我安慰。
不过,对于一般日本老百姓而言,崇拜神明,信仰宗教的理由很直接,就是趋吉避凶、祈福消灾,这一点和中国老百姓并没有什么不同;前面我们说过,日本传统的宗教信仰,是万物有灵。所以在中国民间宗教鬼神信仰进入日本之前,日本本土已经有了大量属于本土宗教,叫神道教的守护神;所以,日本老百姓,在看到这些漂洋过海而来,功能都特别具体的中国神仙之后,第一反应就是,眼熟!可以拿现成的本土神仙模板来套。所以,中国来的神仙,能不能打动日本老百姓,其实就靠两个简单粗暴的指标来衡量:第一,专业是不是对口,也就是这位大神是不是负责保佑自己所从事的行当,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气。第二,就是灵验不灵验,这个就要看老百姓民间流传的口碑。当然了,名人效应对口碑影响比较大,就像今天的IP拉动流量:比如对关羽的崇拜,就因为十七世纪,《三国演义》故事在日本民间的流行,而进一步兴盛。
中国民间鬼神被日本老百姓接纳并信奉,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作者吴伟明就说,首先,是在日本本土的庙宇里和功能、身份相近的日本神明一起被膜拜祭祀,甚至被认为是同一个神仙的两个分身。 其次,是被日本老百姓加上了全新的身份、背景故事或者职能,比如中国的伏羲,到了日本,还变成了忍术、茶道、兵学的始祖和保护神。第三,这些外来的神仙,还会被日本人编进自己的民间文艺作品,如小说、浮世绘、能乐剧或者木偶剧里。
刚才,我们顺着本书作者吴伟明的思路,为你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和神灵崇拜,会在来到日本后,被无缝接纳的历史文化原因。接下来,咱们就通过几个生动的案例,来看看,这些漂洋过海而来的中国神仙,到日本后,它们的形象、职能发生了哪些有趣的变化,对日本本地民间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精神,起了哪些潜移默化的改变作用。
首先出场的,是我们在上一部分中提到的伏羲、神农和大禹。值得注意的是,在咱们中国民间,伏羲的形象、地位和功能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演变发展的。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传说,就是伏羲画八卦,所以就被尊为发明易学、天文占星的圣人。对伏羲的崇拜,首先发源于华夏文明的核心区,黄河流域,再逐渐随着华夏文明与中国版图的扩展而传播。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伏羲已经是身份横跨儒教、道教、佛教三大信仰的神仙:在儒家信仰中,他是羲皇,所谓“三皇五帝”中的一位;在佛教中,伏羲是宝应声菩萨的分身,而在道教中,伏羲是大家熟悉的“东王公”。
虽然伏羲的事迹,早早随着儒家经典在东亚的传播,进入日本。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伏羲还只是一个古代圣人和明君的形象,也只有爱好儒学的贵族和学者,对伏羲比较推崇;日本民间老百姓也没有把伏羲当神仙。比如,公元840年,日本的仁明天皇,就下过一道圣旨,说,因为天灾,决定减免老百姓的税收和劳役,理由是,中国上古的明君,伏羲、神农就是这样体恤人民的。在12世纪,日本有个高僧叫静宪,也用伏羲的典故来劝诫当时的后白河天皇,说您不要沉迷游乐宴会,因为即使是伏羲这样的圣人,尚且时不时要探查民情,知民间疾苦。
到了17世纪,德川幕府时代,随着战乱的结束,日本社会进入一个较为长期的安定时期,经济文化繁荣,再加上幕府极端提倡儒学,所以作为儒家尊崇的伏羲,就被日本当时的一些学者,甚至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拿出来给自己背书。
由于伏羲属于上古神话人物,所以各种经典里对他的记载篇幅有限,比较零碎,所以这也正好给了日本人足够的想象空间,可以放手加以演绎,加上各种各样的职能 :比如一些兵法家,就说,伏羲首创的易学,对用兵之道,有指导性的作用,所以伏羲是兵法的始祖;甚至做日本料理的师傅也说,伏羲是料理界的始祖,保护神,因为上古时候,伏羲教大家祭祀神明和先祖,而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把珍贵的家用牲畜宰杀,再烹饪,作为合格的祭品,在这个过程中,料理和烹饪技术就被伏羲发明、改良。
比起伏羲,大禹和神农在日本民间,显得就比较“用户下沉”,在下层社会里,对他们的崇拜就比较普遍。这是为什么呢?用咱们今天互联网产业的话来说,因为这两位大神行使的职能,都是普通人的“刚需”:大家知道,在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一部药典,《神农本草经》,作者被假托为神农本人。在唐代,这本药典就传入了日本,被广泛引用,比如日本天皇宫廷内的御用医药机构,叫典药寮,就把《神农本草经》当作基础教材。
由于神农在中日两国,都被当作药神来崇拜,而身体健康、祛病长寿又是普通人的普遍愿望,所以到了德川幕府时代,神农就变成了医生和药材商普遍供奉的保护神。很多汉方药,也就是日本本土化的中药,在给药丸取名的时候,都会加上神农两个字,像什么“神农解毒丸”“神农感应丸”之类;因为这样叫,会让前来求医问药的老百姓觉得,这药肯定有疗效。
不仅如此,在日本著名的商业城市大阪,有一个药材商铺云集的商区,叫道修町;1780年,在这里做买卖的药材商人,就集资建了一座神社,把神农和日本自己的药神,叫少彦命名,一起来祭祀,并且还说,这两位药神,实际上是互为彼此的分身。有了这样的新人设,于是神农的职责又扩大了,他和少彦命名一样,同时还兼职当上了保佑酿酒工匠和温泉的神仙。 所以,如果大家去日本旅游,就会在一些温泉旅馆里,看到神农的塑像或者画像。
同时,在普通日本老百姓家里,常常也会挂一幅神农画像,因为神农有祛病消灾的法力,可以保佑全家人不得传染病。甚至,德川幕府的将军,也把神农请进了自己家的神社进行供奉,希望他保佑自己的统治。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禹。大禹身上的光环有两个,一是中国上古时代的明君,第二就是曾经成功治理洪水,造福万民。而日本,恰恰是一个河川纵横,地形复杂,洪灾等自然灾害频繁的地方,所以日本民间对大禹的崇拜,也可以说是一种天然的“刚需”。
比如,日本京都附近的著名河流,鸭川,在1288年发过一次大洪水,把桥梁都冲走了,根据民间传说,正当负责防洪的官员惊慌失措的时候,鸭川当地的地藏菩萨,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国土地城隍一样的神仙,就化身为一个和尚上门,对他说,要想杜绝洪水,就应该在鸭川的东岸给大禹修一座庙。 于是洪水之后,当时统治日本的镰仓幕府就下令,重新修桥的同时,在旁边修一座禹王庙,用来震慑河流,不再发水。所以,古代日本历代政府,就开始陆续在容易泛滥决堤的河流边,修大禹庙,或者立一块禹王碑。一来是祈求大禹显灵,制止洪灾,二来是彰显自己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的功绩:比如,在赞岐国,也就是今天的日本香川县,曾经有一条泛滥的河流,叫香东川。17世纪初,德川幕府刚刚建立的时候,有个日本著名的水利工程师,叫西岛八兵卫,他花了13年时间,完成了香东川水利工程的建设。于是,西岛就在河畔立了一块刻有大禹名字的石碑,他自己,也被当地百姓尊称为“赞岐国的大禹”。
另外,日本宫廷中负责占卜、祭祀、施法的神职人员,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阴阳师”,他们有一种驱魔消灾的仪式,叫“禹步”,大禹的禹,步伐的步,就是模仿大禹走路的样子。“禹步”,据说为大禹本人创立,是大禹在治水祭典上向鬼神祈祷的仪式,后来被中国道家引入,发扬光大,又传到了日本。具体来说,“禹步”就是要施法者按照一定的步伐和节奏,朝着既定的方向一边念咒,一边按照天空中遁甲九星连接的轨迹走动九步,用来驱逐恶鬼。根据日本典籍记载,历史上第一个实施过“禹步”仪式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阴阳师安倍晴明。
不仅如此,在日本各地,大概在四月春天的时候,还会举办民间祭典,祭祀大禹。逐渐地,大禹就成为日本民众心目中最灵验的治水神。到了18世纪之后,日本著名的绘画艺术“浮世绘”流行之后,“大禹战蛟龙”这个来自中国的神话故事,也成为历代浮世绘画家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只不过,大禹的形象、衣着与兵器,已经转变为当时流行的日本武士形象,与刚刚传入日本时,相去甚远。
好了,接下来出场的两位东渡日本的神仙,无论在他们的故乡中国,还是日本,就比较广为人知。他们,分别是武圣关羽和捉鬼的判官钟馗。
关羽的形象,是在魏晋之后的民间艺术创作中,一点点丰富起来,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历史人物,变成了神灵,以及武勇和忠义的化身。其中的具体过程,得到听书曾经专门解读过一本《关羽》,在此就不再赘述。总之,在诸多戏曲、民间传说和评书话本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三国演义》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兴盛,在14世纪中后期,流传到了日本。
关羽的武艺高超,对主君刘备忠心不二;这两个特征,和日本武士阶层的守则纲领“武士道”的宗旨,非常契合,再加上在中国本土,关羽已经成为佛教里的护法神,所以当时在日本,最先把关羽当作偶像和神灵来崇拜的,就是封建武士阶层。在14世纪,日本国内也发生过一次长时间的内战,史称南北朝时期,最终,北朝武将足利尊氏统一全国,建立了室町幕府,当时民间就有传说,说足利尊氏上阵打仗的时候,在自己的军营里就悬挂关羽的画像,结果真的引来神灵关羽助战。而在取得胜利返回京都后,足利尊氏还请了许多画家,来给自己画肖像,描绘自己凯旋的英姿,这些画家也纷纷把足利尊氏的形象往关羽身上靠:全身披挂,手持大刀,身骑骏马。
德川幕府建立后,随着中日两国贸易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常驻长崎港,更有部分移民从中国渡海而来,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国东南沿海故乡的建筑、土特产,也带来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作者就考证说,长崎城里,中国海商和移民就建了很多寺庙,寺庙里供的是什么神仙呢?首先是保佑水手出入平安,避开风浪的妈祖,其次就是关羽,因为这个时候关羽在中国本土已经当上了财神,而在平安抵达异国他乡后,能够通过贸易发财致富,是这些中国商人和移民的共同愿望。
经过中国商人和移民这么一宣传,来长崎做买卖的日本老百姓也逐渐觉得,关羽这个神仙,一专多能,神通广大;所以对于关羽的信奉,就逐渐从长崎,扩散到日本各地。很多高僧在自己开山建寺的时候,都会隆重地给关老爷修一间专门的殿堂,从中国本土请一尊关羽像放在里面供着,很多日本老百姓还学会了中国的求签习俗,都说,关帝庙里的签,特别灵验。
关羽在日本民间的热度,还体现在各类文艺作品对他的改编和描写里。在日本特色的绘画“浮世绘”、歌舞伎舞台剧,以及被称为“净琉璃”的木偶剧里,以关羽为主角,三国为背景的作品,也是层出不穷,主题大多都是彰显关羽的勇武,比如刮骨疗毒、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等等。 甚至,当时的日本市民情色文学,也要把关羽写进作品,改造为女人无法抗拒的情圣男主角,把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传奇,改编为关羽夜宿花街柳巷,一夜连续约会五大花魁名妓的艳遇故事。
不仅是民间老百姓,日本的精英阶级,也对关羽崇拜有加,但崇拜的点,主要是他恪守儒家的道德宗旨。在整个德川幕府时代,日本文学界一共出现过几百首歌颂关羽勇武、忠心、遵守儒家思想的汉文诗歌。当时有个大阪儒学家,兼文学家中井竹山,由于生日和关羽的诞辰在同一天,非常引以为傲,于是给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叫“同关子”;他还请人给自己刻了一枚私人印章,用来做自己书信和书画作品的落款,上面是四个字“髯公同物”。简单四个字,蕴含了中井的自我期许和激励:翻译过来就是,以这枚印章,提醒自己,时刻要学习偶像美髯公关羽的言行和为人。
最后,我们来看下面目狰狞、主管捉鬼的钟馗。在中国道教信仰里,关羽、钟馗和真武大帝,被并称为“三大伏魔帝君”。作者吴伟明分析说,钟馗形象和传说引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平安时代末期,日本国内政治动荡,各种灾害和灵异事件不断出现,而钟馗的人设,正好是捉鬼驱魔,所以钟馗崇拜,首先在日本民间流行开来。到了室町幕府时代,也就是公元14到16世纪,各种流行疾病又在日本横行,尤其是致命的天花;于是钟馗又被日本老百姓安上了祛病辟邪、防治天花的功能,还被当作是日本神道教大神素盏鸣尊的分身。当时,日本的民间艺人甚至还创作了一出能乐剧,剧情结合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钟馗捉鬼故事:说杨贵妃忽然得了重病,唐玄宗急得一筹莫展,结果钟馗显灵,斩杀了附体杨贵妃的恶鬼。
在16至17世纪的日本战国时代,很多信奉佛教的战国武将,为了彰显自己的武勇,震慑敌人,纷纷在军旗和铠甲外罩的战袍上绘制钟馗的形象,甚至模仿神像和绘画中的钟馗,留起了浓密蓬松的络腮大胡子。这种大胡子,就被称为“钟馗髭”,一直流行到德川幕府时代。
直到今天,在日本各地许多民间祭典活动中,都有钟馗的身影。在祭典游行中,民众会推着载有巨大钟馗塑像的花车游街,同时还会上演舞剧“钟馗捉鬼”,钟馗画像也在被当作门神,贴在民居的大门口。
好了,这本《和魂汉神》的基本内容,说到这里就介绍得差不多了。本书虽然是一部学术巨作,但是作者吴伟明在写作中,不仅参考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还踏访了日本各地的庙宇神社,亲身体验了中国民间宗教对于当地民众信仰和风俗的影响,收集了许多传说和民间逸闻趣事,所以本书读起来让人感觉是深入浅出,饶有风趣。
在本书中,作者吴伟明提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够漂洋过海,在日本落地生根,首先要归功于两国持续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中国建构的东亚汉字文化圈:在东亚,中国长期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不仅持续向外输出各类产品、技术与制度,也让中国文化的精神,演化为东亚地区共有的价值文化。
中日两国交流早期,日本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属于积极输入方,努力接受中国传入的技术、文化、商品、制度等成果,既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算是积极融入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表态,和文化精神上的自我安慰。
其次,古代中日两国,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高度趋同性,也让日本在接受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抵触与障碍。无论是妈祖、关羽还是钟馗,他们身上高度人格化,和现实具体化的职能,都与日本本土宗教里的各路神灵高度相似,从而迅速融入日本社会的信仰系统。同时,强调注重自身文化特性的日本,又对这些来自中国的各路神仙,进行了长期的改造,赋予了他们本土化的形象、背景和故事传说。
不仅如此,我们可以深刻了解到,文化在不同地区、民族、文明之间的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被不断改写与再创作的过程。每一批传播者,都会根据自己民族与文化的审美与价值取向,对这些文化结晶中的叙事细节,以及形象设定进行修改、补充,甚至二次创作。所以说,文明,如同一条浩瀚、永远在变化的河流;而沿途每一条支流都在汇入后,为它增添了不同的生命力和特点。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此外,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文化在不同地区、民族、文明之间的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被不断改写与再创作的过程。
-
文明,如同一条浩瀚、永远在变化的河流;而沿途每一条支流都在汇入后,为它增添了不同的生命力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