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关》 张明扬解读
《入关》| 张明扬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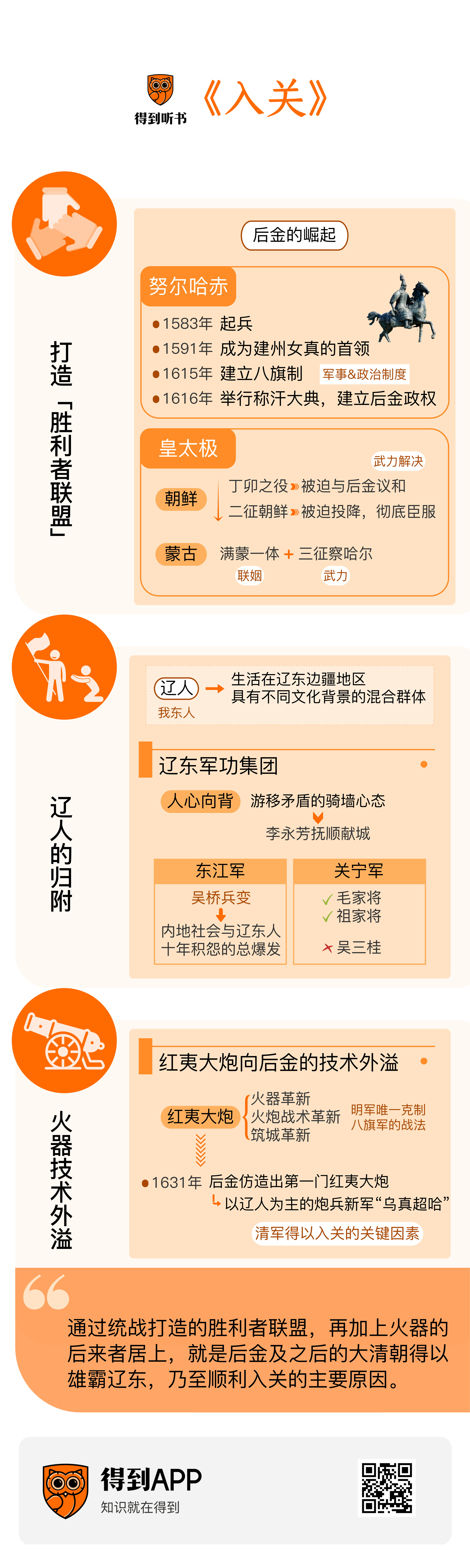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张明扬,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我的新书《入关》。
明亡清兴,可能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段古代历史。通常的说法是“明亡清兴六十年”,也就是从1583年努尔哈赤以13副盔甲起兵为起始,以1644年八旗入关为结点。
而这本《入关》,覆盖的时间更为精简些,叙述重点从1618年努尔哈赤誓师伐明写起,以1644年为全书终结,前后共26年。请注意,在1636年之前皇太极称帝之前,那时还没有大清,只有后金这个说法。
从我开始写《入关》,到书出版,一直有人会问:明清之变,已经出版了那么多书,你为什么还要写这本《入关》,这本书的新意在哪?
对此,我有个最简略的回答是:在以往的明亡清兴历史叙述中,重点往往都放在“明亡”之上,而忽视了“清兴”。这也就是我在《入关》后记中说到的:明军打不过清军,似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明朝自身出了问题”:党争、奸臣、叛将、昏君……这些年,还多了袁崇焕与毛文龙这两个责任人。
这背后的历史观似乎是:明亡清兴,仅仅是明朝自身的问题,与后金清朝是否强大,八旗军是否善战,八旗军的火器革命是否成功,努尔哈赤皇太极是否英明,清朝的统战是否有效,似乎干系都不大。
但是,这种看法明显有偏颇,一个王朝的衰亡,怎么可能只与自身的内政相关,而与敌人的崛起兴盛关系不大呢?
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刷新只有“明亡”,而没有“清兴”的传统历史叙述。
“清兴”的大方向虽然有了,但这终究是一个过于宏大的概念。接下来,我将分三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首先,我将以东北亚地缘政治的视角,讨论下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是如何一步步突破明朝——蒙古——朝鲜三方结成的C形包围圈,进而将朝鲜和蒙古发展为自己的盟友;接下来,我将引入《入关》这本书中一个相对新鲜的概念——辽人,来重点阐释辽人是如何成为后金与明朝争霸时的胜负手的;最后,我还会谈到皇太极主导的火器革命,是如何使后金反客为主,在火器上压倒明朝,并颠覆了明朝在关外的火器优势的。
首先,让我们看看与明朝开战前,后金的崛起状况。
当时的女真分三个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从1583年起兵到1591年,努尔哈赤花了八年时间,基本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成为建州女真的首领;而到1616年,努尔哈赤已接连兼并了海西女真的三个大部族:哈达、辉发和乌拉,已成为女真世界主宰者的他这才在这一年举行了称汗大典,建立了后金政权。
从一个部落首领到一个民族国家的大汗,努尔哈赤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建立后金前一年,也就是1615年,他还建立了八旗制,可动用的军队至少已达6万之众。
可以说,在与明朝开战前,努尔哈赤在军事、政治制度,乃至内部集权上都做好了起兵的一切准备。
也许会有人问,在努尔哈赤的崛起过程中,明朝就一点没注意到么,放任他一路坐大?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明朝在辽东的主要对手是蒙古,女真人是相对不被重视的次要对手;第二,在女真各部酋长中,努尔哈赤对明朝的恭顺程度绝对是第一位的,曾多次亲自进京朝贡,明朝非但对他疏于防范,反而通过加封官职成为其崛起的助力者;第三,1592年爆发的日军侵朝战争严重牵扯了明朝辽东边军的注意力,主力在援朝战争中损失惨重,在辽东事实上造成了一个军事真空区。
尽管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无往不利,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决定性地击败了明军野战军主力,凭借女真本部这数万人,后金称霸辽东是毫无悬念的,但要实现入关等更高一层的战略目的,则还是困难重重的。努尔哈赤与自己的继任者皇太极,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不遗余力地继续扩大女真政权的势力,让自己手中尽量拥有更多的筹码。
即使暂时不考虑入关,后金政权也在战略态势上需要迫切解决一个问题:明朝在东北亚通过传统的结盟,与蒙古大汗林丹汗、李氏朝鲜一起,三方联合对后金政权构成了一个C形战略包围圈。
而在明朝这边,除了宁锦防线的辽东边军之外,在皮岛上还有毛文龙的数万军队。
于是,皇太极一上台,就在积极寻找破局之策,击破C形包围圈。
皇太极的第一个目标是朝鲜。作为明朝的羽翼,尽管朝鲜军事实力平平,但仍可有效牵制着后金,令后金陷入两线作战的风险。
朝鲜本为大明藩属国,萨尔浒之战中还曾出兵一万三千人,协同参战。1623年,朝鲜还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新任国王仁祖李倧一上台,就全盘推翻了前任国王的中立外交政策,一切以尊明为本位,拒绝与后金产生任何官方交往。
为了消除腹背受敌之战略窘境,皇太极即位仅几个月后,就命二贝勒阿敏率领三万余八旗精兵,发动对朝战争,史称“丁卯之役”。
朝鲜虽在战场上一败涂地,国王仁祖率百官从王京仓皇出逃至江华岛避难,但坚持不降,派人去明朝求援。
虽然明朝中枢积极筹备援朝,主张趁后金空虚,从海上及宁远多个战略方向直捣辽东腹地,但袁崇焕却对救援朝鲜表现得极为冷淡和消极。
眼见明朝援军无望,朝鲜这才被迫同意与后金议和,放弃了与明的反金军事同盟,与后金结成了所谓的“兄弟之国”。
十年后,皇太极第二次对朝鲜发动战争,刚刚称帝建立清朝的他统领十二万大军,亲征朝鲜。
皇太极二征朝鲜的主要原因是,朝鲜并没有认真履行盟约内容,不仅继续保持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而且对盟约中自己应尽的义务,则消极对待,迟迟不肯履行。
经过十年的无效交涉,皇太极在愤恨日积中逐渐明白,朝鲜问题除了武力解决之外,别无他途。
与上次一样,这次战争仍无悬念,朝鲜军队照旧是溃不成军,朝鲜国王逃到了南汉山城。死守一个多月后,内无粮草,外无援军,朝鲜国王于1637年年初被迫亲自出城投降,对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君臣大礼,象征着朝鲜彻底臣服于皇太极政权。
由此,朝鲜由清朝卧榻之侧的敌人,变为盟友,皇太极彻底解决了朝鲜问题。
在二征朝鲜前一年,也就是1635年,皇太极也彻底解决了蒙古问题。
蒙古问题远比朝鲜更为复杂,也远非是单纯的武力征服可以解决的。
在后金清朝崛起的时代,蒙古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军事强权,严格说来,是几个甚至几十个军事部落实体。但与此同时,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一系的蒙古大汗仍然存在,只是弱化为一个名义上的蒙古世界精神领袖。此时名义上的蒙古大汗,是林丹汗。
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后金,以及清朝对蒙古的基本国策就是,一面尽力拉拢漠南蒙古各部,一面全力打击林丹汗。
1612年,努尔哈赤迎娶了漠南蒙古科尔沁部的一位王公之女,开启了“满蒙联姻”乃至“满蒙一体”这一延续近三百年的历史进程,在努尔哈赤时代,仅与科尔沁部就联姻十次。
满蒙一体,是努尔哈赤崛起之路上的关键一步,不仅极大扩张了他的实力,也让建州女真及之后的后金实现了从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多民族帝国的转变,实为清帝国建国之基。
而在另一面,由于努尔哈赤对蒙古世界的渗透越来越深,这让心怀复兴蒙古帝国大志的林丹汗不寒而栗,从而与明朝越走越近,直至结成了反女真联盟。
壮志凌云的林丹汗既幸运也不幸。林丹汗之幸在于,这个时代的蒙古各部战斗力偏弱,没有能够抵抗自己的对手,他直属的察哈尔部战力已堪称全蒙最强,这似乎是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若无外力介入,林丹汗即使无力最终统一蒙古,但武力整合漠南蒙古还是有可能的;而林丹汗的不幸在于,他的战略机遇期为勃兴的后金帝国所笼罩,同样野心勃勃的皇太极不仅不会坐视林丹汗统合蒙古,更有缔造满蒙帝国之志,这就意味着,皇太极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摧毁林丹汗的蒙古共主之位,并取而代之。
1628年和1632年,皇太极两次亲征察哈尔,但都未抓住察哈尔部主力,林丹汗在八旗大军压境前,便逃之夭夭。
但是,这两次军事意义不大的皇太极亲征,却令林丹汗在政治上一败涂地,以至众叛亲离。道理很简单,那些尚在观望的蒙古诸部,甚至包括察哈尔部在内,看到他们的大汗逢战必逃,最终认清了林丹汗的外强中干,转而将武德充沛的皇太极视作草原上的新主人。
1634年,林丹汗身患天花死于逃亡途中,成为蒙古帝国的末代大汗。
第二年,皇太极决定三征察哈尔,给黄金家族奉上最后一击。穷途末路中,年仅14岁的林丹汗之子额哲与母亲一起投降了后金。
对于皇太极而言,额哲归降有两大利好:其一,献上了传国玉玺;其二,以额哲为首的漠南蒙古四十九个王公齐聚盛京,承认皇太极承继了蒙古大汗的汗统。这两者直接促成了皇太极的建立新朝与称帝。
而对于明朝而言,林丹汗的覆亡,标志着大明在蒙古世界失去了最后一个有实际军事能力的盟友。
至此,在接连收服漠南蒙古和朝鲜之后,清朝的战略处境由被明朝、蒙古和朝鲜三面包围,反客为主为三面合围明朝。在《入关》中,我将之称为打造“胜利者联盟”。
短短十年间,这是多么奇迹般的大反转。
朝鲜和蒙古的归附是皇太极打造胜利者联盟的重大收获,但他统战的最关键一环其实发生在辽东内部,也就是辽人的归附。
所谓辽人,世代居住在辽东明朝实控区,在民族构成上虽以汉人为主体,但由于女真、蒙古和朝鲜各族人口的迁入,实际上是生活在辽东边疆地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混合群体。以李成梁家族为例,其先祖即来自朝鲜半岛。最迟至明代中叶,族源不一、身份各异的辽东人,在卫所体制的整合下,逐渐塑造出独特鲜明的边疆军事社会与尚武刚毅的社会文化,形成了比较普遍的地方群体认同意识,自称“我东人”。
努尔哈赤起兵前,在饥荒、苛政与边患的凌虐下,辽东社会凋敝残破已久,对明朝的离心力也在苛政中日益增强。战前甚至曾有来辽东的明朝中央官员惊呼:“辽东危在旦夕”。
而在另一边,辽东本土的武将也逐步演变为以李成梁为首的,以贿赂与私人关系维系的军事利益集团,也就是《入关》一书中多次出现的“辽东军功集团”。
在努尔哈赤对明朝开战的第一战抚顺之战中,抚顺明军守将李永芳在接到劝降信后,先战后降,其间观望踌躇了很久。李永芳这种游移矛盾的骑墙心态是明末辽东军功集团的共性:他们无论对明朝与后金都谈不上有多少基于价值观的忠诚度,所谓的忠诚更多是惯性和机会成本,兵权、投机与效忠领袖才是辽人集团的安身立命所在。
在明清战争中,辽人与辽东军功集团的人心向背成为战争胜负的重要变量。这在以往的通俗历史出版物中,很少被重点提及。
自李永芳抚顺献城始,辽人与汉官便成为后金政权的重点吸纳与统战对象。尽管努尔哈赤统治后期,一度曾苛待前来归附的辽人,导致辽人对后金政权离心离德,而孙承宗与袁崇焕等负责辽东战事的明朝地方官员,也出台了“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来争夺辽人对明朝的支持,但皇太极继位后,立刻意识到之前的错误,迅速改弦更张,以更大的力度,争取辽民与辽东军功集团的支持。
在辽东战场上,辽人一度成为抗清之绝对主力。在正面战场的宁锦防线上,有孙承宗与袁崇焕打造的以辽人为主体,“以辽人守辽土”的关宁军;在“敌后战场”上,有毛文龙盘踞在皮岛的东江军。
后来,袁崇焕误杀毛文龙,崇祯再冤杀袁崇焕,一错再错之下,东江军与关宁军这两大辽人集团相继溃散,明清在辽东战场上保持多年的战略平衡由此被打破。
先是东江军。毛文龙死后,作为整体意义的东江军就此分崩离析,各寻出路。1631年年底,出身于东江军的孔有德所部在进援大凌河途中,于直隶河间府的吴桥发生兵变,是为震惊天下的“吴桥兵变”,从而直接导致明朝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式火炮部队和随军工匠投靠皇太极。吴桥兵变的直接起因是,主要由辽人构成的孔有德所部在关内沦为被防范和被歧视的对象,吴桥县民皆闭门罢市拒做辽人生意,辽军在冻饿交加中发生兵变。
故有说法称,吴桥兵变是“内地社会与辽东人十年积怨的总爆发”。
吴桥兵变后,孔有德、耿仲明与尚可喜这三位毛文龙昔日军中下属降清,清朝至此基本收编了东江军势力,也就是所谓的“毛家将”。回过头来看,起因坏在毛文龙被袁崇焕误杀。如果毛文龙不死,孔有德耿仲明此等东江军精英又怎会落魄离散,又怎会在内地汉人对辽人的歧视中冲冠一怒兴兵作乱。
而后是关宁军。袁崇焕死后,关宁军的实权到了辽人武将世家祖大寿家族手中,包括祖大寿的亲外甥吴三桂,所谓的“祖家将”成为明朝在辽东的最后军事存在。但与袁崇焕时代相比,明朝中央政权对关宁军的控制力已日益衰减。
在大凌河之战中,虽然祖大寿降而复叛,但“祖家将”中相当一部分能征惯战的将领,都投降了后金,“祖家将”事实上已被分为两部分,祖大寿和“祖家将”此时其实已是在明清之间“两边下注”。
大凌河之战后,大明“以辽人守辽土”的方略已然徒负虚名,辽人被内地社会视为异己视为奸细,皇太极则将收服辽人人心作为基本国策,极尽笼络之能事。在对辽军辽民的人心争夺战中,皇太极赢下了关键性的一局。有了辽人的主动归附,满人才第一次具备了问鼎关内的人力基础。
1642年的锦州之战后,剩下一半的“祖家将”也追随祖大寿降清。随着祖大寿的投降,以辽人为主体的八旗汉军也正式编立完成,八旗汉军计一百二十九个牛录﹐两万四千五百名官兵。至此,除了吴三桂以外,辽人、辽军和辽东军功集团全部被纳入满人麾下。
皇太极有意照搬收服“毛家将”和“祖家将”的模式,劝降吴三桂。为此他两次亲自写信吴三桂,一面劝他审时度势,一面许以高官厚禄。
但吴三桂还是拒绝投降。无论日后吴三桂的节操如何不堪,至少在那个历史时刻,大明国运暗淡,人心浮动,吴三桂还是坚持不降,成为大明王朝最后时刻的重要倚仗之一。
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缢于煤山。此时,放在吴三桂和关宁军余部面前的选择只有两种:投降李自成或归附清朝。对于吴三桂而言,谁都不降就是自取灭亡,不仅是腹背受敌,而且沦为没有任何战略腹地和后勤补给的孤军。吴三桂既没有这么愚蠢,也没有这么愚忠。
吴三桂本想投降李自成,但后来得知,闯军进入北京后,军纪不佳,捉来许多明朝宗室大臣严刑拷打,要求他们交出家产,自己的父亲吴襄也未能幸免,再加上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抢去,于是吴三桂冲冠一怒,最终降清于山海关。吴三桂降清,标志着辽人与辽东军功集团的最后一支抗清势力也加入了大清的“胜利者联盟”。明清战争的一条暗线,即双方围绕着辽人进行的“忠诚竞争”,双方争夺的不仅仅是辽东的城池土地, 也在争夺着那些土生土长的辽人与辽将。角力的结果是八旗汉军建立,辽西“祖家将”和海上“毛家将”先后投降清朝,清朝联合辽人进关,统一中国。
所谓的满人入关,实为满蒙辽“联合入关”;所谓的满蒙联合政权实为“满蒙辽联合政权”。辽东军功集团、辽人与清廷结成一强有力且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在入关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从帝国边陲登上历史主舞台,建立了辽人前所未有的功业。
崇祯自缢后,明朝并未就此灭亡,从弘光帝到永历帝,忠于明朝的势力在南中国坚持抵抗,屡败屡战,接连建立起多个抗清政权,这在历史上被称作“南明”。在对南明政权的追杀中,吴三桂等辽人军队甚至成为绝对主力,满蒙八旗反倒因气候与地理环境等原因成为辅助力量。一个有力的例证是,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即死于穷追不舍的吴三桂之手。辽人,就这么在一波三折反反复复中,最终成为清朝入关的关键盟友。
清军消灭南明政权前后,辽人和辽东军功集团的势力臻于巅峰,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和吴三桂这四个辽人不仅封王,还分别镇守南方一省,作为封建藩王与满人中央政权共天下。但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辽人藩王对满人中央政权的价值下降,藩王庞大的军费开支对清朝财政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再加上康熙在汉化教育中深受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浸染,在价值观上无法容忍辽人藩王的半独立政权,双方矛盾渐生,直至难以调和不可收拾。
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是为辽人与满人总决战;1681年,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自1610年代开始活跃于明清鼎革大变局的辽人势力最终黯然退场。
在汉人民间话语中,辽人是数典忘祖的汉奸;在满人王权话语中,辽人是反复无常的叛臣。在此种高度道德化的历史叙事中,辽人渐而被边缘化,甚至隐身于大历史中。
辽人的归附,不仅帮助皇太极完成了对胜利者联盟的打造,也意外促成了火器,特别是红夷大炮向后金的技术外溢。
在明清战争中,火器本是明军最为突出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在宁远之战中,明军首次在实战中运用红夷大炮,便让努尔哈赤遭遇了生平最大败仗,明军则取得了双方开战八年以来的首场大捷。
这也是红夷大炮第一次亮相于中国战争史。之所以叫“红夷大炮”,是因为明朝误以为这批炮产自荷兰,而荷兰人被称为“红夷”。
明军惨败于萨尔浒之后,明朝大臣徐光启痛定思痛,深感明军现有以佛朗机为主的火器装备已无法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因此以私人捐资的方式,向澳门葡萄牙当局求购新一代的西洋火炮,也就是红夷大炮。
凭借红夷大炮的火器革新,袁崇焕在宁远又启动了火炮战术革新和筑城革新,明军依托着这三重革新,在辽东战场上第一次找到了唯一一种可以克制八旗军的战法。
但即使在宁远之战后,后金仍未对红夷大炮的横空出世有足够的认知,没有识别出这是明军的一次划时代火器革命。在后金的文献里,宁远战败的原因被归咎于军队的糟糕表现、质量低劣的武器,甚至努尔哈赤的骄傲轻敌,而不是明军的红夷大炮。
1627年,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宁锦防线,这也是他即位以来第一次对明朝用兵。但在宁远和锦州坚城下,八旗军一筹莫展,再败于袁崇焕和红夷大炮之手。
宁锦之败后,皇太极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骑射,已不能适应火器革命时代的战争需要,为了取天下,后金也有必要造出自己的红夷大炮,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挑战宁锦堡垒群。
1631年,后金仿造出第一门红夷大炮,还为此成立了一支以辽人为主的炮兵新军,即所谓的“乌真超哈”,是为八旗汉军之滥觞。在数月后的大凌河之战中,首次出战的红衣大炮就为皇太极立下奇功,外击来援明军,内轰大凌河城,逼得祖大寿率军归降。
后金炮兵更大规模的一次升级也有赖于辽人。
吴桥兵变后,东江军一系的辽人将领孔有德、耿仲明与尚可喜相继归降,不仅给皇太极带来了更多的红衣大炮,还送上了一支受过葡萄牙人专业训练的工匠和炮手团队,增强了后金的炮兵实力和军工能力。而继袁崇焕被冤杀之后,明朝最精通火器技战术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却受吴桥兵变牵连被朝廷诛杀,明朝就此丧失了国内最精通火器的一线督抚。此消彼长之下,后金火炮部队已开始超越恃火器为核心竞争力的明军。
在明清战争的决定性战役松锦之战中,作为明清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炮对战,也是清军炮兵第一次在实战中全面压制明军炮兵,锦州、松山、塔山和杏山陷落皆有红衣大炮之功。
松锦之战后,明清火器强弱对比彻底逆转,甚至可以说是强弱悬殊,清军已拥有上百门红衣大炮,而逃回宁远的吴三桂所部仅剩下了十门红夷大炮,清军在火炮的数量和质量上均已凌驾于明军。
至此,红夷大炮入华不仅没有帮助明军达成克制八旗野战优势的预期目标,反倒为八旗军补全了攻坚能力不足的唯一军事短板,将清帝国塑造为骑兵与火器均称雄东北亚的超级军事强权,甚至因此被称之为“火药帝国”。
可以说,火器技术,特别是红夷大炮从明向清的转移外溢,是清军得以入关的关键因素之一。
通过统战打造的胜利者联盟,再加上火器的后来者居上,就是后金及之后的大清朝得以雄霸辽东,乃至顺利入关的主要原因。在《入关》一书中,我把这两大原因总结为“器”与“人”。
这可能就是清兴的终极奥秘。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代君主,将蒙古人、朝鲜人和辽人先后都纳入了“胜利者联盟”中,将建州女真这个偏居辽东一隅的部落,先是奠基了后金这个民族政权,继而缔造了清朝这个满蒙汉多元大帝国,在红衣大炮的加持下,大清跃升为东北亚压倒性的军事强权。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在以往的明亡清兴历史叙述中,重点往往都放在“明亡”之上,而忽视了“清兴”。
-
通过统战打造的胜利者联盟,再加上火器的后来者居上,就是后金及之后的大清朝得以雄霸辽东,乃至顺利入关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