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仙》 刘玄解读
《修仙》| 刘玄解读
关于作者
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范德堡大学亚洲研究和宗教学教授。研究领域为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六世纪的中国宗教史,以及宗教的跨文化比较。除本书(2009)外,还著有《述异:中国中古早期的志怪小说》(1996)《与天地齐寿:葛洪<神仙传>翻译与研究》(2002)《冥祥: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灵应故事》(2012)等。
关于本书
本书融合了多元的理论方法和坚实的中国古代文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修仙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互动。它描绘了修仙是一种社会氛围,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书里提出的研究范式对理解其他社会中的圣人角色也有帮助。本书先后获得美国宗教学会2010年度宗教研究杰出著作奖,和美国亚洲学会2011年度列文森奖。
核心内容
1.仙文化总集是怎么形成的?
2.人们如何运用它来达到现实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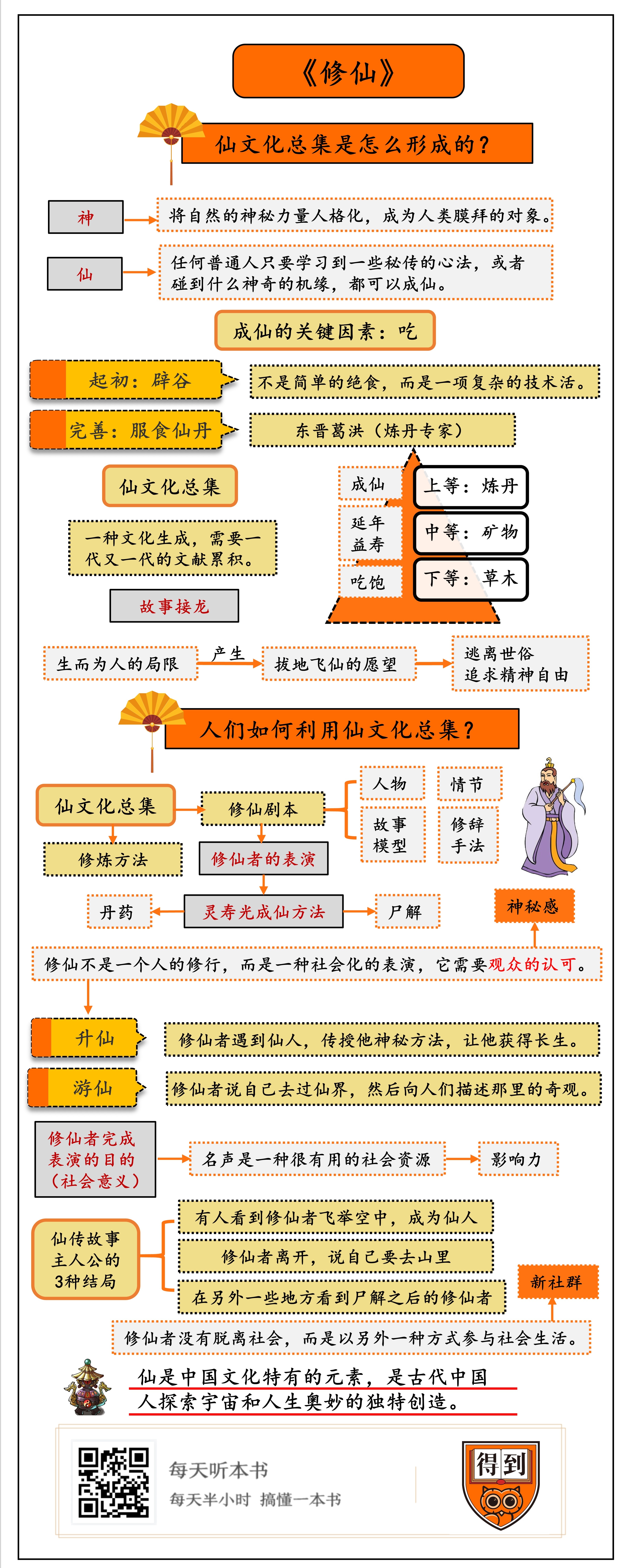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要为你讲的书,名字叫《修仙》。这本书说的是,中国古代的仙文化是怎么形成的?
说起仙,你会想起谁?三头六臂的哪吒?四处云游的赤脚大仙?组团过海的八仙?这些神仙,来自不同时代的故事,各有各的神通。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首先当然是长生不老;其次,既然是神仙,总得会点法术,不管是变身隐形,还是腾云驾雾,要有些超乎常人的能力。
作为一个理性的现代人,我们当然知道,这些都是古人的浪漫想象。有的人可能还会说,神仙世界是古人的迷信,不能当真。但是,古人真的相信神仙存在吗?还真不一定。三国时的曹植就很理性,他虽然写过不少描写仙界漫游的诗,但是他不信仙,还批评过当时流传的成仙故事十分虚妄。那时候,像曹植这样的明白人,其实不在少数。这样看的话,仙这个事还挺奇怪的。这些人明知道成仙荒诞不经,却又写诗撰文去描绘仙的世界。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康儒博是一位美国汉学家,专门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史。他的几部著作,讨论的都是神仙鬼怪的事,比如《述异:中国中古早期的志怪小说》《冥祥: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灵应故事》等等。在这本《修仙》里,康儒博带我们回到了造仙运动从兴起到兴盛的阶段,也就是先秦到魏晋时期,去看仙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它又怎么成了传承至今的文化基因?
这个问题当然很复杂。在书里,作者为我们总结了仙文化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和两条主要线索。这个关键因素,作者叫它“仙文化总集”,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把先秦到魏晋有关神仙的故事、诗歌、修炼技术等等资料放到一起,看作一个知识集合。仙文化形成的第一线索,就是仙文化总集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过程,很像是一场故事接龙大赛。先秦的时候,有人想出了“仙”这个设定。后来的人根据这个设定,编故事、写诗歌、记录相关的逸闻趣事,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到了魏晋,已经积累下丰富的素材。仙文化形成的第二条线索,是人们如何利用仙文化总集。作者认为,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么多修仙的传说,说明修仙者没有完全脱离社会。修仙者是把仙文化总集当成了剧本,根据剧本在大众面前“表演”修仙,这种表演,能让他们获得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名声,这是修仙者参与世俗社会的独特方式。
弄清楚这两条线索,我们不仅会对仙文化有更深的理解,也能从中体会文化形成的一些普遍规律。下面,我就按照这两条线索,来讲讲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平常我们说话的时候,会把“神”和“仙”连用,听起来,神和仙的意思好像也差不太多。确实,在佛教、道教盛行之后,仙、神、佛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比如孙悟空,他能长生、会变化,也算是个神仙,而《西游记》就是他成神不得,又成佛的故事。
不过,细究起来,神和仙基本的意思其实很不一样。从蒙昧时期的原始思维,到后来出现的宗教,人类创造了各种神,比如宙斯、上帝、妈祖等等。这些神,是把自然的神秘力量人格化了,是人类膜拜的对象。而仙呢?任何普通人,只要学到一些秘传的心法,或者碰到什么神奇的机缘,都可以成仙。就像古代小说里说的: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
一个凡人,怎么成仙呢?今天的仙侠故事里,我们能看到各种奇妙的演绎,那最初的设定是什么样的呢?你可能想象不到,在仙文化刚形成的时候,成仙的关键因素,是吃。
我们就来看看战国时的人是怎么说的。《楚辞·远游》里说,诗人在一位仙人的指导下,开始修仙。他首先要做的是不吃饭,也就是辟谷。辟谷最直接的效果,大概是减肥,在古人眼中,肥肉是升天的阻碍。不过,辟谷并不是简单的绝食,而是一项复杂的技术活。辟谷不是什么都不能吃,只是不能吃凡人的食物。但是,修仙的人也需要营养啊,怎么办呢?《远游》里接着说:诗人要学会把天地灵气当作食物,把“气”转化成生命能量,也就是古人说的“精”。整个过程,相当于对身体做了一次提纯。这样,人就可以超越肉体的束缚,把“神”解放出来。
战国的时候,虽然还没有“仙”这个概念,但成仙的基本逻辑已经出现了。到了汉代,这套逻辑就不再只是诗人的想象,而成了修仙的方法论,还有了相关的指南。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却谷食气篇》,就是这样一本指南。里面提到,在不同的季节,不同年龄的人,食气的方法也不一样,而且,想要成仙,还得学会避开有害的气。当时的人真的会用这种方法来修炼,《史记》里就提到,西汉的开国功臣张良,到了晚年宣布自己要修仙,方法就是辟谷。
在辟谷的基础上,古人又逐渐完善了修仙的方法。比如说,除了食气之外,也可以吃点别的东西。像千年灵芝、万年雪莲这些东西,就在人们的想象中应运而生。东晋的葛洪,是当时神仙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更加严谨,把天下的药分成了三等:下等的草木,只能让人吃饱;中等的矿物,最多让人延年益寿;只有上等的黄金白银玉石等等,吃了才能成仙。你想想,这些东西吃进去,人就算侥幸没死,也会得胃穿孔,所以必须解决怎么吃的问题。解决方案,就是炼丹。葛洪也是历史上著名的炼丹专家。
炼出来的仙丹,主要成分是硫化汞,吃了还是会死人。葛洪的《神仙传》里有个故事,说一个叫魏伯阳的人带领徒弟烧制仙丹。烧成之后,大家都不敢吃。魏伯阳就说:先喂狗吧。狗吃了后,不幸死了。魏伯阳不甘心,炼了这么久的仙丹,死了也要吃。他吃了之后,当场也死了。现在来看,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很可能是真的,不过,作者还是给它补上了一个喜剧的结局:魏伯阳复活了,然后把仙丹分给弟子和狗,大家一起成仙去了。这样写,大概是为了鼓励后人,在成仙的道路上不要害怕死亡的考验。
说到这儿,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不管是辟谷,还是服食仙丹,修仙这件事,跟吃有扯不清的关系。没错,作者考察了大量文献之后发现,在古人的观念里,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确实是成仙路上的关键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部神仙故事集《列仙传》里的一个故事。汉成帝的时候,一位猎人在终南山看到一个野人。这个野人没穿衣服,浑身黑毛,奔跑如飞,逾坑越谷,如履平地。后来,猎人们终于抓住了她。野人说:自己本来是秦国的宫女。秦朝灭亡,皇宫被烧,她逃到山里,差点饿死。幸好,一位老翁教她吃松叶松果。她发现,吃了这些不仅能填饱肚子,还有神奇的效果,冬不怕冷,夏不怕热,整个人焕然一新。猎人们大发善心,把野人接回了人类社会,给她吃粮食。一开始,她觉得很恶心,不过也慢慢接受了。过了两年,她身上的毛发脱落,开始变老,不久就死掉了。从秦末到汉成帝时期,这个宫女差不多活了两百岁,所以讲故事的人感慨道:假如猎人没有抓住她,没准,她就能成仙了。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不吃谷物,对成仙来说至关重要。这个标准,听起来有点滑稽,但背后其实有很严肃的理由。你想想,仙的基本定义,就是凡人的升级版,有点像今天的超级英雄。他们首先是人,但又超越了凡人。所以,仙的形象和成仙的方法,核心也就一条,就是跟凡人不一样。
食用谷物,正是凡人的一个重要特点。民以食为天,吃本来就是生而为人的首要大事。在文明诞生之初,食用谷物又是华夏文明特有的习惯。考古学家张光直甚至说:在上古时期,食用谷物是区分华夏和蛮夷的一条重要界限。再有,古代君王的统治范围叫江山社稷。这里的稷是一种粮食,而且是百谷之长,被封为谷神。从这个词就能看出来,在古人眼中,谷物也象征着国家权力。
你看,谷物既能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又是文明和社会秩序的象征。想要塑造“仙”这个不同于凡人的形象,谷物的这些象征意义,正好可以利用。用作者的话说,为什么成仙不能吃谷物,古人根本说不出什么像样的道理,他们特别强调这一点,仅仅是因为食用谷物是凡人的特征,而否定食用谷物,就等于否定凡人的习惯、凡人的文明和凡人的社会秩序。
否定,正是文化生成的一种策略。我在《侘寂》那本书的解读里就提到过,唐代的时候,日本人吸收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却能从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就是因为他们用了这一招。这个道理,上升到哲学层面,可以用庄子的“非彼无我”来解释,简单来说就是,想要有独特性,一定要有对照物。凡人皆有一死,仙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不死。孙悟空修行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从阎罗王的生死簿上,划掉自己的名字。凡人皆会老去,仙一般不会变老,甚至能返老还童。仙还会有凡人不具备的神奇能力,像变形、隐身、发光、预测、控制动物等等。有的仙还有一些跟凡人不一样的外形特征,比如方形的瞳孔,没有影子什么的。另外,凡人离开世俗社会很难生存,但仙一定要住在远离人群的深山洞穴,或者干脆四处云游,居无定所。仙的这些特点,有的像神,有的像鬼,有的像动物,有的像灵媒,总之,就是跟凡人不一样。
从先秦到魏晋,在想象的世界里,仙的形象依据“不同于凡人”这条标准,逐渐形成。各种奇思妙想,通过诸子散文、游仙诗歌、志怪笔记等等形式流传下来。如今回头去看,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一场故事接龙游戏。一开始,有人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仙人,超脱生与死,云游四海间。这个情境,就是故事的基本设定。然后,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游戏里,不断丰富这个故事,最终完成了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个“仙文化总集”。
“文化总集”是书里一个很重要概念,它的意思是说,一种文化生成,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文献累积。不同时代的人共同参与原创、改写、删减、加工、拓展、重建、分类、汇总等等工作。这就是我说的故事接龙游戏。比如说,仙在做什么?怎么成为仙?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成了升仙和游仙,这两个典型的故事模版。前面提到的魏伯阳的故事,就是一个升仙故事;游仙的故事你肯定也很熟悉了,《红楼梦》里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就是化用了游仙的故事模型。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像葛洪这样相信神仙之说的人,会整理神仙故事还比较好理解,但是像曹植那样显然不信仙的人,为什么也要加入这场故事接龙呢?
我觉得,这背后的理由,其实我们都能体会。生而为人的局限,让我们产生了拔地飞仙的愿望,渴望逃离世俗,追求精神自由。那些我们想逃而逃不掉的难题,到了仙的世界,都不再是难题;那些我们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也都可以在仙的世界里,借由想象来实现。
第一部分我们说了,从先秦到魏晋,中国出现了独特的仙文化。到今天,仙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不仅融入日常语言,也融入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一对夫妻感情特别好,我们会说他们是“神仙眷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只是一个升仙故事,也可以指官场潜规则。如果仙文化总集,只是少数人参与的一场故事接龙,很难想象它能有对整个中国文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那仙这个元素,到底是怎么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的呢?
这就要说到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了。作者认为,仙文化总集形成之后,对修仙的人来说,里面不仅有修炼的方法,也有现成的人物、情景、故事模型和修辞手法,就像是一个修仙剧本。按照这个剧本行动,就算不能真的成仙,修仙者也能通过“表演”修仙,吸引追随者,获得名声。仙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修仙者的表演。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说这个问题。
在这本书的开始,作者讲了一个成仙的故事。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叫灵寿光。他得到了一个炼丹的方子,合成了丹药,吃了以后,长生不老,活了二百二十岁。后来,他在一个叫胡冈的人的家里去世了。过了一百多天,另一个人居然在其他地方见到了灵寿光,就写了封信告诉胡冈。胡冈听说之后,赶紧挖出灵寿光的棺材,结果发现,虽然棺材的钉子没有脱落,但里面的尸体已经不见了。
这是个典型的成仙故事,里面提到了两种常见的成仙方法:一个是丹药,一个叫尸解。大部分研究者看这个故事,关注点也在这些地方。但是,读完这个故事,你会不会还有点好奇,记录这个故事的人,为什么不直接说灵寿光吃了丹药长生不老,又通过尸解飞升成仙,非要绕弯子,一会儿说胡冈,一会儿又说写信呢?
仔细体会一下就感觉到,这是一种叙事策略。有了这个策略,灵寿光成仙的故事,就显得更可信了。灵寿光死在胡冈家,说明在那之前,他跟胡冈肯定有往来。作者就说,很多修仙者从正常的社会角色中退出,但他们并不是从此生活在真空中。至少有一些修仙者像灵寿光这样,依然跟世俗社会里的人保持往来。他们的语言、风格、外表和行为,会吸引像胡冈这样的人。这些人期待灵寿光成仙,其实就是期待他按照仙文化总集中的剧本完成表演。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这种期待,灵寿光才能完成这场修仙表演,因为确认灵寿光成仙,必须有胡冈做见证。所以作者说,修仙不是一个人的修行,而是一种社会化的表演,它需要观众的认可。
观众为什么要配合修仙者完成表演呢?答案是神秘感。修仙者一般会宣称自己拥有罕见的秘术,或者见过神奇的仙界,但又不把它们完全展示出来,这种神秘感,能吸引大量的关注。正所谓愈隐则愈显,只有别人知道你拥有一个秘密的时候,秘密才有价值。修仙者塑造神秘感的方法,来自仙文化总集。他们讲的故事,有两种典型模式。第一种是修仙者遇到仙人,传授他神秘的方法,让他获得长生;第二种,是修仙者说自己去过仙界,然后向人们描述那里的奇观。这两种套路,不就是第一部分提到的,升仙和游仙这两种故事模型吗?
那么,修仙者完成这场表演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当然没办法知道每个人具体的目的,但是从效果来看,他们获得了名声,名声是一种很有用的社会资源,能带来影响力。在作者看来,这就是修仙的社会意义。
不过,名声的传播,古人不会记载。这就像做营销分析,只能看到广告文案,却看不到传播数据,很难分析清楚。幸运的是,作者发现葛洪记录的一个故事,展现了当时修仙者获得名声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故事。
故事的主角叫李宽,讲一口四川话,大概是四川人。据说他会法术,也能治病。李宽来到江南地区,治好了很多人,一下子出名了。因为有四川口音,当地人觉得,他肯定就是四川某个已经很出名的神仙,那个神仙也姓李。葛洪讲完这些之后,淡淡地说了一句:实际上当然不是了。这句话很值得玩味,他是在暗示,会法术、能治病,都是仙文化总集里提到的仙的特点,符合一般人对仙的期待。李宽的行为满足了人们的期待,人们就对号入座,把他奉为神仙。
出名之后,无数人来拜访李宽,他却娇贵起来,不肯轻易见客。李宽也收了一些弟子,不过只教了符咒、导引术之类简单的东西。葛洪还说,他认识一些见过李宽的人,都说李宽年纪大了,衰老得很快,眼瞎耳聋,齿堕发白,跟凡人没什么区别。显然,葛洪是想证明李宽不是神仙,因为根据仙文化总集的标准,神仙不应该衰老。这样看的话,李宽不轻易见客,既是为了塑造神秘感,也可能是怕自己变老,被人发现。不过,当地人依然相信李宽,他们还为他找理由,说李宽变老是故意假装自己跟普通人差不多。后来,当地爆发了一场大瘟疫,死了很多人。李宽也染上了,他没能治好自己。而他的弟子依然坚持这个神话,说李宽最后尸解成仙了。
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我们来思考一下,老百姓说李宽是故意变老,弟子说李宽尸解成仙,是因为他们愚昧迷信吗?这样的解释显然太简单了。名声需要社会网络才能存在,反过来说,社会网络也需要名声来维系。所以“李宽是神仙”这个名声,不仅对李宽来说很重要,对他的弟子和追随者来说也同样重要。
像李宽、灵寿光这样的修仙者,除了会招收弟子,一般还有赞助人。根据作者推断,胡冈应该就是灵寿光的赞助人。赞助人为修仙者提供住所、资助和服务,他们不一定像弟子那样想学习修炼方法,也可能只是为了寻求庇护。有的故事里提到,赞助人供奉修仙者,是希望自己也能沾光,跟随修仙者一道飞升成仙。这样看的话,人们维护修仙者的名声,就不完全是因为愚昧,也可能是要实现自己的目的。
那些成功塑造名声的修仙者,会成为仙传故事的主人公,一般会有三种结局:一种是有人看到修仙者飞举空中,成为仙人;第二种是修仙者离开,说自己要去山里;第三种是人们在另外一些地方,看到了尸解之后的修仙者,就像灵寿光的故事一样。在那之后,人们会建立祠堂或者庙宇,来纪念修仙者,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获得庇护,获得精神能量。
围绕名声,修仙者、弟子、赞助人和其他相关的人,形成了一个社群,哪怕修仙者不在了,这个社群也不会因此中断。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是围绕宗法制度形成的差序格局,所有人都应该在这个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修仙的社群,相当于在主流社会之外,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李宽的故事里就提到了一个细节,李宽的弟子,很多都是当时不受管制的流动人口,他们通过这个社群,在社会网络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在这个意义上说,修仙者没有脱离社会,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
说到这里,你应该理解了修仙的社会意义。对修仙者来说,仙文化总集就像一个现成的剧本,为他们把自己打造成神仙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技术指南、公关策略、成功个案等等,也为他们在大众心中打好了信任的基础。成功的修仙者能用好这个剧本打造仙的形象,获得名声。围绕名声,修仙者、弟子、赞助人以及其他相关的人,结成了新的社群,参与到社会生活中。这就是仙文化广泛传播,并且传承至今的现实基础。
归根到底,我们的文化接受仙这个元素,并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出于现实的诉求。
这本《修仙》,我就讲到这里。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元素,是古代中国人探索宇宙和人生奥妙的独特创造。从两千多年前,直到今天,中国人一直向往神仙。神仙永远年轻不死,能实现凡人可望而不可得的愿望,还能永远享受现世的快乐。
作者康儒博认为,仙是不是真的,古人信不信仙,我们其实没必要纠结这类问题。仙文化流传至今,是因为它在古代社会中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仙的世界,并不是某些人虚妄的追求,而是天下人心共同创造的精神乐园。
最后,我还想跟你分享一点我个人的感受。古人构建仙的世界,终究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一旦我们开始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就会遇到死结。你可以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在有生之年,尽情欢乐;你也可以说“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让自己投身到更大的意义中;你当然也可以“俯观五岳间,人生如寄居”,让精神暂时摆脱肉身的束缚,跳出三界外,享受更大的自由。
撰稿、转述:刘玄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划重点
-
生而为人的局限,让我们产生了拔地飞仙的愿望,渴望逃离世俗,追求精神自由。那些我们想逃而逃不掉的难题,到了仙的世界,都不再是难题;那些我们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也都可以在仙的世界里,借由想象来实现。
-
古人构建仙的世界,终究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