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婚姻》 朱步冲解读
《五四婚姻》| 朱步冲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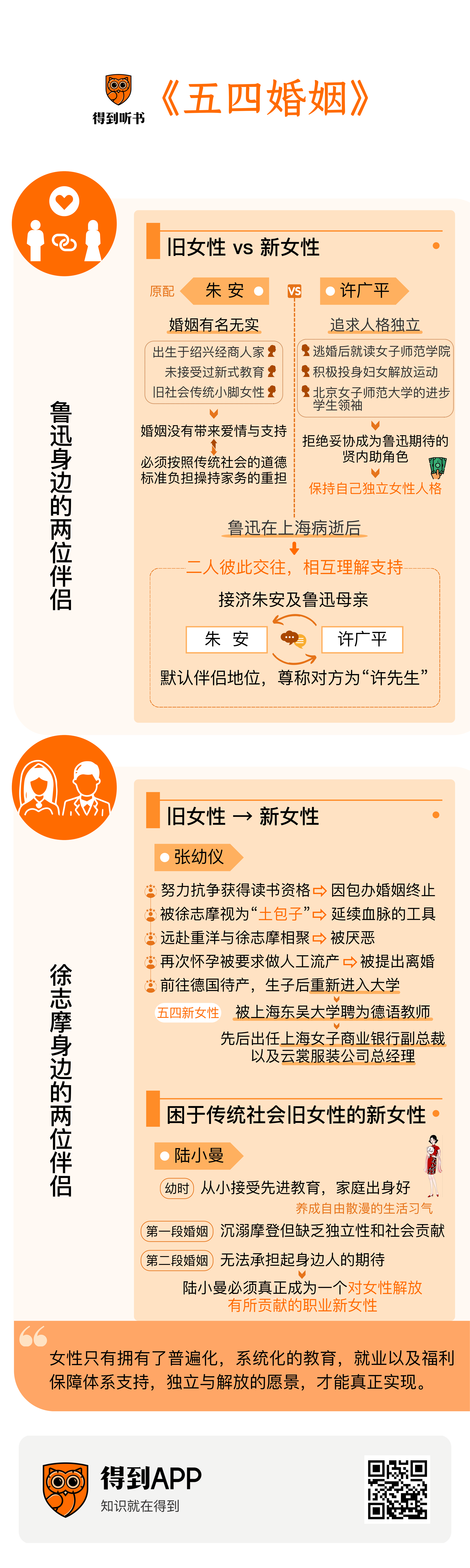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解读的书,是中国香港地区作家、翻译家孔慧怡的《五四婚姻》。
本书的主角,是七位大家耳熟能详的民国时期女性名人,包括许广平、张幼仪、陆小曼、林徽因等等。她们都是民国初年,接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努力追求独立的“新女性”代表。而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她们为主角,通过她们的婚姻与感情纠葛,来探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女性追求解放的艰辛与不易。
中国女性追求独立和解放的运动,在五四期间达到一个全新的高潮,但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一部分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中国文化中的落后部分。这些落后部分,既包括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水平,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古旧的道德习俗,比如女性被桎梏、束缚的状况。
和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革命一样,近代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最先从一些技术细节问题开始。 “办女学”和“放缠足”,是清末妇女解放运动最初的两大主题,目的分别是提高女性的知识水平,强健女性的身体,让她们能够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现状。
当然,作者孔慧怡批评说,这种考虑,比起传统社会,固然是一种进步,但还是对女性自身的诉求、利益和地位提升,有所忽视。她认为,以梁启超、康有为为代表的知识界改良派,他们的目的是培养出身体更强健,劳动与服务技能更强的“贤妻良母”,并没有打算让妇女成为和男性平等的性别。
进入二十世纪后,近现代的中国青年,能够远涉重洋,直接目睹,甚至参与当时在欧美的平权运动,在回国后,他们就成了各类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先行者。比如,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胡适,在前往美国留学前,也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保证她们成为贤妻良母,但到了美国之后,顿时感到了自身思想的狭隘与陈旧,于是大声疾呼,为了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就应该“造就一种能独立自由的女子”。
于是,自民国初年起,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核心变成了追求女性自身的“自由与独立”,希望能制造出一种与传统社会截然相反,拥有独立人格,与男性平等,掌控自己生活的“新女性”。 到了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更为现代中国女性的解放运动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动员。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敬告青年》,希望青年一代中的女性,成为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女性,而这种新女性有两个标准,分别是“脱离夫权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由自主之人格”。而李大钊,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妇女解放运动,对“自由的发展,民权的伸张,专制桎梏的打破”,是极大的助力,“没有女性解放的新社会”,不是完整的新社会。
这种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就是本书故事发生的大背景。在五四运动中,青年们的核心诉求,不仅在于改革当时北洋政府的腐朽统治,更在于实现个体的自由发展,而“婚姻感情的自主”,就是个人自由的核心。在本书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民国新女性的抗争,几乎都是始于追求婚恋自由,希望掌控自己的感情生活。然而,她们随后又纷纷意识到,婚姻感情的自由,也需要有一大堆条件作为后盾;总之,如果女性不能拥有经济上的独立,和适当的社会地位,那么感情自主,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势在必行。作者孔慧怡说,在本书中出场的这七位民国初年的女性名人,即使她们拥有诸多优越条件,但在追求人格独立的抗争中,依旧遭遇了重重阻力,有的与社会现实妥协,有的则咽下了失败的苦果。
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们将会看到,所谓新女性,与旧女性的分界线,并非泾渭分明。例如今天被捧为“民国传奇名媛”的张幼仪,正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家庭的支持,抓住了宝贵的机会,能够脱离传统社会与家庭的桎梏,成为经济、社会人格同时独立的“新女性”。然而遗憾的是,张幼仪的成功,对于民国初年绝大多数渴望解放的女性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才能借助新社会的系统性改造和进步,实现自身独立、平等的梦想。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详细介绍本书的大致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近代文学的奠基人、革命家与思想家鲁迅身边的两位伴侣的故事:一个是身为“旧女性”代表的朱安,一个是身为“新女性”的许广平。而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再来了解下,两位截然不同的“新女性”代表:张幼仪与陆小曼。一个如何在婚姻破裂后,努力从“旧女性”变成了“新女性”的楷模,而另一个,为什么空有“新女性”的光环,却无法走出传统社会旧女性的天地。
首先,我们来看看鲁迅先生的原配,朱安女士。当我们谈到鲁迅的伴侣时,大家关注的重点,往往是身为“新女性”和鲁迅战友的许广平,而不是这位长期被忽略的“旧女性”。光绪四年,也就是1878年,朱安出生于绍兴一个经商人家。朱家的家境还不错,有一座大宅,里面包括两栋大屋,每栋附带三进院落。不过,直到1899年,朱安21岁的时候,才开始谈婚论嫁,本着门当户对的原则,朱家选中的姻亲对象,是同在绍兴的周家。周家虽然家道中落,经济拮据,但好歹还是绍兴本地的官宦世家,而朱安未来的丈夫,就是周老爷,周福清的长孙,本名周树人的鲁迅。
本来,1901年冬天,就是举行婚礼的好日子,但鲁迅当时考中了去日本的留学资格,这一去,就是7年,而且,鲁迅在赴日留学后不久,就写来一封信,要求朱安进学堂读书,接受新式教育,同时还要放脚,也就是把缠好的小脚松开。
对于这种要求,因循守旧的朱家虽然震惊,但也只能默默接受。1906年7月,这段推迟了许久的婚礼终于在绍兴举办:鲁迅是被一封母亲得了急病的假电报哄骗回来的,对此他在余生中始终耿耿于怀。不过,对于朱安来说,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有名无实;虽然她为了讨好丈夫的新派思想,穿了一双正常尺码的绣鞋,里面塞满了棉花,仿佛已经放弃了缠足,但鲁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感情,婚礼三天后,就匆忙返回了日本。
朱安无法享受婚姻带来的爱情与支持,但却必须按照传统社会的道德标准,替鲁迅负担起操持家务的重担。周家当时已经败落,唯一的固定收入来自佃户租种自家土地的租金,所以如何用这些微薄的收入,支撑一个家庭的日常开支,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幸亏朱安性格柔顺勤勉,和婆婆一起操持家务,相处融洽之余,还能让周家的生活得以维持下去。
1910年,鲁迅终于学成回国,先是担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然后被蔡元培推荐,在教育部谋了一份差事。于是,他独自北上,迁居首都。两地分居的生活,让朱安更加无法进入鲁迅的感情世界与内心,朱安曾经鼓足勇气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建议他纳妾,好生下一男半女,延续家族的香火,但这种好意,鲁迅也拒绝领受,他回信痛斥妻子,说这种想法简直是荒谬。
终于,在1919年,朱安和自己的婆婆,一同来到北京。不过,这种全新的生活,让朱安的孤单和不适感更加剧烈。此时,鲁迅已经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从而声名鹊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每天,前往鲁迅家中拜会的文化名人络绎不绝,虽然他们在表面上都对朱安客客气气,但朱安心里明白,自己在这个家里只不过是个外人。
终于,到了1925年,朱安感觉到,自己丈夫的心中,另有他人,而这个涉足自己婚姻的外来者,就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进步学生领袖许广平。 这个打击对于朱安来说是决定性的,她曾经说:在这段婚姻中,自己仿佛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但现在自己没有办法了,没有力气爬了,因为她感觉到,自己对鲁迅再好,也是没有用的。
许广平的人生轨迹,与朱安截然相反,她的大哥许崇禧留学日本,思想开明。许广平在大哥的影响下,不但早早开始阅读《妇女报》等宣传女性解放的进步刊物,更是在家人的支持下,毅然逃婚,只身来到天津,就读女子师范学院。在这里,许广平积极投身妇女解放运动,并最终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挪威著名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与他的名作《玩偶之家》被引进国内。剧中的女主角娜拉,最终决定告别沉闷而庸俗的婚姻生活,毅然离家出走。这一设定,让当时渴望自由的中国青年,立刻把娜拉当成了精神偶像与寄托,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五四时期的文艺创作。 1923年,鲁迅给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做了一场讲座,名为“娜拉出走后会怎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离开婚姻关系,只是女性和旧社会秩序决裂,寻求独立的第一步,更艰巨的工作还在后头,毕竟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保障女性的基本生活,与人格独立;否则,那些轻率出走的中国娜拉,只有两条路,要么是为了生计而堕落,要么就是回归曾经背离的家庭。
说到这里,作者孔慧怡评论说,此时的许广平,应该为讲台上鲁迅的风采所倾倒,和其他自比娜拉的进步女性一样,她似乎看到了一条全新的出路:那就是,娜拉遇到了一位思想进步,献身于女性解放的文坛斗士,这既是一位理想的爱人,也是一位卓越的精神导师。他们之间如果能够结合,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激动和幸福的事情。
鲁迅和许广平的交往,以通信开始,随后,许广平和她北师大的女同学,就成为鲁迅家里的常客。很快,革命的风潮来临了,北师大的进步女学生,发起了驱逐守旧派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身为这场学生运动核心的许广平,被校方称为害群之马。最终,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在这场风暴中变得越来越紧密:因为支持北师大学生,鲁迅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了教育部的职务。为了远离迫害,鲁迅先是前往厦门大学任教,随后于1927年定居上海。在这一趟从北到南的颠沛流离中,无论是妻子朱安,还是母亲,都没有和鲁迅同行,陪伴在鲁迅身边的,正是许广平;在此之前,倔强的许广平已经“主动出击”,撰写了两篇文章,向鲁迅示爱,其中就有这样大胆直白的句子:
“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
生性孤傲的鲁迅,也无法抵挡这样的攻势。于是,鲁迅抵达上海之后,终于和许广平正式奠定了关系,两人开始同居。然而,在获得了渴望的稳定关系后,许广平却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娜拉式的困境,发现自己和之前追求的事业独立,渐行渐远:在广东女子师范和中山大学期间,许广平还能担任教职,但到了上海之后,鲁迅期待她扮演的角色,就是贤内助。
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就是,像许广平这样的新派知识女性,刚入职场,薪水非常低微;而鲁迅,则因为名声越来越大,可以依靠优渥的稿费,毫不费力地同时负担两个人的生活。这样一看,似乎鲁迅当年讲演的内容,一步步地变成了现实,那就是娜拉出走之后,要么再次回归家庭,要么只能堕落。
一个始终站在五四运动风口浪尖上,为女性独立解放奔走的新知识女性,最终发现,自己通过自由恋爱获得的感情,居然导致自己,依旧要回归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角色。这个结局,在今天看来,依旧让人唏嘘。那么,回归家庭后的许广平,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旁观者的记载是:她既是妻子、母亲,又是秘书、保姆;每天有大量的家务活,一日三餐,里里外外……客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她一边谈着,一边手里织着毛衣,客人留下吃饭,她就得临时上街买菜,下厨。鲁迅临时要寄一封信,她就换上皮鞋,跑到邮局去。
这样的生活,肯定不是许广平所希望的,她曾经写过一篇杂文,叫《像捣乱,不是学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为了寻求活着的学问,向社会战斗的学问,去请教鲁迅先生,然而后来却消磨在家庭和小孩的繁琐上。一个女人,如果这两方面没有合理的解决,是没法放开脚走一步的。这苦恼的情形,不是男人所能了解。
当然,极度追求人格独立的许广平,依旧没有完全妥协。作者孔慧怡在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在和鲁迅一起生活后,许广平始终在身边放着一笔三百元的存款,并公开告诉鲁迅和两人共同的朋友,如果关系破裂,这笔积蓄将是自己暂时维持生计的保障,同时它也是许广平保持自己独立女性人格的具体象征。 尽管如此,研究鲁迅生平与思想创作的传统学者,往往将许广平简单归结成鲁迅的“贤内助”,很难看到许广平放弃职业生涯的这层退让,忽视了二人关系中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这是今天的我们,必须加以反思和重视的。
1936年,鲁迅在上海病逝。出乎意料的是,这反而成了朱安和许广平彼此交往,相互理解支持的契机:许广平毅然承担起了接济朱安和鲁迅母亲的义务;而朱安,也默认了许广平作为鲁迅伴侣的地位,两人开始通信;当然,由于目不识丁,朱安的信件,是由她口授,别人代笔的。在信中,朱安始终尊称许广平为“许先生”,而许广平,也让自己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管朱安叫“姆妈”。朱安晚年接受记者访问,当记者问到她如何看待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时,恪守旧道德、性情温和隐忍的朱安是这样回答的: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之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对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说完了鲁迅、朱安与许广平的故事,接下来我要为你讲述的,同样是两位被五四运动提倡的女性解放运动深深吸引,努力想活出独立人生的知名女性。同样,她们也因为命运的安排,与一个才华横溢的民国文坛才子纠葛在一起,产生了错综复杂的感情关系。她们,就是张幼仪和陆小曼,而在她们生命中曾经同时占据过重要地位的男人,就是著名诗人徐志摩。
如果简单粗暴地用鲁迅的故事来类比,那么张幼仪的角色类似朱安,而陆小曼接近许广平。
张幼仪和徐志摩的离婚,是民国初年的“重量级新闻”,甚至被称为“中国第一宗现代离婚事件”。然而,对这件社会公案的记载,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学研究界,都先入为主地,以徐志摩一方提供的资料证言为准,这就导致,真相长期被遮蔽在历史的迷雾之后。
1900年,张幼仪出身于上海宝山县一个富裕家庭,父母育有八男四女,二哥张君劢是日后的法律与政界要人,被称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不过,虽然张家家境不错,重视后代的教育,但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并不支持张幼仪和姐姐接受现代西式教育。实际上,张幼仪最终能到学校读书,完全是依靠她自己的努力和抗争:12岁那年,她在报纸上看到了苏州预备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就联合姐姐,向父母发起软磨硬泡,最终才如愿以偿。
然而仅仅三年后,张幼仪的学业就因一桩包办婚姻,戛然而止。替她做媒的,正是她的四哥张嘉璈,时任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在巡视学校时,他发现杭州一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学生,日后的民国风流才子徐志摩。徐家当时已是江南富商,这桩婚事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于是双方父母一拍即合。但可以肯定的是,婚姻中的当事人,无论是张幼仪还是徐志摩,对此都是极为不满的。
在经过后世重重篡改、删除和隐瞒后,徐志摩和张幼仪的离婚,变成了一件男女双方平等自愿,友好和平分手的“佳话”,但实际情况是如何的呢?
从结婚第一天开始,徐志摩就把张幼仪视为“土包子”,对她不理不睬,仅仅把婚姻看作是完成父母抱孙心切,延续血脉的工具,张幼仪于18岁生下儿子徐积楷后,徐志摩立刻前往美国留学,并借此逃离这段毫无感情的婚姻。2年后,徐志摩放弃了在美国的学业,转而前往英国求学,徐家父母这才感觉儿子有些放飞自我,这才决定把张幼仪送到英国与徐志摩团聚,试图让徐志摩能够回归家庭。
然而,看到远涉重洋而来的妻子,徐志摩表现出的只有厌恶,因为他此刻正在全力追求才女林徽因;而张幼仪也逐渐感觉到,自己丈夫的心里,另有他人。在张幼仪口授,侄孙女张邦梅撰写的回忆录《小脚与西服》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徐志摩带着张幼仪搭乘公车,一起去南安普顿,在车上,徐志摩神情紧张,一面指着坐在后面的张幼仪,一面打手势给身边的朋友,让他少说话。敏感的张幼仪自然意识到,丈夫有什么事情在隐瞒自己。
当时,两人移居到了剑桥大学附近的小镇沙士顿,徐志摩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做旁听生,而张幼仪生活中的主轴,就变成照顾丈夫饮食起居。对此,她非常失落,因为在自己的设想中,自己应该能接触更为广阔的世界,同时继续自己的学业。1921年夏天,张幼仪再次怀孕,而徐志摩的反应,却是冷冰冰地让妻子去做人工流产。《小脚与西服》一书中,记载了夫妻两人关于此事的对话,直到今天,徐志摩表现出的冷酷与绝情,依旧会让人义愤填膺:
听到丈夫让自己流产,张幼仪立刻发出了抗议,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徐志摩的回答是:“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了呢!难道你看到人家就不坐火车了吗!”
到了九月初,徐志摩正式向张幼仪提出了离婚。根据记载,懦弱的徐志摩甚至不敢和妻子面谈此事,而是委托了一位朋友通知张幼仪。在这通敷衍的照会发生后一周,徐志摩就从家里不辞而别,抛下了怀着三个月身孕的妻子。
作者孔慧怡说,徐志摩这种举动,在五四运动这个新思想与新文化狂飙突进的年代里,并不少见。对于许多当时在文化知识界崭露头角的男性名人来说,家庭安排的旧式婚姻,是传统封建社会对青年一代最明显的迫害,所以“逃婚”从道义上说就有了正当性:叫冲破樊笼,追求自由;当然,这样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让自己能够抛弃缺乏文化修养和共同语言的原配妻子,转而寻求自己中意的“新式女性”作为伴侣。
所幸的是,在这个时刻,张幼仪的兄弟张嘉森和张景秋都在德国留学,张幼仪得以前往德国待产。同时,徐家出于愧疚,每月固定寄来两百美元,作为生活费。多亏这些支持,张幼仪能够在生下儿子徐德生之后,重新走进了大学这座知识的殿堂。由于天生聪慧,学习刻苦,张幼仪在回国后,就被上海东吴大学聘为德语教师。而这,才是张幼仪正式成为“五四新女性”迈出的第一步。用她自己的话说“在去德国之前,我什么都怕;在到了德国之后,我无所畏惧”。
接下来,张幼仪的人生事迹,对民国女性历史轶闻有兴趣的人,就都比较了解了:她先后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以及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凭借着出色的工作能力,优雅的品位和留学欧洲的履历,一举从丈夫徐志摩口中的土包子,变成了民国新女性的典范。
说完了起点低,但励志上进的张幼仪,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更为熟悉,同样作为民国新女性,以及名媛的陆小曼。
和张幼仪相反,陆小曼从一开始,就顺风顺水地拥有了“新女性”的身份和各种自由。父亲陆定是前清举人,但思想解放开通,曾经留学日本,陆小曼的童年,上的是上海的西式幼儿园,到了北京,又就读北京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以及法国教会开办的圣心书院,熟练地掌握英法两门外语;到了十多岁时,如此优异的教育背景、家庭出身,再加上出色的容貌与气质,让陆小曼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社交场合的焦点。
1920年,陆小曼走入了人生中第一段婚姻,丈夫是民国陆军界知名的青年才俊王赓。王赓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是同学,回国后就进入北洋政府陆军部,前程似锦。不过,婚后的陆小曼,如同很多同时代人批评的那样,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新女性,因为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社交、购物、打牌、跳舞。而陆小曼本人,对这种虽然摩登,但实质上缺乏独立性和社会贡献的生活,不仅不排斥,还沉溺其中。
很快,这段婚姻的矛盾迅速出现,王赓忙于公务,无法陪同陆小曼一起在社交场合应酬,而风流浪漫的徐志摩,就对陆小曼展开了排山倒海一样的“情书攻势”。不用说,徐志摩先恶意抛弃原配妻子张幼仪,随后又介入他人家庭,追求自己好友王赓的妻子;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确实是为人不齿,难以洗白。但是,作者孔慧怡说,这种对现存道德习俗的极端反抗,被无数五四时期要求解放的新一代青年,看做是黑夜中的明灯:这种倾向,可以用五四时期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的评论来总结:我就佩服志摩的纯真与小曼的勇敢,假使我马上要死的话,也要做一篇伟大的史诗,来赞颂志摩与小曼。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名人,对两人的结合,也是同情、支持,大于反对。比如张幼仪的兄长,依旧和徐志摩保持着往日的友情和来往;许多民国初年的文化名人,也都参加了两人的婚礼,包括胡适和梁启超。
不过,浪漫带来的激情并不长久。第二段婚姻中的陆小曼,也很难说幸福。根据作者孔慧怡的分析,除了丈夫徐志摩不能专心于二人世界,还有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陆小曼无法承担起身边人的期待,不论是徐志摩,还是身边那些爱慕自己的男性文化名人。这个期待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陆小曼必须真正成为一个对女性解放有所贡献的职业新女性。
众所周知,陆小曼确实天资聪颖,才华横溢;但因为优越的家境,她养成了一种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气:在任何领域,陆小曼都只肯凭着兴趣,游戏玩票,但懒得花苦功夫深入:陆小曼曾和徐志摩联合创作话剧《卞昆冈》,但实际上陆小曼只出故事梗概,细节打磨全是徐志摩完成;同样,陆小曼也曾拜刘海粟为师,学习国画,还作为票友出演过京剧,水平其实不错,但实际上,这些只是她打发时间的消遣而已。
相比之下,徐志摩生命中的另外两位女性,都已经凭借自身的才能,在专业领域崭露头角,真正实现了新女性所推崇的独立:一个,是在古代建筑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林徽因,而另一个,就是在商界声名鹊起的张幼仪。实际上,徐志摩的父母,更偏爱张幼仪,这不仅因为徐家对张幼仪有所亏欠,以及张幼仪是徐家长孙的生母,更是因为张幼仪的独立、干练与可靠。
实际上,徐志摩逝世后,徐家的财产,也全部交给张幼仪来打理,而大度的张幼仪,一直在支付陆小曼的生活费。这一切,都是心高气傲的陆小曼,难以忍受的。
相信读到这里,很多人会和我一样感慨,张幼仪和陆小曼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告诉我们:所谓“新女性”与“旧女性”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自强者如张幼仪,只要给予一线机会,就能够果断抓住,开创属于自己的新生活;而比起张幼仪来,陆小曼则反而被自身优越的出身与天赋所拖累,过着“新瓶装旧酒”的舒适生活;女性独立,只不过是陆小曼享受生活的光环与装点,而她本可以利用自己的天赋和条件,成就更多。
好了,到这里,这本《五四婚姻》的大致内容,就为你介绍完了。在二十世纪最初的二十年里,中国女性追求独立与平等的努力,依靠新文化与五四运动两场狂飙突进的社会运动,达到了一个顶峰;作者孔慧怡,通过讲述朱安、许广平、林徽因、陆小曼等七位著名女性的情感生活,来分析民国初年,“新女性”如何在这两场社会运动中诞生,开始追求个人独立与平等。
不可否认的是,包括孔慧怡在内,许多历史学者都认为,民国初期,追求独立与平等的新女性首先出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虽然,在清末的改革中,各地都开设了不少公立与私立的女性学校,传授来自西方的文化知识,传播女性解放平等思想,但在传统道德影响依旧浓厚的社会氛围下,只有家境相对富裕,且思想开放的人家,才有余力和觉悟,把家庭中的女性下一代送进这样的学堂接受教育,由此,造成了所谓新女性与旧女性的分流。结合本书内容来看,林徽因、陆小曼、许广平等“新女性代表”,正是在传播新派思想与知识的学校中,有了最初的独立觉醒意识。
不过,除了能接受新式教育,民国初年的女性要想实现生活自主,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与个人经济收入,主导自己的婚恋,还需要其他条件与机会的帮衬。通过对七位新女性生平的分析,孔慧怡得出的结论是,当事人还需要家庭中男性亲人的理解和支持,一笔自己能够支配的财富,以及超常的勇气与韧性,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七位女主人公,林徽因、陆小曼和许广平是幸运的,而张幼仪可谓“输在了起跑线上”,当然,她最终凭借自己的坚韧、努力,并没有因此沉沦为因循守旧、消极接受的传统家庭女性;反过来,天资和外在硬件条件最好的陆小曼,反而高开低走,安于当一位安逸舒适的“客厅太太”,以摩登的生活方式,遮盖了自己传统家庭女性的本色。
然而,遗憾的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下,能够幸运地同时拥有这些条件的女性,几乎是凤毛麟角。不要说占据主体的乡村女性,就连城市中的普通市民与小资产阶级出身女性,哪怕是接受了现代教育和女性独立思想的洗礼,也会因为自己稚嫩的理想无法抵抗残酷的社会现实,从而被迫妥协。所以,正如鲁迅等文化思想界先驱所看到的那样,进一步的社会改革与进步,势在必行,女性只有拥有了普遍化、系统化的教育、就业以及福利保障体系支持,独立与解放的愿景,才能真正实现。
另外,本书作者孔慧怡提出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这些民国新女性为了追求独立与自由,非常努力,而她们的伴侣,很多是民国初年声名鹊起的文化名流,却显得自私与凉薄。他们打着“追求感情自由”的旗号,抛弃缺乏文化修养和共同语言的原配妻子,转而寻求自己中意的“新式女性”作为伴侣。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在新旧社会形态与道德标准变动的年代,往往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投机取巧的人,会用新社会主张的权利,逃避旧社会要求自己担负的义务,同时又动用旧社会主张的权利,来逃避新社会的义务;反过来,那些自我道德规范比较高的人,往往会忍辱负重,同时担负起新旧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义务。例如本书所讲的鲁迅原配妻子朱安。不幸的她,沦为了新旧时期伦理道德冲突的牺牲品:既无法享受传统中国旧道德规定的家庭保障,也无法像新时代女性一样走出家门,追求自己的独立。她的一生,都在以旧时代的“隐忍妥协”标准要求自己,又从这方面成就了鲁迅。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样默默牺牲的无辜女性,绝对不应该被漠视,也不能被简单贴上一个“守旧”的标签。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这个音频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新女性”与“旧女性”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
除了能接受新式教育,民国初年的女性要想实现生活自主,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与个人经济收入,主导自己的婚恋,还需要其他条件与机会的帮衬。
-
在历史的长河中,默默牺牲的无辜女性,绝对不应该被漠视,也不能被简单贴上一个“守旧”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