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十三天》 刘怡解读
《九月的十三天》| 刘怡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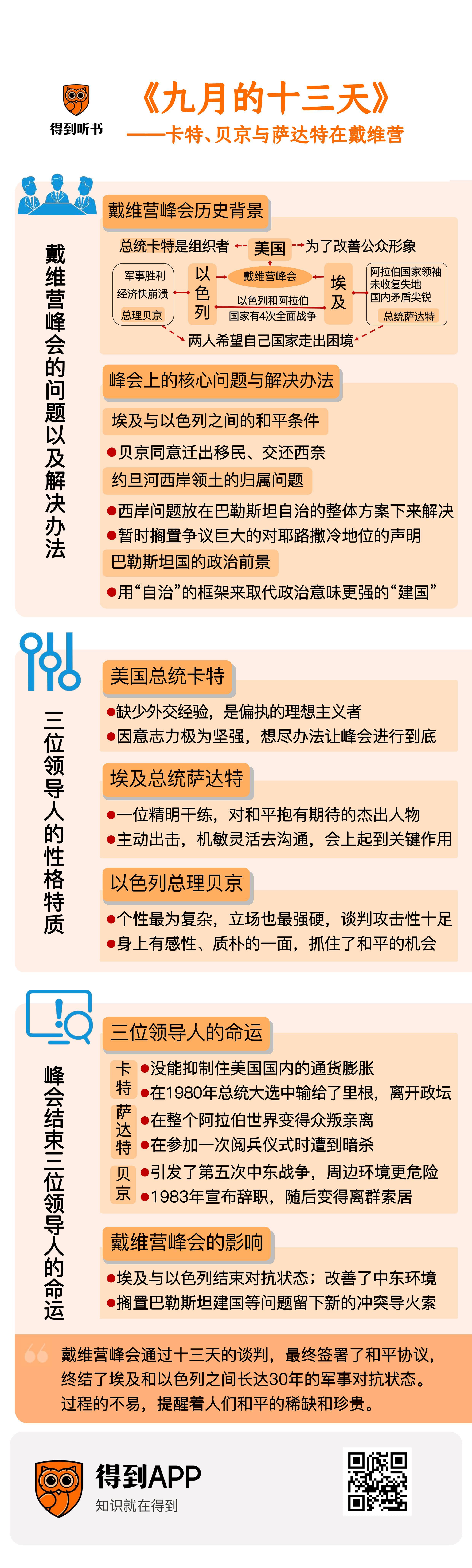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是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奖得主劳伦斯·莱特的《九月的十三天》。
提到“峰会”(Summit)这个词,你一定觉得耳熟能详。不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聚集在某个场合,商讨一些可能会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话题,这种类型的会议被称为“峰会”。一年一度的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以及“冷战”期间美苏领导人不定期的会晤,都属于峰会。如果某次峰会达成的协议还长久地改变了一个地区的政治、外交形势,历史学家就会给它加上一个前缀,称它为“历史性峰会”。“二战”期间的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就属于历史性峰会。
不过,即使已经知道了“峰会”这种外交活动的定义,你对它的详细过程,可能还是有很多疑问。除去正襟危坐式的对话,领导人们会在餐桌上聊些什么呢?他们私下会一起散步,一起看电影吗?如果某次会谈中发生了争吵,要怎样打圆场?大人物的情绪波动,会影响到他在谈判桌上的表现吗?对于这些问题,很少有作品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峰会的保密性质,把新闻记者隔绝在了会场之外,他们能捕捉到的只有一些碎片化的细节。参加峰会的当事人,有一些会在回忆录里复述当年的真实场景,但很少有回忆录会事无巨细地描写某一场单独的峰会。实在有点可惜。
但我今天要讲的这本《九月的十三天》,恰好可以满足你对“峰会”这个问题的全部好奇心。它描写的还是一场相当重要的历史性峰会,那就是1978年9月在美国总统官方度假地戴维营举行的美国、埃及、以色列三国首脑峰会。当时,中东地区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已有5年之久;为了打破坚冰,美国政府出面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这两个宿敌之间的正式谈判。在这次峰会上,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签署了实现中东局部和平的框架性协议,也因此分享了197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戴维营峰会本身的过程,却是跌宕起伏、波折不断的,这给历史学者还原会谈细节增加了巨大的难度。不过,相当巧合的是,邀请作者莱特撰写这本《九月的十三天》的人,就是峰会的第三位主人公——美国前总统卡特。他不仅接受了莱特面对面的采访,还借出了自己在峰会期间撰写的私人日记,并安排作者前往埃及和以色列,拜访当年列席峰会的当事人。 正因为如此,这本花费近三年时间写成的书,既有可信的史料依据,笔法又相当生动传神,可以说忠实再现了一场现代首脑峰会的各个侧面。你也可以在“得到”电子书书库中阅读这本书的完整内容。
本书作者劳伦斯·莱特,是一位兼具资深记者和历史作家双重身份的中东问题专家。他既为《纽约客》杂志撰写过30多年的长篇报道,也是纽约大学法律与安全中心的研究员。莱特在2006年出版的代表作《末日巨塔》,对国际恐怖组织“基地”的崛起历程做了极其详尽的追溯,不仅为他赢得了2007年的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还被改编成美剧播出。而这本《九月的十三天》,是莱特继《末日巨塔》之后,第二部以中东问题为主题的专著,曾入选《纽约时报》2014年度十大好书榜单。它用舞台剧式的笔法,塑造了参加1978年戴维营峰会的三位领导人个性鲜明的形象。如果你希望了解今天阿拉伯-以色列争端的历史渊源,本书会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即使你对中东问题所知不多,它也可以清晰地告诉你:一场典型的当代峰会是怎样进行的,其中有哪些内幕。
接下来,我就分三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它提出的新观点。首先,按照作者莱特的陈述,我来为你梳理一下,哪些问题在这次戴维营峰会上引发了最多的争执,它们又是如何得到解决的。而在第二部分中,我会向你展示,在作者莱特眼里,三位参加峰会的领导人各自有哪些鲜明的性格特质,这些特质又是怎样影响他们在会谈中的表现的。最后,我再为你总结一下,为什么这样一场历史性峰会,给三位参会者的政治生涯带来的影响却是极为负面的,他们的命运又能带给你怎样的思考和启示。
全书一开篇,作者莱特首先交代了1978年9月这场戴维营峰会的历史背景。从1948年到1973年,围绕着以色列建国问题和巴勒斯坦领土的归属,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相继爆发了四场激烈的全面战争。以色列在接连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 而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国家,虽然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挽回了一部分国际声望,但依然没能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也异常尖锐。 可以说,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这两位立场对立的领导人,在启程前往戴维营时,都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都渴望在外交战线上取得重大突破,来帮助自己的国家走出困境。而作为峰会的组织者,美国总统卡特同样面临着国内民众的质疑。在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已经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他只有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取得显著进展,才能改善自己的公众形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峰会也是三位领导人的一次集体“自救”,不容失败。
不过,本书作者莱特也注意到:三位领导人对一些暗藏的陷阱,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误判。美国总统卡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都认为,既然埃及是整个阿拉伯阵营公认的领袖,那么埃及总统萨达特提出的条件,一定代表了所有阿拉伯国家共同的想法。但实际上,在讨论约旦河西岸领土的归属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时,萨达特既没有征求埃及的主要盟友约旦的意见,也没能说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 这意味着即使埃及和以色列达成了和平协议,其他阿拉伯国家也不会配合执行。另外,卡特、萨达特和贝京恰好是来自三个拥有不同宗教传统的国家,三个人的个性也都十分骄傲。这意味着当他们在具体问题上发生争执时,很容易上升到信仰和文化层面的冲突。随后出现的一系列波折,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
在这次长达13天的峰会上,有三个核心问题一直困扰着所有出席者。它们是: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件;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的定居点的未来;巴勒斯坦国的政治前景。 分歧最严重时,会谈几乎当场宣告破裂。
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相对而言是最清晰的。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占领了属于埃及的西奈半岛,在当地部署了军队,还开始迁入犹太移民,建设定居城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曾试图收复西奈,但以失败告终。以色列总理贝京认为,西奈构成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重要的战略缓冲,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埃及总统萨达特同样拒绝让步,因为西奈不存在复杂的历史纠葛,一直以来都是埃及的一部分。双方断断续续的争吵持续了十天;到了第十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说服西奈定居点的设计者沙龙将军向贝京总理建言:与埃及实现和平,要比西奈的归属更加重要。 经过一天的犹豫,贝京最终同意迁出移民、交还西奈,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直接矛盾得到了解决。
第二个问题涉及约旦河西岸领土的归属,脉络最为复杂。在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巴以分治方案中,西岸地区的大部分领土属于新的巴勒斯坦国。但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这个方案,并在1948年发动了第一次中东战争。战争结束后,西岸领土被约旦控制。到了1967年,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获得大胜,不仅占领了整个西岸,还控制了圣城耶路撒冷。在那之后,历届以色列政府陆续在西岸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犹太人定居点,并且拒绝撤出。
在西岸问题上,有两个技术细节成为矛盾的焦点:其一是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其二是耶路撒冷的国际地位。埃及本身在西岸没有直接利益,但埃及总统萨达特作为阿拉伯世界公认的领袖,需要在这个问题上维护本国的盟友约旦和巴勒斯坦。而以色列总理贝京的政治基础之一就是西岸的定居者社区,自然也不肯让步。针锋相对的博弈一直持续到了峰会最后一天。最终,埃及政府接受了美国方面的提议,同意把西岸问题放在巴勒斯坦自治的整体方案下来解决。以色列则承诺会在五年内撤出在西岸的驻军,并取消目前的管理机构。但以方坚持要求保留已经建成的定居点,并拒绝承诺不会进一步扩建。这个问题在最终的协议文本中实际上被模糊处理了。埃以两国也同意暂时搁置争议巨大的对耶路撒冷地位的声明。
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同样引发了激烈的争吵。从1947年联大通过巴以分治方案开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实际上一直没能建立起来。埃及作为阿拉伯阵营的领袖,虽然支持巴解组织的武装斗争,但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态度十分暧昧。以色列则干脆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双方最终同意用“自治”的框架来取代政治意味更强的“建国”:以色列承诺,会在五年之内撤出西岸以及另一块巴勒斯坦领土加沙地带,由当地阿拉伯裔居民自行组织独立的民政机构。埃及还要求让约旦加入巴勒斯坦地区的自治进程。未来的自治谈判,将在埃及、以色列和约旦三国之间举行。至于巴勒斯坦本身,埃及方面没有提及它的独立建国问题,也没有商定如何让分散在整个世界的巴勒斯坦难民重归故土。这也成为后来一系列冲突的根源。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埃及总统萨达特不采用这样的模糊战术,整个峰会都将无法进行下去。
第十三天,1978年9月17日,三位领导人最终签署了关于中东和平的两个框架性协议。第一项协议涉及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第二项则是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件。 六个月之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了全面和平条约。尽管框架协议本身存在明显的缺陷,但在当时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它终结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长达30年的军事对抗状态,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发展正常关系创造了机会。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也因此被授予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
当然,长达13天的峰会过程,并不总是在唇枪舌剑中度过。三位领导人和他们的随员都有许多轻松时刻。习惯早起的美国总统卡特夫妇会在清晨打上一个小时网球,周末还会到附近钓鱼。 在约见以色列外交部长达扬时,卡特赠送的礼物是故乡佐治亚州的花生,因为他自己在少年时代就种植过好几年花生。 立场彼此对立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某些时候也会变得非常“八卦”。峰会第三天,他们刚刚互相拍完一通桌子,就立即转到了萨达特在接受采访时偷吻美国女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的花边新闻。 第六天,卡特邀请贝京和萨达特一同前往葛底斯堡旧战场参观。在美国总统的专车上,贝京和萨达特兴致勃勃地交流起了坐牢的“经验”:他们在青年时代,都曾因从事激进政治活动入狱过。
鉴于萨达特和贝京在最初的会面中表现得互不相让,从第四天开始,卡特减少了两人的直接对谈,改为由美国官员和双方的几位关键代表做私下接触,再汇总彼此的意见。这给不少参会者提供了难得的闲暇时光。第五天晚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陪贝京下了四盘国际象棋,并以1:3告负。有人认为,这是布热津斯基在安抚贝京的情绪,以换取以色列人在西岸问题上让步。 埃及外交部的正副部长则用彻夜长谈来打发时间,揣测着自己的总统和美国领导人的真实想法。 第十天,会谈一度濒临破裂,心情郁闷的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连看了5遍电影《巴顿将军》,整晚都没有睡着。 幸运的是,三方代表最终达成了共识,这场戴维营峰会没有在中途前功尽弃。
好了,以上就是《九月的十三天》一书描述的1978年戴维营峰会的主要经过。和通常的国际峰会不同的是,在戴维营,三位最高领导人介入了每一场谈判的具体细节。为了贯彻自己的理念,他们甚至会和自己最亲密的顾问发生冲突。 这意味着个人性格有时会超越具体的谈判策略,成为决定峰会前途的关键因素。另外,作者莱特也提到:自己最初的计划是把戴维营峰会的过程写成一部舞台剧。 为了增加戏剧张力,他精心搜集了大量素材,对每位领导人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特质都做了揣摩。正因为如此,卡特、萨达特和贝京的形象被描写得极为鲜活,令人印象深刻。
美国总统卡特是戴维营峰会的发起者,也是全书的线索人物。作者莱特注意到,卡特身为一名前海军军官和典型的美国南方政治家,对国际事务了解不多,更不清楚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那些复杂的历史纠葛。 他的许多个人判断,建立在不可靠的感觉基础之上。比如,只因为埃及总统萨达特和自己都出生于农村家庭,卡特就认定他比其他人更能体会萨达特的心态和感受。 而卡特对以色列人的好感,则是源自青少年时代几位为他提供过莫大帮助的犹太裔朋友。 虽然卡特对以色列总理贝京在峰会上的强硬立场多次表现出不满,但为了回报昔日朋友的善意,他还是愿意尽力坚持下去。
另外,卡特总统还是一位偏执的理想主义者。在政治生涯早期,他和美国佐治亚州猖獗的种族主义现象进行了顽强斗争,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声望。 这种经验使他由衷地相信,中东和平面临的障碍也可以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来克服,并且他本人就是完成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作者莱特引用卡特的前演讲撰稿人法洛斯的话说,这位总统相当自以为是,经常沉溺在琐碎的细节中,却缺乏真正的智慧。 不过在某些时候,“不聪明”也意味着具备强大的决心和韧性,这是许多人都缺乏的。
卡特的这些优点和缺点,在戴维营峰会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始,他低估了会谈的难度,甚至认为萨达特和贝京在那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已经有了共识,自己只是一个单纯的主持人。 但这种幻想很快被激烈的争吵所打破。卡特惊讶地发现:自己不仅要安抚另外两位领导人的情绪,还必须帮助他们找到可以妥协的具体问题,以形成协商的基础。因此,从第五天开始,卡特打破外交惯例,主动列出了20多个需要商讨的核心事项,作为谈判的基础。 他随后分别找到埃及和以色列代表团的核心人物,征求双方的意见,再把沟通的结果写进最终协议的草案。为了避免萨达特和贝京这两位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情绪影响到谈判的进行,卡特还开创了“代理人谈判”的模式,让埃及和以色列双方各派一名法律顾问去从事前期各项问题的商议。 也是在卡特的坚持下,以色列总理贝京勉强同意对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和巴勒斯坦的前途暂时不做定论。 这为两项框架协议的成功签署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可以说,如果没有卡特这位缺少外交经验,但是意志力极为坚强的美国总统;如果不是他赌上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一定要将峰会推进到底,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和解,可能还要耽搁更长时间。卡特这位“主持人”,实际上成为峰会的主角。
埃及总统萨达特是一位精明干练,富于个人魅力的政治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后来又长期担任埃及政治巨头纳赛尔的副手,外交手腕之高超曾经令基辛格叹为观止。 萨达特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第一位意识到必须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政治家;正是他在1977年对耶路撒冷的“破冰”访问,开启了通往戴维营的道路。 但萨达特的立场遭到大多数埃及高级官员的反对。陪同他前往戴维营的埃及外交部长卡迈勒,是总统几十年来最信任的朋友,这时却公开反对在任何问题上向以色列让步。 巨大的心理压力让萨达特的情绪变得起伏不定,有时甚至要靠星相学的暗示来平复心境。 为了安抚自己国内的反对者,他首先提出了一份条件苛刻的协议草案,随后就保持了沉默。
不过,萨达特毕竟是一位对和平抱有期待的杰出人物。在察觉到因为埃以双方互不相让,峰会正在陷入僵局之后,他迅速改变了谈判策略。一方面,萨达特主动出击,和美国总统卡特展开了沟通,通过美国方面向以色列代表施加压力;与此同时,他还私下约见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透露了自己的谈判底线,也了解了对手的核心诉求。 这种机敏灵活的姿态,对和平协议的最终达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萨达特内心也很清楚,自己从此将被整个阿拉伯世界视为叛徒和罪人。峰会结束后,他开始频繁地谈论死亡,并且越来越不愿和外界接触,仿佛知道自己大限将至。
在出席峰会的三位领导人中,以色列总理贝京的个性最为复杂,立场也最强硬。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缺少安全感,对以色列的周边环境抱有深切的忧虑。 贝京虽然承认,以色列无法长期维持扩军备战的状态,但他又偏执地认定:阿拉伯国家对犹太人只存在仇恨和猜忌,没有任何善意。以色列只有依靠武力,才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协议,也必须优先考虑以色列的安全需求。这种攻击性十足的姿态,让贝京多次成为破坏峰会气氛的麻烦人物,连美国总统卡特也感到不胜其烦。不仅如此,贝京的行事方式,还受到他独特的从政经历的影响:贝京和“现代以色列之父”本·古里安曾经是长期的政敌,舆论形象不佳,还被爱因斯坦和阿伦特批评为“恐怖分子”。 但在1977年以色列大选中,贝京代表的强硬派却意外获胜,这给他增加了巨大的自信。 当峰会陷入僵局时,贝京往往会拂袖而去,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和其他人交流,直至他的要求最终得到满足。这显然不是一种有诚意的沟通方式。
所幸,以色列代表团中的几位重要成员,个性和他们的总理截然不同。如果说在埃及方面,是一位“鸽派”总统萨达特领导着一群咄咄逼人的“鹰派”部长;那么在以色列方面,就是“鹰派”总理贝京被一群“鸽派”部长包围着。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是埃及总统萨达特最信任的对方官员,他不厌其烦地在两个代表团之间穿针引线,获得了埃及方面的重要保证。 以色列外交部长达扬是军人出身,身经百战,但也因此觉察到了武力的局限性。在贝京总理拒绝露面的情况下,达扬和魏茨曼以及大法官巴拉克充当了以色列方面事实上的谈判代表,并参与拟订了协议的初步文本,争取到了理想的结果。
然而,在长达13天的峰会期间,贝京身上感性、质朴的一面也渐渐流露了出来。当卡特专门为他的孙子和孙女题写签名照片时,贝京热泪盈眶,随即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在和卡特、萨达特一起参观葛底斯堡旧战场时,贝京的情感波动也是最强烈的,似乎第一次意识到了和平的价值。 尽管他也曾经抱怨说,戴维营好像“一座豪华的集中营”,但在峰会进入第十一天之后,贝京最终放弃了他的不合作立场,抓住了转瞬即逝的和平机会。在第十三天的签字仪式结束后,他兴高采烈地告诉一位朋友,自己刚刚签署的是“犹太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份文件”。
好了,关于劳伦斯·莱特这本《九月的十三天》的主要内容,以及书中涉及的核心人物,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早年的一些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著作,会略微神化当事人的个人形象。无论是19世纪的梅特涅、俾斯麦,还是20世纪的罗斯福、基辛格,在一代代作家笔下已经变成了“老谋深算”这个词语的化身。似乎当他们出席任何一场国际峰会时,都会提前准备好精心设计的谈判方案,随后借助一系列话术和个人魅力,取得预期的成效。但《九月的十三天》告诉我们,真相可能根本不是这样。美国总统卡特、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都是当时优秀的资深政治家,也都清楚这场戴维营峰会的重要性。但他们最初的想法和峰会的实际发展经过,可以说大相径庭。一开始,卡特的角色是主持人,中途却变成了和平方案的实际起草者。他时而循循善诱,时而做出威胁,这才避免了谈判在中途就宣告破裂。 萨达特和贝京在前两天都抛出了自己的方案,但他们的诉求截然对立,立场又针锋相对,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沟通的效果。在戴维营的封闭环境里,这种对立几乎变成了个人敌视。如果不是埃及和以色列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设法从中斡旋,如果不是两位领导人最终稳定了心态,握住了对方伸出的橄榄枝,事情本来可能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
在全书的结尾处,作者莱特感慨地说:从1948年到1978年,中东各国本来有无数提前实现和平的可能。 但无论是以色列还是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都把自己的荣誉感看得太重,认为和平就等于投降,从而放任军事冲突一次又一次地升级。即使是在代表阿以双方的萨达特和贝京已经抵达戴维营之后,这种荣誉感以及历史和文化因素带来的压力,依然会时不时地闪现出来,影响他们的情绪,令他们陷入间歇性的抑郁、烦躁和自我封闭。这可以说是人性使然。但人性还有另外一些侧面:在精疲力竭的关头,它会渴望确定性,会容易被一些小事打动。微薄的信心和偶然迸发出的善意,在某个时刻被激发和组织起来,这才决定了峰会的最终结果。可以说,和平未必属于必然,因此才弥足珍贵。
更令人唏嘘的是,三位渴望在戴维营挽救自己政治生涯的领导人,随后的命运却发生了逆转。美国总统卡特虽然成功促成了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但没能抑制住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攀升,他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也很糟糕。这让卡特在1980年总统大选中输给了里根,从此离开政坛。 埃及总统萨达特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变得众叛亲离,本国的激进宗教势力也把他看作头号敌人。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在参加纪念第四次中东战争的阅兵仪式时遭到暗杀,阿拉伯国家没有派代表出席他的葬礼。 至于以色列总理贝京,他在峰会后期流露出的善意和感性,很快重新让位于偏执的扩张政策。1982年,以色列悍然介入黎巴嫩内战,引发了第五次中东战争,却让自己的周边环境变得更加险象环生。心力交瘁的贝京在1983年宣布辞职,随后变得离群索居,直至1992年去世。 这场历史性峰会,并没有帮到它的当事人。
但在40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尽管《戴维营协议》存在众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毕竟彻底终结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抗状态。从1978年到今天,这两个国家没有再发生战争,两国关系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这在暴力肆虐的中东政治中称得上难能可贵。“冷战”结束后,约旦也参考埃及的先例,与以色列缔结了和平条约。从这个意义上说,戴维营峰会的正面成果毕竟没有被浪费,它实实在在地改善了中东的国际环境。不过,这场峰会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尽快达成一致,美国、埃及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巴勒斯坦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地决定了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为了向以色列方面显示诚意,美国和埃及还同意搁置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以及耶路撒冷地位问题。这就给新的冲突留下了导火索。直到今天,巴以关系仍然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也提醒着人们和平的稀缺和珍贵。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此外,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这本《九月的十三天》,它用舞台剧式的笔法,塑造了参加1978年戴维营峰会的三位领导人个性鲜明的形象。如果你希望了解今天阿拉伯-以色列争端的历史渊源,本书会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
在40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尽管《戴维营协议》存在众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毕竟彻底终结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抗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