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五代至南宋》 朱步冲解读
《中国绘画:五代至南宋》| 朱步冲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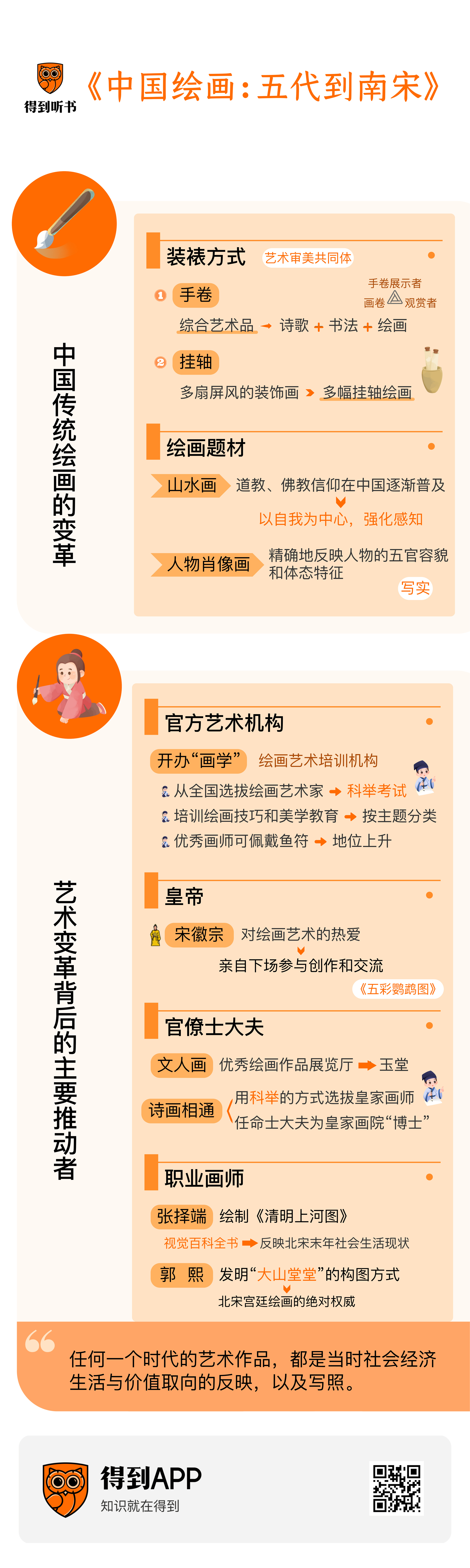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美术历史学家巫鸿的新书《中国绘画:五代至南宋》。
从五代到宋这个时段,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与社会剧变的年代,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大变革年代,无论是绘画呈现的载体,还是描绘的内容主题、绘画技巧,都发生了显著的革新和拓展;传世名作和经典大师,如同井喷一样,纷纷涌现。一提到中国传统名画,我们脑海中所浮现出来的经典之作,比如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或者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很多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艺术,是反映社会生活与制度变迁的一面镜子,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缩影。中国传统绘画,是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详细了解它们诞生的时代和技术背景,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经典作品背后的时代意义与审美价值;一方面,也能让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血脉,有更加准确的了解与把握。
本书作者巫鸿,是著名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专家,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早年获得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曾任职于故宫博物院,2022年荣获美国大学艺术学会“艺术写作杰出终身成就奖”。这本《中国绘画:五代至南宋》,是巫鸿先生中国传统绘画史三部中的第二部,着重为大家介绍这个中国艺术史上的繁荣与大变革时代。
在本书前言中,巫鸿表示,自己在写作时,叙述的主要线索,既不是朝代与年代更迭的时间线,也不是作为人物的画家,而是绘画作品本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到艺术本身:即使是作者未经考证的作品,甚至寂寂无名的普通画家留下的作品,依旧是那个变革年代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保存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只鳞片爪,以及创作中作者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标准。另外,对于那些传世大家来说,现存文献往往只能给我们一个高度抽象、浓缩的生平记载,反过来,如果我们转而关注他们的作品,反而能提取出更多直观而丰富的信息,从而能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那个古老的时代。
接下来,我就分两部分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看,从五代到宋,中国传统绘画在技巧、题材和载体方面,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革,而在第二部分中,我们转而来看看这场艺术变革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分别是建立官方艺术机构、赞助绘画的皇帝,作为绘画审美标准制定者的官僚士大夫,以及职业画家。
首先,在本书一开头,作者巫鸿就说,在五代到宋这个时期,绘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独立地位,单独构成了一种视觉艺术类型。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啊,从上古时期到唐代末年,我国传统绘画的主要形式载体是壁画和屏风画。墙壁和屏风,一个是房屋建筑里的构件,一个是家具,它们的重要作用,都是把建筑空间进行切割,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区域,而上面的各种图案和纹样,主要是起到一个装饰性的作用。所以用今天的话说,在唐代之前,绘画的作用,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视觉艺术,不如说是一种为建筑和家具进行美化,锦上添花的装饰。
然而,从五代到宋,有两种全新的绘画装裱方式诞生,一种叫手卷,一种叫挂轴。手卷就是一种高度在30厘米左右的绘卷,在收纳状态,是圆筒状,中间有轴。原本,这是中国传统文字书籍档案的装订方式,但从两汉魏晋时代开始,就逐渐被用于绘画作品的装裱和展示。
古人观赏绘画手卷,还有一套讲究,比如,一场文人雅集里,主人要向来宾展示自己刚刚到手的珍贵画作,于是,以主人为中心,大家就齐聚在桌子周围,主人从最右端开始,把手卷徐徐展开,平铺于桌案之上。位于中央的绘画部分,称为“画心”,在绘画画面的左右,是创作者或者收藏家为画作撰写的题跋,内容是介绍画作的主题,或者对画家技巧的称赞,以及为相应绘画主题而创作的诗歌。这样一来,一件手卷,就变成了集诗歌、书法与绘画于一身的综合艺术品。
手卷的展示与鉴赏,也显示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魅力。随着手卷的打开,通过绘画形象构成的主题和故事,如同电影一样在观赏者面前,徐徐展现,让每一名观众都产生持续不断的遐想与期待,也形成了手卷展示者、观赏者,以及画卷本身三方的互动。
说完了手卷,再来介绍下挂轴。相对于手卷,挂轴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作者巫鸿考证说,挂轴这种装裱形式,可能最初出现在唐代,最终于宋代发展完善;如果简单粗暴地类比下,可以说,挂轴就是画面竖立,上下长,而左右窄的手卷,可以长时间悬挂在墙壁上鉴赏,而它竖长形的构图形式,则是借鉴了之前的屏风绘画。作者巫鸿在书里举例考证说,活跃在五代末年,至宋代的著名画家巨然,流传到今天的几幅挂轴名作,比如《溪山兰若图》《层岩丛树图》,以及《秋山问道图》,很可能原本是为一架多扇屏风创作的装饰画,后来被分别取下,装裱变成了挂轴绘画,然后落入不同的藏家之手。
那么,这两种全新的绘画装裱、收藏技术的诞生,对于绘画本身有什么影响呢?我自己想了一个比喻,那就是,更加便携的特性,让绘画拥有了更强的社交属性,方便画家和鉴赏收藏者,聚集起来进行社交、买卖与品鉴活动,进而创造了一个所谓的“艺术审美共同体”,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绘画技术的进步和审美标准的形成。这个情况,和手机拍照技术与移动互联网成熟后,基于手机照片和短视频分享的互联网社交平台纷纷出现,同时颠覆了原有的摄影艺术审美标准,是一个道理。
举个例子,在五代之前,经典绘画作品,不是壁画,就是屏风,大家想去看,就必须远途跋涉,去画作所在的寺院,或者名人家里,太麻烦了。现在好了,有了手卷和挂轴技术,大家就可以约一个方便的地方,先吃饭喝酒,然后画作的所有者,打个响指说“哥儿几个,差不多了,来看看我这幅《春树秋霜图》!”于是,招呼下人拿出挂轴或者手卷,找个挂钩一挂,或者在桌案上给大家一展,所有人都能当场观看点评了。
在简单介绍完手卷和挂轴这两种全新、轻便的绘画装裱、收藏技术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从五代到宋代,由于绘画艺术的繁荣,绘画的题材,出现了哪些细分领域。
首先,我们来看看山水画。
山水画的兴盛,与道教、佛教信仰在中国的逐渐普及密切相关。在唐代之前,之所以山水等自然景观没有被当做重要的绘画题材,是因为当时的画家认为,这些自然界中的地理景观,没有内在的生命,因而作为创作主题的人,和它们难以产生精神上的共鸣;然而佛教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与观察,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们感官中呈现出来的外部世界,正是人类内心世界的延伸。所以,从东晋到隋唐,无论是文学,还是绘画,都开始逐渐追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强化感知的创作手法:描写的重点可能是景物转瞬即逝的某一刻;而且,创作者的情绪和心境,和诗歌绘画中所描述的景象混为一体,没有界限。读者可以跟随诗句的描写或者画家的笔触,在山水楼台和诗人的内心感怀之间随意穿越。
其次,人物肖像画,在五代到宋这个时段,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人物肖像画更加写实,能够精确反映出人物的五官与容貌,以及体态特征。为什么画家的技巧出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呢?作者巫鸿就说了,首先,宋代结束了唐末五代的战乱割据局面,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社会经济,在两宋之间达到了高度繁荣,极大促进了艺术品的创作和消费需求。另外,由于唐末残酷的战乱,让许多人远离故土,异地定居,所以他们格外重视各类祭祖活动,而在祭祀活动中,挂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祖先画像,能够有效让子孙们牢记家族血脉的渊源,增加家族向心凝聚力。
不仅如此,包括佛教、道教在内,很多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促进了人物肖像绘画技术的进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刚才我们说过,手卷和挂轴,让绘画的收藏和展示,变得更加普及、便捷。很多信徒在家修行、礼佛,缺乏足够的空间来安置佛像,那就在墙上挂一幅宗教题材绘画,比如释迦牟尼或者菩萨的肖像,当做平替。毕竟,画神仙,画菩萨,也是依据现实中,人的相貌为蓝本,这就要求画师对于人相貌体态的把握和描绘,要越来越精确。
同时,宗教信仰的兴盛,还带来了一个现象,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信徒,愿意出资,修建寺庙或者开凿石窟,这个身份,就叫供养人。当然,这些供养人出了钱,肯定也要留个名,宣扬自己的功德,所以就要请画匠,在寺庙或者石窟的宗教壁画上,或者佛像的旁边,找个偏僻一点的位置,把自己的形象画上去,或者立一个小塑像,当然了,塑像和画像肯定是要求和供养人自己越像越好。
作者巫鸿,就在书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下面这张绘制于北宋乾德六年,公元968年的《水月观音图》。这张绢画,最早发现于敦煌藏经洞。在画面的最下方,就是四名供养人的形象,分别是当时敦煌镇的行军司马曹延清,以及他的侄女、母亲和夫人,一男三女。

好了,说完了五代到宋这个时间段里,中国传统绘画在绘画技巧、题材和装裱展示技术上的变革,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顺着作者巫鸿的叙述,来了解一下这场绘画变革背后的主导力量,也就是人,包括当时的文人官僚士大夫,还有那些为宋代皇家宫廷服务的职业画师。
我们知道,宋代是一个君主和中央王朝权力大大增强的朝代,同时,由科举考试选拔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逐渐构成了各级官僚的主体,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门阀大族,则逐渐衰落。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就把这场社会政治层面的变革,称为“唐宋之变”。这种政治上的趋势,必然也会决定当时的社会风气,最终反映在当时的艺术创作中。作者巫鸿总结说,时代之变,对于宋代绘画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两项:首先是皇帝与宫廷一方面积极赞助绘画,同时也利用自己的偏好,对绘画的审美与发展,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是新兴的士大夫官僚群体,逐渐成为绘画创作和品鉴的主体。
从唐代开始,由于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物质财富的持续积累,让文人官僚的日常生活与社交呈现出审美化和艺术化的倾向。创作和品鉴,成为他们社交聚会消遣的主要乐趣之一。这种审美活动,成为士大夫官僚之间加强凝聚力的重要推手,所以古代中国绘画艺术的标志性流派“文人画”,也就在这个时期,宣告诞生。
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士大夫官僚,是如何把影响力从政治舞台延伸到艺术领域的呢?首先,北宋初年,在皇帝的旨意下,朝廷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叫翰林学士院,职责是起草朝廷文件,同时为皇帝当顾问,提供政治决策上的建议。991年,宋太宗亲自给学士院的正厅写了一块匾额,叫“玉堂”,从此玉堂也成为学士院的别称。有趣的是,皇帝在这个办公厅里,布置了丰富的壁画和屏风画,后来,但凡是学士院里官僚的优秀作品,也有机会被公开在玉堂里展示。渐渐地,玉堂就变成了学士院官员的优秀绘画作品展览厅,而这些官员,也纷纷感觉,自己的绘画作品能够在玉堂里出现,是一种殊荣。
当然了,这些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官员,也会对玉堂里展示的画作进行点评,这些意见,皇帝本人自然也非常重视;相应的,玉堂里的绘画会定期更新,那些职业画家在创作的时候,也会参考学士院里这些官员的审美。
举个例子,北宋著名山水画家郭熙,他的作品之所以口碑好、地位高,不仅是因为绘画技巧精湛,更是因为他的绘画风格,被许多重要的文人士大夫推崇,后者认为郭熙的绘画,忠实反映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和情感。包括苏轼、文彦博、黄庭坚等著名士大夫文人,都曾为郭熙的作品题诗,表达他们的喜爱。
日本著名美术史研究家岛田修二郎说,宋代的山水画体现出一个什么倾向呢?就是,自然景观被理想化了,也就是说,由于科举士大夫掌握了对绘画的审美话语权,所以在他们心目中,自然景观的本来面目变得并不重要;绘画的目的,是借助山水风景,来表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秩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为了把职业画家的画风,和士大夫精英阶层的精神统一起来,后来的宋徽宗还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决定,那就是,用科举的方式来选拔皇家画师。考试内容之一,就是要这些画家先读古代文学大家的诗词,然后以其中的诗句来作为绘画命题,只有那些能把古人的“诗意”和绘画表现融会贯通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后来,这种要求,就变成了中国传统文人画里的一个重要评价准则,叫“诗画相通”。正如北宋著名诗人和画家张舜民总结的那样: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另外,宋徽宗还先后任命米芾、宋子房等著名文人士大夫,担任皇家画院的“博士”,也就是专业老师,来对这些职业画家进行文化教育,让他们更能领会士大夫官僚心目中的审美标准。
一方面,北宋画家在努力迎合士大夫官僚的审美与品位,同时另一方面,北宋的士大夫官僚,也开始积极参与绘画创作,把绘画当做一种直抒胸臆的风雅消遣,以及在社交场合的交流媒介。有意思的是,宋代乃至后世的文人绘画,都刻意表现出一种“业余”风格,也就是说,具体的绘制笔法并不需要精细,主题和意境,以及搭配的诗文,反而更重要。
例如,北宋末年的著名文人画家李公麟,出身于官宦世家,进士出身;虽然官职从来没有达到过五品以上,但因为擅长绘画,所以他在同时代的士大夫官僚中,享有盛誉。
李公麟能够驾驭的绘画题材很多,从山水到人物和动物。但有趣的是,他最擅长的技法,却是白描,笔下的形象,也都很朴实庄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非常简单,不炫技。但是,同时代爱好艺术的士大夫都说,李公麟的绘画之所以好,就好在深厚的文化内涵,甚至达到了“当世无与伦比”的地步。具体来说就是,李公麟对于古代文物书画的鉴定,有很高的水平,这就导致,他的画非常有“古意”,也就是宋代之前那些绘画大师的意境和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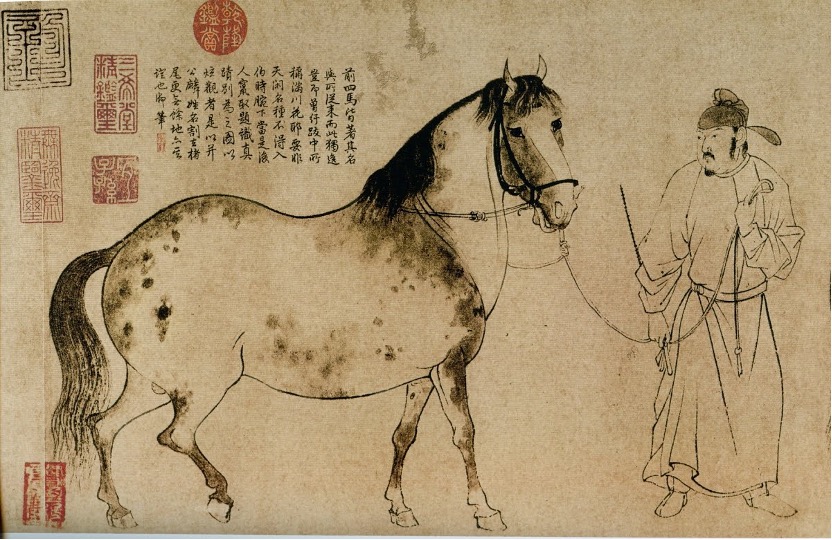
说完了科举官僚与士大夫对于绘画艺术的影响,我们再来看看,宋代皇帝和宫廷在这轮绘画艺术变革中的作用。作者巫鸿就在书里说了,首先,在宋太宗的主持下,北宋朝廷在公元984年,也就是雍熙元年,成立了一个御用绘画机构,叫翰林图画院,把全国各地的著名画家,悉数网罗进来。这些有了编制和固定工资的画家,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皇帝和宫廷提供服务,从绘画到壁画创作,临摹宫廷收集的古代名人字画,以及为皇帝当枪手代笔,生产赏赐臣下的书画,等等。
这些奉旨创作的美术作品,其核心目的,主要就是宣扬皇帝的仁政和所谓的繁荣盛世。当然,北宋宫廷绘画的技法和审美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就是皇帝个人的审美好恶。比如说,宋太宗就比较喜欢来自四川的黄筌和黄居寀父子。他们原本是后蜀政权的宫廷画家,擅长精细富丽的花鸟工笔画;后蜀灭亡后,黄氏父子就被宋太宗罗致到翰林图画院。结果,黄氏父子的四川蜀地工笔画风格,就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宋代宫廷画院的主流技巧和审美标准。在今天的故宫博物院里,还收藏有一幅黄筌的真迹作品,也是唯一传世的一幅,叫《写生珍禽图》,上面描绘了麻雀、斑鸠、蝉、乌龟、蟋蟀等几十种动物昆虫形象,形态精确,栩栩如生,色彩丰富。

然而,到了宋真宗和神宗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的品位,更倾向于自然清雅,黄氏父子那种精巧富丽的风格不再受宠了。于是,籍贯安徽的花鸟与景观画家崔白,成为宫廷画院里的当红炸子鸡:崔白作品的特征就是,虽然在鸟类等动物的具体描绘上,细节依旧写实精致,但背景,往往是大片墨染组成的自然环境,粗犷写意,例如秋冬季节萧瑟的枯枝、芦苇,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在宋代绘画中,最能体现皇权影响艺术创作的案例,莫过于宋代山水画中,一种固定的构图技法,叫“大山堂堂”。这个专有名词,是刚才提到过的北宋山水画家郭熙发明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幅山水画,画面中心,是一座雄伟的大山,牢牢地占据了中心地位,并且控制了整幅画面的布局,其余的山岗、坡峦、林木等等均处于次要地位,仅仅是点缀。在西方关于中国传统美术与绘画的研究著作中,这种“大山堂堂”构图还获得了一个独特的名字,叫“纪念碑式风景画”。
在宋代山水画里,“大山堂堂”这种构图的经典之作,或者说开山之作,是著名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这幅雄伟大气的作品中,雄伟的山峰充满了画面的三分之二,是绝对主角,以往山水画里比重比较大的前景,被大幅度压缩,从而让观众感觉到,如同纪念碑一样的山峰,从云雾中突然升起,和画面下方如同蝼蚁一样的人物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者巫鸿分析说,“大山堂堂”这种绘画构图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挂轴这种绘画装裱方式的普及,让画家们都倾向于用竖直的长方体画面来设计自己的构图;但更重要的,是北宋朝廷,希望皇家画院拿出能够彰显皇帝权威的绘画作品;所以,在“大山堂堂”这种构图里,画面中央的山峰,实际上是代表高高在上的皇帝本人,具有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而其他万物,则只能是臣服于大山的点缀。发明这个词的北宋画家郭熙,后来就有一段论述,翻译成白话就是:画面中央的主峰,如同皇帝,而其他丘陵谷地、溪水瀑布和画面上出现的微小人物,则分别和各级官员与平头百姓对应;所谓山水图,实际上就象征着理想中的北宋社会等级地位分布。
到了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代,由于这位皇帝对艺术的喜爱,导致北宋宫廷绘画,无论是艺术水平还是产量,都达到了一个顶峰,同时,宫廷绘画也成为整个北宋时期绘画最具影响力的流派和审美标准。
1104年,宋徽宗开办了“画学”,可以被看作是皇家宫廷下属的绘画艺术培训机构,以类似科举考试的办法,从全国选拔绘画艺术家;入选之后,这些画家不但要按照主题分类,比如花鸟、山水、鸟兽、人物等等,学习提升自己的绘画技巧,而且还要接受系统的美学教育,例如临摹和观赏宫廷收藏的历代画家墨宝。宋徽宗还规定,出类拔萃的画家,可以佩戴鱼符。鱼符,是一种外形如同鱼类的金属佩饰,在唐宋时代,只有官员才能佩戴;而宋徽宗继位后,宣布皇家画院里的优秀画家也可以佩戴,证明画家在宫廷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不再是卑微的工匠。
同时,由于对绘画艺术的热爱,宋徽宗已经不满足于充当画家们的评审与赞助人,而是要亲自下场参与创作以及交流。用现在的话说,在皇家画院里,宋徽宗自己又是裁判,又是水平第一的明星选手。关于宋徽宗痴迷绘画的历史记载有很多,当时有个热爱绘画的官员邓椿,撰写过一部当时著名画家传记大全,叫《画继》,里面就有许多宋徽宗与画院的逸闻趣事:比如隔三差五,宋徽宗就给皇家画院发出自己想的绘画命题,让大家展开创作比赛,然后亲自选出出类拔萃的优胜者,并加以赏赐。
徽宗时期宫廷绘画的特点,简单来说就是色彩艳丽、笔法细腻;从颜料到装裱材料,都讲求昂贵。同时,宋徽宗本人也会利用一切料理政务之外的闲暇时间,来到画院,和画家们一起挥毫泼墨。前面说过的邓椿,就夸这位皇帝的画作是“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不过,如果我们看看宋徽宗遗留至今的画作真迹,就会明白,虽然这种夸赞里有谄媚的成分,但宋徽宗自己的绘画水平确实很优秀。比如流传到今天的这幅《五色鹦鹉图》:画面的核心,是一只色彩斑斓的鹦鹉,栖息在一株盛开的杏树上,鸟类艳丽的羽毛和粉红的杏花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宛如人工盆景一样的景象。根据这幅绘画上宋徽宗亲自撰写的诗文,我们得知,这只鹦鹉是南方进贡来的,宋徽宗以天才画家一般的敏锐,捕捉到了这个构图优美的时刻,迅速创作了这幅画作;当然,这幅画的核心目的,依旧在于夸耀宋徽宗自己的德政:远在南方的边远小国都感化于大宋的威名和恩德,为此特地送来珍稀的鹦鹉作为贡品。

当然,如果非要列举一张大家最为熟知的宋代传世名画,那估计很多人都会投票给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张绘画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从咱们小时候用过的课本,到各种旅游文化专题片和文创延伸商品。
由于史料缺失,今天我们对张择端的生平几乎是一无所知,唯一的线索来自《清明上河图》附带的题跋,是由金朝人写的;里面说,张择端入选过翰林院,是一位通过科举入朝为官的士大夫,在首都汴梁游学期间开始学习绘画,擅长所谓的“界画”类题材,也就是城市、房屋、桥梁等人造景观,自成一派。
实际上,这幅传世名作的尺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巨大:画卷高24.8厘米,长5.28米,装裱形式为手卷;在有限的空间里,作者张择端描绘了814个人物、170多棵树木、60多头牛马牲畜、30多栋房屋楼宇,以及28艘船只。
如果我们按照古人鉴赏的标准,从右到左,徐徐展开手卷,那么我们就会感觉,自己坐在某种飞行器上,从半空中俯瞰清明节时分的北宋首都汴梁:从汴梁城郊的乡镇、农舍、驿站,再到喧闹繁忙的汴河之滨,目睹激荡的河水和大小船只穿越一座宏伟的拱桥,然后重新上岸,进入首都高大的城门,来到汴梁城中繁华的街道,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起喧闹和流动。作者巫鸿评论说,《清明上河图》之所以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显赫的地位,不仅是因为它是写实主义和手卷绘画技术的高峰,更是一部北宋末年社会生活现状的视觉百科全书。
好了,这本《中国绘画:五代至南宋》的大致内容,就为你解读到这里。本书作者巫鸿,利用他深厚的美术专业素养,以及历史、考古学研究积淀,为我们系统讲述了中国传统绘画在十到十一世纪经历的一段重大变革,同时涵盖了名作赏析、画家生平、绘画与装裱技巧的变化、绘画题材的扩展,以及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推动力等等,蔚为大观,如同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了一卷生动而详细的大型手卷,让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变革,有了系统而全面的理解。
总体来说,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作品,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与价值取向的反映,以及写照。
唐宋时代,是中国传统历史上的又一个大变革与繁荣稳定的高峰,被称为“第二帝国时代”。持续大一统所带来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艺术与审美消费的繁盛。同时,由于传统中国逐渐从“门阀大族时代”,进入了士大夫官僚时代,通过科举晋升为官僚的知识分子,构成了帝国官僚的主体,那么这种政治权力格局上的剧变,必然导致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生活上的变革;于是,艺术审美与创作也相应地,同时在创作主题、技术与载体三方面,出现了革新与变化:从总体上看,新兴的科举文人官僚群体,连同权力大大扩张的北宋皇权,一起重新定义了绘画的审美标准;相应地,宫廷和文人绘画,逐渐成为北宋以后,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流派,绘画开始与书法、诗词结合,变成一种三位一体的视觉艺术表现形式。
另外,由于丝、绢等纺织原料的广泛应用,以及新兴士大夫官僚群体的审美社交需求,“手卷”和“挂轴”,这两种全新的书画装裱形式,逐渐成为主流。相对于之前的壁画和屏风画,手卷和挂轴不仅帮助绘画,摆脱了建筑与家具的限制,成为独立的视觉艺术表现形式,而且由于它们便于携带、收藏的属性,能够让画家与士大夫在各种酒宴社交场合里,随时拿出来进行交流与创作;从而让绘画品鉴和诗歌创作一起,成为士大夫群体的主流爱好;更催生了文人画,这种中国传统绘画中影响力最大的流派。
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中,作者巫鸿还对南宋时期,宫廷文人画风格与技巧的进一步演变、对于民间绘画艺术的影响,以及宗教与墓葬壁画的发展,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讲述。如果你想对这一时代的绘画艺术有一个全面而丰富的认识,可以在听完我们的解读后,再阅读全书。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原书的电子版已经为你附在最后,欢迎你进行拓展阅读。此外,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
总体来说,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作品,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与价值取向的反映,以及写照。
-
中国传统绘画,是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详细了解它们诞生的时代和技术背景,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经典作品背后的时代意义与审美价值;一方面,也能让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血脉,有更加准确的了解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