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俗谈》 刘勃解读
《世说俗谈》| 刘勃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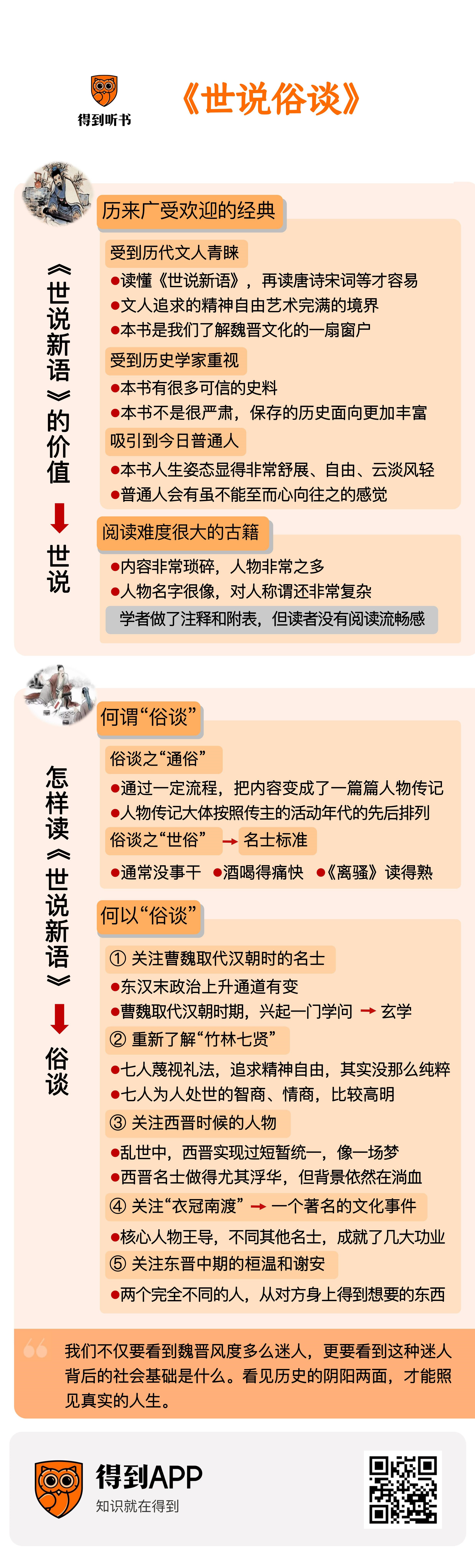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刘勃。
今天和你聊聊我的一本小书,《世说俗谈》。听这个书名,你可能会猜到这本书应该跟《世说新语》有关。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当中,《世说新语》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它是南朝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编纂的小说集。书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东汉末到东晋的名士的。全书不太关心历史大事件,是对名士言行的非常琐碎的记录。
按理说,这样一本既不成体系,格调也显得并不高端的书,很容易在时间的洪流中堕入历史尘埃。但事实上,这本书从诞生以来总是备受推崇。《世说新语》刚问世的时候就不说了,我们说说1500年后中国人对这本书的看法。
鲁迅先生对《世说新语》有句评价,“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简单说就是写人物的言论和行为,都特别传神迷人的意思。你想,鲁迅那是出了名的刻薄,能获得他的称赞,这书大概率不会差。而且,鲁迅据说是号称不开书单的,但他给朋友的儿子列了一个仅有 12 部书的书单,其中就有《世说新语》。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这本书不仅适合现代人读,甚至也包括现代的年轻人。
再比如,我女儿上初一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语文课本里就选了两则《世说新语》。我特地上教育部网站,搜到一份正式文件,名字有点长,叫《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而《世说新语》竟然排在了“初中学段文学类书目”的第二名。
那《世说新语》这部书到底好在哪儿,值得现代中国人继续读呢?更具体一点,《世说新语》讨论的是一千五百年前魏晋名士的故事,隔了这么久,我们能读得懂吗?还有,提到魏晋名士,我们会联想到的“魏晋风度”,它真的像传说中那么洒脱不羁吗?
今天介绍的这本《世说俗谈》将为你解答这些问题。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我讲了快20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杂七杂八也写了快20本历史文化方面的书。这本《世说俗谈》是我最新出版的,我既会为你介绍魏晋风度有多么迷人,也会关掉美颜和瘦脸,讲一讲这种风度背后的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到那时,我们看到的历史场景可能是残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但也许有时候,正是在当时残酷的历史背景下,才显得人格之美尤其可贵。看见历史的阴阳两面,才能照见真实的人生。
介绍《世说俗谈》,我打算从“世说”和“俗谈”两个方面入手。第一部分“世说”,我们会从历史文化维度为你简单介绍,《世说新语》对我们的价值是什么。第二部分“俗谈”,我重点讲读法,面对《世说新语》这部经典好书,怎么读才能读出其中的滋味。
好,我们先看,为什么从古至今人们都喜欢读《世说新语》。换个严肃点的表述,就是《世说新语》对于中国人到底有什么价值?
开头提到鲁迅先生对《世说新语》的高度评价,认为它堪称名士教科书。所以《世说新语》,首先会受到文人喜欢。
古代的读书人,世俗层面的追求,当然是走仕途要当官,精神层面的追求,那就是当名士了。所以自从《世说新语》诞生以来,读书人就几乎没有不喜欢它的。写诗作文,也都喜欢用《世说新语》里的典故。换句话说,不懂《世说新语》,那读唐诗宋词还有后世的其它文学作品,就都会比较困难。
李白为什么那么崇拜谢安呢?“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他的梦想就是学谢安谈笑间平定安史之乱。苏轼为什么经常喜欢cue阮籍、嵇康呢?他的学生,在写诗方面和他齐名的黄庭坚,更据说一步也离不开《世说新语》,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他们追求的精神自由艺术完满的境界啊。
中学里我们都要背的,辛弃疾的词,“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说的是什么事?“八百里分麾下炙”,为什么八百里竟然是一头牛?都要看《世说新语》才明白。所以直到今天,教育部的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里,仍然把《世说新语》摆在突出位置。因为在传统文学的序列里,这部书根本绕不过去,它是我们了解魏晋文化的一扇窗户。
除了文人,历史学家对《世说新语》也很重视。
按照传统分类,《世说新语》是小说,但古代小说的定义和现在不同,它的内容通常不涉及重大主题,但古代小说也是不可以随意虚构的。古代写小说其实像是我们今天发微博或者短视频,说的可能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是不怎么正经的看法,但是如果完全瞎编,是要被骂的。
事实上《世说新语》当然有很多无意识的虚构成分,但可信的史料也很多。尤其是和写晋朝历史的正史《晋书》比,很多时候《世说新语》反而有很多优点。
所谓正史,严格说来是指古代官方认可的纪传体史书。纪传体,本纪放在最前面,突出皇帝,这是体例正;得到当时官方的认可,甚至于就是官方主持修撰的,这是背景正。所以叫正史。但是,这两个特征,并不能保证这部书记录的历史更可信。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历史真相,无关痛痒地问一句“这是正史还是野史”,并不能切中要害,真正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接近真相的关键。
今天的历史学家更看重年代上的接近性。同样是一部《史记》,写黄帝、蚩尤的部分,就不是上古史的可靠史料,因为司马迁距离黄帝比我们距离司马迁还远;但《史记》写刘邦、项羽,尤其是写汉武帝时代的部分,那就史料价值极高。
同样的道理,《世说新语》是晋朝灭亡不久后就编成的,《晋书》是晋朝灭亡两百多年后的唐朝人编写的,所以《世说新语》是更原始的资料。
还有,《世说新语》不是很严肃。它表面上推崇儒家的道德观,可是又好像有点心不在焉;他假装对一些狂放、任性的行为有批判,可是行文之中,又忍不住地透着喜欢。还有一些没什么意义但是好玩的事,它说起来真是兴高采烈。
这意味着《世说新语》不会严格按照当时严肃的价值导向去筛选史料,所以保存下来的历史面向,更加丰富。今天的学者关心的可不仅仅是政治斗争,也会关心社会史、风俗史、生活史,从这些角度看,《世说新语》的不严肃,反而是优点。
要么是文人与文化,要么是历史学者和史料,听起来还是好像跟生活在现代的普通人没啥关系。
其实不然,对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世说新语》也还是很有吸引力,它肯定比很多古书要好看。
今天很多人都在因为活得内卷而焦虑,是《世说新语》里的那些名士们,人生姿态显得非常舒展,非常自由,非常云淡风轻。嵇康被杀的时候,只说一句“《广陵散》从今绝矣”,谢安面对强敌的百万大军压境的时候,还专注和人下着围棋,得到胜利的战报,不过说一句“小儿辈大破贼”,孩子们把贼兵打败了。这是什么样的人生境界!
被沉重的生活负担压迫,被复杂的人际关系束缚的人,读到这样的人生状态,恐怕难免会有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感觉吧。
还有,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做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你这个部门养了多少马,你知道吗?”王徽之说:“不问马。”人我都不问,问马干嘛?
桓冲又问:“马最近死了多少,你知道吗?”王徽之说:“未知生,焉知死。”活着的有多少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死了多少?
王徽之回答的都是《论语》的话,但他挪用之后,都不是本来的意思。这么创造性引用《论语》,产生了奇妙的拼贴效果,非常后现代,把领导噎得没脾气。挨领导骂了而只能忍着的打工人,看着仿佛也很解气。
以上,是说《世说新语》是一部影响力巨大,深受欢迎的书,无论是古代的文人,还是从古至今的历史学者,又或者我们每个普通人都不妨读读《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除了很重要,对于今天的我们,它还有个突出特点,就是很难读。
首先一个大问题就是,全书不到8万字,分成一千多则,通常一则就几十个字,你可以想象内容有多琐碎了。书里出现有名有姓的人物共计将近700位,这么多人物来来去去,读下来很容易晕。
尤其是,很多人名字还很像,甚至同名的也不少。当时是士族社会,一些超级大家族在《世说新语》里占据着核心位置,比如说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就看见一大群姓王的一大群姓谢,到底哪个是哪个啊?他们之间倒是啥关系啊。
更糟糕的是,《世说新语》对人的称谓,还非常复杂。一个人,有名,有字,有小名,有谥号,有官职……称呼起来就会特别复杂。
比如《世说新语》里出现第三多的人是王导,《世说新语》有时称“茂弘”,这是喊他的字,有时喊他“阿龙”,这是叫的小名,有时称官位,那就可能是王丞相,王司空,还有时又干脆简单地尊称为他“王公”。所以一不留神,也会误以为这是几个人。
当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前辈学者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正文下面加注释,还有在书后面附若干张表:告诉你哪些称呼其实是指同一个人;这个人物在《世说新语》的第几门第几则出现过;以及一大家子人,谁是爸爸谁是儿子,谁和谁是兄弟。
比如说,大名鼎鼎的王羲之,和一个叫王允之的,是堂兄弟关系,而王献之、王徽之他们,都是王羲之的儿子,另外一个叫王坦之的,虽然名字里也有个之,但王羲之他们是山东琅琊王氏,王坦之是山西太原王氏,却不是一家人。这些都有老先生给你编成表的。
但是,这对研究者来说固然是很大的便利,足够了,可是对一般阅读者来说,还是不够方便。书看不了几行,就要去看注释,更不用说翻到最后,去查那些表,一点阅读的流畅感都没有了。
面对《世说新语》这道文化佳肴,我们却没法下手,实在是让人着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读这本书呢?
下面,我为你介绍一种我这些年总结的关于《世说新语》的读法,两个字,“俗谈”。
你可以把我写的这本《世说俗谈》小书,当作一套餐具,帮你下手,吃到并吃好《世说新语》这道名菜。
先说说,我这本“俗谈”,到底怎么“俗”了。
第一是比较通俗。
我写作的流程是:第一步,把《世说新语》里某人的相关条目先全部汇总到一起;第二步,正史当中如果有这个人的传记,那就对照传记,或者如果以前有研究者编过这个人的年谱,那就更好了,按照时间线,把这些条目重新排列一遍;第三步,把这些内容组织成文章。
这样,我这本书基本上就变成了由一篇篇人物传记构成的。我们知道,人物传记是比较容易做到可读性比较高的。
然后,这些人物传记,大体是按照传主的活动年代的先后排列的,讲人物的事迹的时候,会特别注重交代时代背景,讲他的言论和行为,在特定社会氛围中的含义。这样,所有这些传记串起来,汉末到东晋的历史大趋势,基本也就讲明白了。
在这样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当中,上面说的人物称谓复杂的问题,一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问题,自然可以在一个人人生经历的讲述当中,顺便就交代清楚了。读《世说新语》原著比较累的朋友,如果从我这本书入门,会轻松很多。
除了“通俗”,《世说俗谈》的“俗”,还有第二个含义,是视角比较世俗。
前面提到,《世说新语》是“名士教科书”。这么说当然是对的。但你也都应该明白,不要以为读了教科书,就真懂怎么当名士了。就像通读了中学各科教材,而没有老师指导你应该怎么刷题,去参加高考的话,分数多半会很难看。更重要的是,哈佛教科书、哈佛公开课满世界都有,哈佛录取通知书,却不会随便发。
其实,跨过门槛的关键,往往并不在教科书里。《世说新语》记录的信息,主要是从东汉末到东晋。这之间虽然有朝代更替,但时代的气质,却有一以贯之的地方。
这个年代,国家机器不如之前的秦与西汉强大,也不如之后隋唐以降的历朝历代。魏晋时代的特权阶级的地位,比较稳固。做人不论是进取还是放任,个人选择的意味都比较浓,体制的压迫感则比较弱。这才是魏晋名士产生的政治、经济基础。但《世说新语》里自然不会说这些。
《世说新语》里有一篇《任诞》,就是“任性”“荒诞”的“任”“诞”两个字。文章借王恭这个人之口,给“名士”下了个定义,原文是“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有个叫王恭的人说,名士不需要出奇的才能,只需要达到三个标准:一,通常没事干;二,酒喝得痛快;三,《离骚》读得熟,就可以叫名士了。
这三条哪条最重要?容易引人注意的是后两条,但其实最重要的,倒是第一条。
这在贵族或准贵族社会里,甚至可算是一个可以不用考虑文化差异的普世标准,有人概括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绅士的关键要求,也是“要‘无所事事’,并把开销维持在某一显著水平上。”第一条达到了,后两条可以通融甚至置换掉。什么样的人才能无所事事还衣食无忧还没人能说你的不是呢?前提当然是要有祖传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精神财富。
但是,后两条更引人瞩目,显然就是《世说新语》想达到的效果,它展示的是名士们最想被别人看到的一面。这么看来,说《世说新语》是名士教科书,又不如说它是名士的宣传片。
我这本书所做的事,很重要一点就是把云端里的名士,拉回到充满世俗气味的社会里来。
就比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名士那是怼天怼地怼一切,我们前面讲到的王徽之怼领导的例子就是这样。但当我们把名士拉回世俗社会,换个角度深入分析,看似王徽之怼领导怼得很爽,那是因为他是士族子弟,所以可以不干活,而他不干的活儿,最终多半要落到我们这样普通百姓身上,那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这些分析和还原,都可以说缺少文艺性的高雅,是很俗气的工作。
当我们把这些名士,从高高在上的权贵浮云中拉回到真实的历史环境、还原到具体的世俗生活中,其实已经找到了一条深入了解《世说新语》的思路了。具体说,可分为五个时间段。我的这本《世说俗谈》就是围绕这五段时间线展开的。如果你回头想尝试自己读《世说新语》,不妨也试试这个思路。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曹魏取代汉朝的那段历史里,涌现的名士。
因为《三国演义》的缘故,这段历史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知名度极高,不过《世说新语》和《三国演义》的关注点完全不同。《演义》力捧蜀汉人物,《世说》除了对诸葛亮比较尊敬外,对蜀汉几乎没眼看,全书只提到过一次刘备,还说他只配添乱。所以这部分出现的人物,除了曹操、曹丕父子,其他人物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很重要,但今天我们未必熟悉了。
有两个变化,值得你关注。
第一,东汉末,世家大族已经在政治上取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但寒门弟子,也还没有彻底失去希望,为了穿过已经快完全淤塞住的上升通道,他们卷到疯狂,费尽了心机。而一旦通过了这个通道,他们又会立刻转身,想把通道进一步堵死。所以,不要以为出身相近,就是自己人。
第二,原来国家重视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然是儒家思想。而曹魏代汉时期,兴起了一门学问,叫玄学,探讨一些很抽象神秘的问题。从哲学角度,可以把玄学讲得很高端,但庸俗地看,玄学就是在给世家大族子弟免去责任。怎样既享受荣华富贵,又不用接受道德、礼法的约束,玄学都可以给你提供很高大上的理由。
名士们的人生选择,往往就是围绕着这两个变化来的。
曹魏代汉的名士之外,我们还需要重新了解“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可能是名士当中最著名的偶像团体,他们蔑视礼法,追求精神自由,在竹林找那个饮酒纵歌,肆意酣畅,令人神往。
其实,这七个人多半活得没这么纯粹,但为人处世的智商、情商,可能远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高明。
拿嵇康来说,很多人印象里,嵇康就是颜值超高,才华绝顶,内心高洁,用激烈的态度批判虚伪的礼法。但是,你看嵇康留下的文字,他身上也有息事宁人谨小慎微的一面,他名气那么大,其实也利用了一些并不见得很体面的因素。还有,嵇康为什么被杀?很多人喜欢嵇康,所以愿意相信一个说法:嵇康影响太大了,尤其是司马昭决定要杀嵇康之后,几百个太学生为嵇康求情,这反而引发了司马昭的忌惮,所以就越发非杀嵇康不可了。
这个说法,既抬高了嵇康的影响力,满足了嵇康粉丝希望偶像影响力超级大的心理需求;又符合很多人对古代专权现象的认识:古代掌权者是绝对容不得可能威胁到自己的人的。所以很多人都信了。
其实,当时的权力格局是怎样的,史书的记述是很清楚的,嵇康怎么可能威胁到司马昭?司马昭杀他,更可能倒是因为他不重要,但是影响力确实大,关注度确实高。当时司马昭刚杀了曹魏的小皇帝曹髦,把嵇康杀了可以转移关注焦点,吓得更多人闭嘴。嵇康这种名声很大但是没有权力根基的人,是最危险的。
当然,我也不希望因为我写到这些,就引出“人设崩塌”了,“原来你是这样的竹林七贤”之类的感慨。我们从小都学过很多简单化的判断,这些判断对吗?大多数都是对的,只是太简单了而已。在你不必太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脑子里又需要有个大致的印象,那么有这么个简单化的判断就够了。但如果想静下心来,深入一点面对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即使是最简单的判断,后面也有复杂的人生百态,前因后果。能够接受复杂性,能够接受有缺陷的优秀人物仍然是优秀人物,能够看到一项伟大事业一路走来,也不可避免有许多肮脏的血迹,才不至于动不动就人设崩塌,梦想破灭。
“竹林七贤”之后,我们需要关注的第三个群体是西晋时候的人物。
从汉末到隋唐,是中国的大分裂时期。这四百年的大分裂当中,只有西晋实现过短暂统一。这在这个乱世里,就显得特别像是一场梦。西晋名士把这场梦,做得尤其浮华。这部分就写这一场大梦中的名士。
这个阶段,美男子特别多。特别有名的,比如潘岳,他字安仁,民间往往称他为潘安,这是古代美男子的代表了,关于他有多帅,最有名的例子是他夹着把弹弓,洛阳城里转一圈,他迷妹和妈妈粉,都向他扔水果,很快他拉着一车水果就回家了。卫玠,也是帅得不得了,但身体很羸弱,穿上衣服,就好像能把他压垮,所谓“弱不胜衣”。卫玠到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来,也是引起全城轰动,南京人民都去围观他,几次粉丝见面会之后,最后就把卫玠活活累死了,留下个典故,叫“看杀卫玠”。
美男子的故事听起来当然令人快乐,读《世说新语》的“容止”一门,很容易觉得眼前出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美男子,只知道这些人都很帅,可是他们彼此间有什么区别呢?很多人辨识度未必高。但细看他们的人生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是不一样。潘岳的颜值是非常高,可是他的出身门第,在士族圈子里却并不高,这成了他人生的天花板。为了突破天花板,他在当时最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卷得很深,并且因此送命。卫玠不同,他的家族,要显贵得多,当年曹魏灭掉蜀国的时候,他的爷爷做了一件非常卑鄙的事,卫玠小时候,他的爷爷又被人用同样卑鄙的手段害死,死里逃生的卫玠从此和各种政治斗争无关,他活成了一个没什么事迹但也因此特别干净的美男子,经过了西晋和东晋之间天崩地裂般的大毁灭之后,他又成了所有人回忆时都愿意美化的对象,所以他虽然其实根本不是死在南京的,看杀卫玠的故事根本不存在,但这个故事大家就是乐意一直讲下去。
将这些美男子故事还原到真实的历史场景中,我们看到的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的互相残杀和社会大崩溃。帅哥身后的背景板上,都是哗哗流淌的血。
西晋结束,伴随着一个著名的文化事件,“衣冠南渡”,也就是北方人向南方的大逃亡。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第四个要点。
这部分的核心人物,是王导。你熟悉的“旧时王谢堂前燕”这句诗,王谢是指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谢家的代表人物是谢安,王家的代表人物就是王导。今天南京的秦淮河畔,还有个“王导谢安纪念馆”。关于王导另一个特别有名的典故是,东晋第一个皇帝司马睿,有一次在盛大的典礼上,拉着王导,要王导和自己一起坐上皇帝的宝座。相应的,还产生了一个“王与马共天下”的段子。
《世说新语》一路看下来,我们看到很多大名士都做了很大的官,可是看起来好像都不干正事,就是一天到晚清谈玄学而已。结果呢?很多人自己结局悲惨,还落了个“清谈误国”的罪名;但王导却成就了极大功业。会有这样的区别,是运气有好有坏,还是相似的外表下,其实有完全不同的思维层次和办事逻辑?
这部分写王导如何做到和别的名士看起来相似,骨子里却完全不同。王导是个简直神奇的平衡大师。这样细腻的画面,也是我们将人物还原在世俗社会中才看得到的。
关于《世说新语》,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第五个群体,也是最后的群体,是东晋中期以桓温和谢安为中心的名士。
《世说新语》里的出场次数,谢安第一,桓温第二。
桓温是枭雄,但是一个和名士们相爱相杀,因此拌嘴时金句频出的枭雄。而谢安差不多就是文人心目中关于理想人格的一个梦。他是世家子弟,风神秀彻,婚姻美满,精通文学、音乐、书法、清谈等等一切才艺,他还雅量高致,天才俊逸,热爱隐居无意功名,却谈笑间建立了最伟大的功业,然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
当然,讨厌文人的人,今天也一样多。于是就会发现,关于谢安的争论,往往不是争的谢安如何,而是争的文人如何。谢安最著名的形象是淝水之战时还淡定和人下棋,但在现在的口水战中,他自己就成了一个棋盘。所以真实的谢安如何,往往很少有人关注。
这部分讲谢安如何与桓温相处,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怎样各自从对方身上,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写到桓温死的时候,突然想到一句话:“桓温与他看不起的名士们,骨子里还血脉牵连。所以,桓温仍是《世说》中人,而后来那个比桓温更有军事天才,更有英雄气概,做成了桓温想做而做不成的事业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里的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刘寄奴,却不是。”
这句话做全书结尾,不好么?于是原计划要写的最后几章,淝水之战到底怎么回事,东晋是怎么被终结的,这几个话题就全部不写了。学一次魏晋名士的洒脱,书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已经讲了太多了,这本《世说俗谈》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今天,我们分别从“世说”和“俗谈”入手,分别了解了,《世说新语》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读懂《世说新语》。
最后,我还想跟你谈谈,有关《世说俗谈》创作的一些感受。
2022年,我受邀在「得到App」开设了一门国学课,我讲的第一部作品,就选了《世说新语》。这本书虽然刚刚出版,但写作时间远在开国学课之前。这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科普文章。科普文章材料搜集完,思路捋清楚,就可以开始写了,不需要灵感的。写书要麻烦得多,我要寻找一种精神内耗的状态。对某个人某件事,我理性上很赞同,但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或者这件事我知道不对,但我就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这种自我撕裂的感觉到位,就可以动笔了。也就是说,这本书绝不是理性、客观、中立的,但是它会同时给你提供几种各不相同的不理性不客观不中立。
曾经和马伯庸老师聊到过一个话题,他说一次编电视剧,开始设计了一个场景,人物对话,通过对话中传递出信息,交代清楚时代背景,已经设计得很完美了,觉得不行,要改,直接上字幕,哪个朝代哪个皇帝在位第几年,用这种方式把时代背景直接告诉观众。因为现代的电视观众,恐怕已经没有耐心和专注力,慢慢去琢磨细节中传递出来的一些微妙的东西了。但到我写《世说俗谈》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知道,相比很多行业,出版行业是比较穷的,赔钱也赔不了多少。所以它反而纵容了我的一些臭毛病,比如不喜欢陈列硬知识,让读者惊呼,哇,干货满满,而是习惯写到某个话题顺便带出来,对有些事情的看法,也点到为止,不喜欢说得太透。总之,就是保留一些重点不突出,层次不分明,措辞不高端的聊天感。
国学课讲述方式,基本是相反的。课和书是不一样的,课的结构和观点都比较清楚,有时我忘了下判断,编辑老师也会提醒我,刘老师,这里补两句。于是我就补,现在补习惯了也觉得挺开心的。还是那句话,课就是传播知识,写书更多是满足自己,和寻找朋友。今天算是该说的都说了,愿意听课还是看书,或者都不愿意,任你选择。当然,如果觉得二者有不同的趣味,都挺愿意,那我就太感谢了。
好,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划重点
1.《世说新语》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关注,它是古代文人的“名士教科书”;它是窥探魏晋风貌的一扇窗户;它是现代人对抗内卷焦虑的精神良药。
- 关掉“美颜”看历史,我们可能看到血淋淋的现实,但也许有时候,正是在残酷的历史背景下,才显得人格之美尤其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