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之舞》 苗炜工作室解读
《娜塔莎之舞》| 苗炜工作室解读
关于作者
奥兰多•费吉斯是伦敦大学教授,他写的《耳语者》《人民的悲剧》《克里米亚战争》都是关于俄罗斯和苏联的故事,他想把历史书写得像故事一样引人入胜,这是他最大的特点。
关于本书
这本俄罗斯文化史并不是一部通史,他从18世纪讲到20世纪。为什么要从18世纪初讲起?因为正是彼得大帝推行的欧化改革撕裂了俄罗斯社会。费吉斯在书中以专题的形式,探讨了与俄罗斯文化认同有关的8个线索,他想让读者欣赏俄罗斯文化形态中的多样性,窥见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
核心内容
为什么说1812年卫国战争是了解俄罗斯文化的入口?俄罗斯知识分子是怎样走向农民的?俄罗斯文化的多样性是如何造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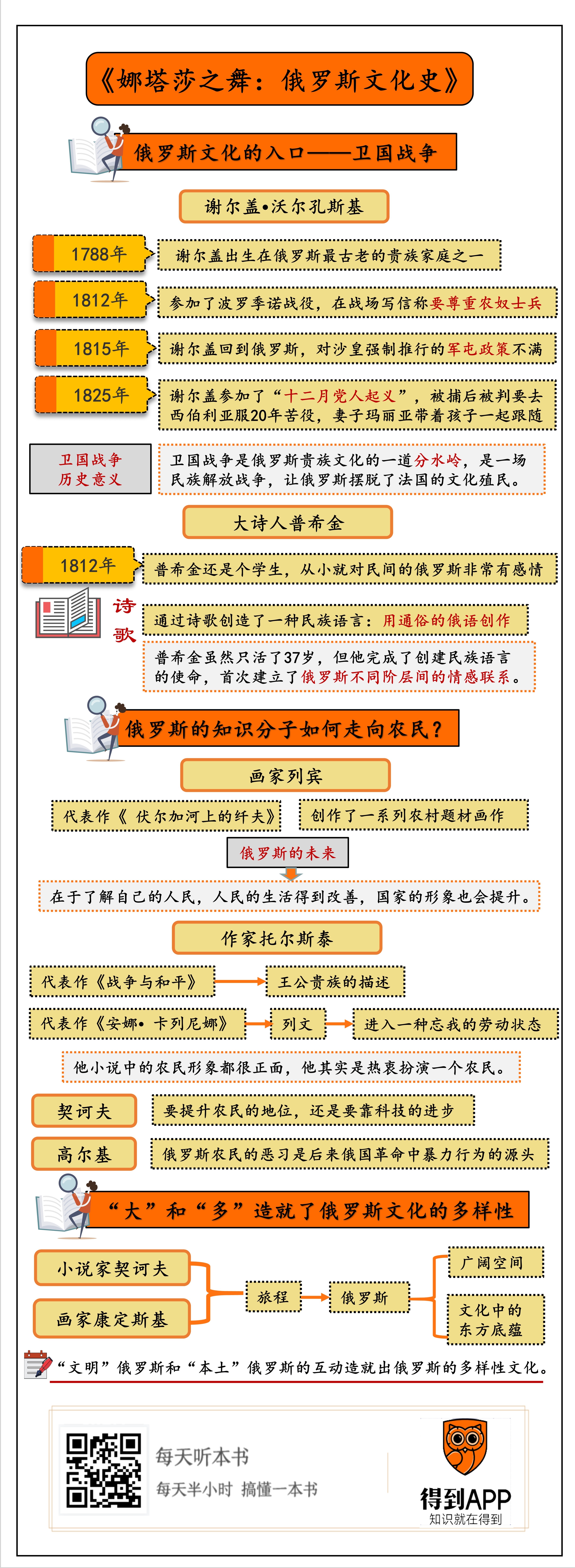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我们对俄罗斯文化,多少有些了解,大作家托尔斯泰,大诗人普希金,大画家列宾、康定斯基,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等等,每个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每位都有丰富的经历。怎么把这些人放到一本书里来描述?
先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娜塔莎是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人公,是位贵族小姐。小说里有一段情节,娜塔莎跟着一个远房亲戚“大叔”,在乡下打猎,打猎完毕,大叔邀请她到小木屋做客,吃饱喝足后,大叔开始弹琴唱歌,让娜塔莎跳舞。
娜塔莎一直跳芭蕾,是社交舞会上矜持的女宾。在乡下小屋里,她跟着俄罗斯民歌的节奏翩翩起舞,从姿态上、精神面貌上都展现出了俄罗斯民间舞蹈的精髓。女管家看到这位贵族小姐能有一颗俄罗斯的心灵,非常欣慰。这段情节就被本书的作者奥兰多•费吉斯拿来做标题。
娜塔莎接受欧洲古典贵族教育长大,在乡下小屋跳起了俄罗斯民间舞蹈,发觉“自己身上流着农民的血液”,一下子揭开了俄罗斯“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创伤。18世纪初,彼得大帝推行的欧化改革,撕裂了俄罗斯社会,分化出了价值观和理想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文明”俄罗斯和“本土”俄罗斯。
“文明”俄罗斯是欧化的模式,上层阶级崇拜西方文明,语言和生活习惯都改变了。而“本土”的俄罗斯是民族化的模式,大量农奴和农民还过着原来的生活,通用语言是俄语。这两个世界的复杂互动,造就了独特的俄罗斯文化。
“娜塔莎之舞”,是今天这本俄罗斯文化史的主题,它展现了“文明”俄罗斯和“本土”俄罗斯之间的对抗,上层阶级和底层农民之间的分裂,也代表了独特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被欧化的俄罗斯人表面上按照欧洲习惯生活,内心又会被俄罗斯的风俗和情感影响。开头提到的那些艺术家,他们既面对西方的文明世界,也面对俄罗斯的荒蛮大地,他们如何调节内心矛盾,选择怎样的创作道路,就是这本《娜塔莎之舞》的主要故事。
本书的作者费吉斯是伦敦大学教授,他写的《耳语者》《人民的悲剧》《克里米亚战争》都是关于俄罗斯和苏联的故事,都非常好看。这里说的“好看”,是费吉斯的一个追求,他想把历史书写得像故事一样引人入胜,这是他最大的特点。不过,在史学界同行看来,这也是他最大的缺点,同行指责说,费吉斯的作品文学性太强,让人无法判断内容究竟是史实还是虚构的,作品中还有事实错误。
费吉斯的这本俄罗斯文化史并不是一部通史,他从18世纪讲到20世纪。为什么要从18世纪初讲起?因为正是彼得大帝推行的欧化改革撕裂了俄罗斯社会。费吉斯在书中以专题的形式,探讨了与俄罗斯文化认同有关的8个线索,他想让读者欣赏俄罗斯文化形态中的多样性,窥见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
今天的解读,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讲1812年卫国战争,这是了解俄罗斯文化的入口。第二部分我们讲俄罗斯知识分子是怎样走向农民的?第三部分讲广阔空间,俄罗斯面积巨大,民族多,这个“大”和“多”,造就了俄罗斯文化的多样性。
第一部分,来了解下1812年的卫国战争。分裂的俄罗斯上层阶级和广大农民,联手推动了民族的形成。我们首先来认识两个人,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和普希金。
谢尔盖出生于1788年,他们家是俄罗斯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谢尔盖在军事预备学校学习,然后加入近卫军。19岁时,他在一次战役中被子弹射中肋部,后来,他转入圣彼得堡的皇家卫队。谢尔盖深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赏识,经常和沙皇一起吃饭,还时不时能见到尼古拉王子,算是尼古拉王子的玩伴。
1808年,谢尔盖回到前线,接下来的4年,参加了50次战役,24岁就升为少将。1812年,谢尔盖参加了波罗季诺战役,这是拿破仑侵入俄国时期的一次会战,俄军损失惨重。8月26日,谢尔盖在横尸遍野的战场上给他的兄弟写信,信中说,“俄罗斯应该尊重他的农奴士兵,他们可能只是农奴,但是这些人在战场上拼命,就像公民为祖国而战。”
像谢尔盖这样的贵族,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农奴等同于人形牲畜,他们不会把所有农奴都看成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个体。如果不打仗,贵族们用法语聊天,跳跳舞看看戏,可一旦打起仗来,贵族军官就和农民士兵同仇敌忾,他们很自然地有了平等的思想。谢尔盖写过一则笔记,提出国有银行要给农民贷款,给农民开公立学校,来改善穷困人民的命运。
1812年的卫国战争,是俄罗斯贵族文化的一道分水岭。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让俄罗斯摆脱了法国的文化殖民。谢尔盖带着一支部队追击拿破仑直至巴黎,然后去参加维也纳和会,再回到巴黎,加入一个政治家的小圈子。谢尔盖又去了伦敦,看看上议院下议院和君主立宪制是怎么回事。他还打算去美国看看什么叫民主。一批像谢尔盖这样的军官回到俄罗斯,就会发现,俄罗斯还是老样子,还是君主专制,还是有农奴制。
谢尔盖在1815年回到俄罗斯,他有了点民主思想,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就有点不满。像他这样参加过卫国战争的青年贵族军官,本来都对沙皇有很大的期待。亚历山大一世曾经许诺要进行政治改革,要设立参议院,这是司法与行政的最高机构,要设立上院,这是立法机构,还要有最高法院,沙皇还放宽了审查制度,贵族军官们本以为沙皇会沿着改革之路走下去,他们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现代的欧洲式的国家,希望每一个俄罗斯农民都有宪法保障的权利。不料沙皇说一套做一套,强制推行军屯政策,凡是农奴出身的士兵,就要强制为国家种地或者进行其他义务劳动,不服从者,杀。
这批青年贵族军官愤怒了,有的向沙皇提交请愿书,要求废除农奴制,有的就想着等待,下一个沙皇应该继续改革。还有急性子的,就想,干脆把这个沙皇杀了。俄国的贵族虽然有大量的土地,大批的农奴,但说到底,他们也是沙皇的奴仆,只不过是等级比较高的奴仆。
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尼古拉一世继任,这一年的12月14日,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大约三千名士兵聚集在圣彼得堡的元老院广场,拒绝向新沙皇宣誓效忠,这次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500名十二月党人被捕,其中就有谢尔盖。十二月党人当中5人被判绞刑,121人被剥夺贵族头衔,送往西伯利亚服苦役。谢尔盖和尼古拉一世是少年时的玩伴,他没被判死刑,但要去西伯利亚服20年苦役。
整个家族都和谢尔盖断绝了关系,但他的妻子玛丽亚带着孩子,跟着他踏上了流放之路。像玛丽亚这样的妻子有一大批。押解犯人的车队在前面走,陪丈夫一起流放的妻子就在后面跟着,她们这样做可能出于爱情,也可能是出于牺牲精神。去西伯利亚之前,玛丽亚在莫斯科参加了一个告别沙龙。沙龙上,普希金朗诵了一首诗叫《寄西伯利亚》,诗中有这样几句,你的艰苦辛劳并不是白费,你的凌云壮志也不是徒劳,希望就在附近。
玛丽亚跟着丈夫来到西伯利亚,找来一本《圣经》开始学俄语。在这里,受法国教育长大的贵族都掌握了俄语,也都学会了种地。谢尔盖后来被称为“农民公爵”,在他眼里,西伯利亚是一片充满了民主希望的土地,朝气蓬勃,天真烂漫,原始又粗犷,农民显得特别诚实又正直,跟农民在一起,就意味着和贵族子弟所生长的罪恶世界断绝关系。谢尔盖的这种精神追求,后来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一再重现。
我们来看第二个人,大诗人普希金。
1812年卫国战争打赢了,就有一种呼吁说,战争的历史应该用一种简洁明了、各阶层的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来撰写。当时的俄罗斯上流社会说法语,和法国开战之后,贵族都有点忌讳法语,教育孩子时也会适当加一些俄语。当时俄罗斯的书面语由斯拉夫语和拉丁语混杂而成,没有固定的语法和拼写方法,俄罗斯农民说的口语和书面语差别很大。一场民族解放的战争打完,民族语言的创建就变成了一个要紧事,文学语言不成熟,也就谈不上什么文化。
在19世纪初,俄罗斯诗人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创造一种以社会中人们所说的语言为基础的文字。当时,一些基础的文学概念在俄罗斯的口语中还没有形成,比如“同情”“隐私”“冲动”和“想象力”,这几个词只能用法语说,俄语中没有这些词。还有长裤、背心、礼服,这些生活物品也是从西方传来的,也没有俄语词。所以,俄罗斯作家们不得不改写法语或者借用法语。
1812年时,普希金还是个学生,他很向往西方,8岁时写的第一首诗就是用法语写的,但他对民间的俄罗斯也非常有感情。他被农奴出身的保姆带大,从小就听保姆给他讲故事唱歌。
普希金写作时,会收集民间故事和民间词汇,用到自己的诗歌里。通过诗歌,普希金创造了一种民族语言,他用通俗的俄语创作,识字的农民能看懂,尊贵的公爵也能看懂。虽然普希金只活了37岁,但他完成了创建民族语言的使命,首次建立了俄罗斯不同阶层间的情感联系。有一本《俄国文学史》这样开头:外国人很难信服普希金在俄国作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他不懂俄语,那么他根本就不能理解。然而,即便他持有不同意见,仍有必要接受这一信念,那就是普希金至高无上,否则他对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文明的一切观念都是不可靠的。
其实,每种语言的使用习惯,都是由使用该语言的重要文学家奠定的。比如,我们现在用白话文,白话文的初始状态就与新文化运动先驱的新诗和小说紧密相连。同样的道理,歌德打造了德语的基因,普希金打造了俄语的基因。俄罗斯经过1812年一战,意识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再经几代人努力,俄罗斯文学蔚然大观。
为什么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如此厉害?有评论家认为,当时的俄罗斯有农奴制,有报刊审查制度,直接评论社会现实的著作不太可能出版,作家不得不通过文学、诗歌等形式,表现人们对沙俄社会不公正的批判和对未来的畅想。所以,沙俄时代的俄罗斯文学才有特殊地位,才会成为社会讲坛,替代了哲学、政论、宗教思想甚至是社会科学的功能。可以说,当时的俄罗斯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各种文化文本。
好,这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1812年卫国战争,俄罗斯打败了拿破仑,但一批年轻的贵族军官接受了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他们希望俄罗斯变成一个欧式的现代国家。卫国战争的胜利,让俄罗斯摆脱了法国的文化殖民,开始自己的文化建设。
第二部分,来了解下俄罗斯知识分子是怎么走向农民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这么做?1860年代,俄罗斯的普遍看法是要像欧洲一样,选择自由化改革的路线,但是要带着农民一起。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关注农民问题,知识分子们想要向农民靠拢,教育他们成为公民,把他们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和自己一样。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俄罗斯在世界的崛起,仰仗于农民能否提升到公民。
这部分,我们也来认识两个人,画家列宾和作家托尔斯泰,他们都为了走向农民做出了很多努力。
1861年,沙皇宣布废除农奴制。之后的艺术界有了一种风潮,说俄国画家不要再模仿欧洲艺术了,应该描绘乡村和城市的景象,画人民自己的悲伤与快乐,艺术应该来自人民。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叫斯塔索夫,是一位艺术与音乐评论家,他是列宾的精神导师。列宾的名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就是在斯塔索夫的鼓励下创作出来的。
列宾出生在贫穷农村家庭,进入皇家艺术学院之前专门画圣像。1870年夏天,列宾带着艺术学院的介绍信,到农村去画画。那时的农民并不愿意当模特,他们觉得被画家画在纸上,灵魂就被魔鬼带走了,但他们看到列宾介绍信上艺术学院的皇家徽章,就会说,是沙皇派他来我们这儿的。
列宾花了点钱才找到一群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给他当模特。纤夫的身体被纤绳束缚,脸上饱经风霜,列宾在这些模特脸上看到俄罗斯人民的性格。《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画的是烈日之下,十一个纤夫拖着货船,步履沉重地前进,每个人身材、表情各不相同。这幅画最后献给了沙皇的次子,王子殿下还请了一群纤夫到自己家一起吃饭。这就是当时的社会风气,王子和艺术家,都知道俄罗斯的未来就在于了解自己的人民,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国家的形象也会提升。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之后,列宾创作了一系列农村题材画作。不过,他与导师斯塔索夫的关系陷入紧张,后者主张艺术中要有现实主义、人民性和民族性,而列宾想要追求纯净的艺术。列宾后来去了巴黎,被印象派吸引,画作也转向了法式肖像画和漂亮的街景。可以说,他背弃了自己青年时期的道路,斯塔索夫谴责他放弃了对祖国和同胞的艺术责任。可列宾并不后悔,他说,“我已经忘记怎么通过艺术作品来表达和传递价值判断,这一功用过去几乎将我吞噬,失去它我毫不惋惜”。
这是画家列宾在艺术观念上的纠结。1870年代,俄罗斯有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像列宾一样,去到农村,“走到人民中去”。他们宣称要和农民一起生活,建设一个“新俄国”,让民族精神重生,这样贵族和农民将会团结一致,这就是俄罗斯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他们真的相信,改变农民,提升农民的地位,就能改变国家的面貌。他们坚信农民是民主事业的奋斗盟友,他们对农民的每一种看法都会赋予农民某种美德。一些俄罗斯知识分子认为,西方人为了追求物质,已经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淳朴的俄罗斯农民有更纯洁的信仰,保留着俄罗斯灵魂。但在西方的视角来看,在工业化进程中落后于西方的国家,才会产生民族之魂这样的概念,相信自己经济上虽有缺失,但原生态的乡村中有美德。
贵族出身的作家托尔斯泰和那些学生一样,也想“走到人民中去”,他享受和农民在一起,甚至想把自己真正变成一个农民。
《娜塔莎之舞》中记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列宾给托尔斯泰画过肖像,去过托尔斯泰的庄园。列宾说,托尔斯泰只是花一天的时间到农民那里了解一下疾苦,然后就宣布“我和你们在一起”。列宾从小就在辛勤劳作,知道农民生活是多么贫困和艰难,他不相信庄园主托尔斯泰能够真的像农民一样生活。
托尔斯泰年轻时吃喝嫖赌,赌博输掉过自己的祖产,但他的确有道德追求,他想做一个优秀的农场主,在农村寻找幸福,他办过十几所农民子弟学校,把一大部分土地都无偿分给农民。农奴制废除之后,托尔斯泰解雇了所有佣人,自己做农活。可他不会喂猪,就故意把猪都饿死,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到书房。承认自己天生就是做老爷的命,这会让托尔斯泰在道德上有压力。所以他会对农民子弟说,我要放弃贵族生活,盖一个茅草屋,锄草犁地。但是,转过头来,他又会说农民都是无可救药的人,没法被教育,也让人无法理解。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对王公贵族的描述,到《安娜•卡列尼娜》里,他又写了一个叫作列文的贵族,这个角色是根据托尔斯泰本人的梦想塑造出来的,列文能在农田的劳作中感受到活力,进入一种忘我的劳动状态。但托尔斯泰自己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农民,他把农民理想化,他的小说中的农民形象都很正面,他其实是热衷扮演一个农民。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农民,大部分是善良、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人。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后来发现,农民并不是自己头脑中想象的那样代表着“俄罗斯的灵魂”,他们身上并没有成为社会道德模范的特质,他们酗酒、打老婆。这些恶习真的能改变吗?农民的素质和地位真的能提升吗?对于这个问题,两位比托尔斯泰更了解农民生活的作家,给出了自己的反思:契诃夫当过医生,见识过底层农民的悲惨生活,他认为,要提升农民的地位,还是要靠科技的进步。高尔基是个孤儿,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对农民不抱任何幻想,他认为,不管俄罗斯农民本身有多善良,只要他们聚集在一起,所有善良品质都会消失殆尽,俄罗斯农民的恶习是后来俄国革命中那些暴力行为的源头。
好,这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俄罗斯知识分子认为,取消农奴制,让农民都成为有教养的公民,俄罗斯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他们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但这些努力往往会让他们意识到艺术家与农民之间那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托尔斯泰在“娜塔莎之舞”这个场景中,寄托了一个信念:俄罗斯农民和参加卫国战争的贵族军官,通过一种纯正、传统的俄罗斯民间舞蹈,形成一个广泛共同体。但作者指出,俄罗斯民间舞蹈中的很多因素都是舶来品,并不存在所谓的俄罗斯传统,这一点象征了,纯粹的俄罗斯民族文化是不存在的。“文明”俄罗斯和“本土”俄罗斯的互动造就出的俄罗斯文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文化,而是富有多样性的文化。
第三部分,我们通过小说家契诃夫和画家康定斯基各自的旅程,来看看俄罗斯的广阔空间和俄罗斯文化中的东方底蕴。
1887年,契诃夫发表了一篇小说叫《草原》,写四个人搭乘一辆马车在草原上穿行,四周是一种停滞和荒凉的感觉,风景单调乏味。按理说,广阔天地会给人一种身心自由的感觉,但契诃夫这个小说写的却是压抑,无边的土地让人觉得无处可逃,无边的土地就是一个大监狱。
有好几位俄国作家都写过单调的草原给人带来的影响,太宽广的空间会让人感到空虚,走出村庄,看到空空如也的四周,就会感到空虚渗入灵魂。一望无垠的田地有催眠效果,长时间的注视辽阔大地,会让你大脑一片空白。广阔空间让人心存恐惧,在冰天雪地之外,在森林线之外,冰风暴呼之欲出,能把人冻死。
俄罗斯领土辽阔,从西走到东,在当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890年4月,契诃夫想要在自己死前完成一些严肃的成就,写出能够超越自己过往作品的伟大著作,他要去萨哈林岛,研究苦役犯和移民的生存状态,萨哈林岛在日本的正北方向。契诃夫从莫斯科出发,途中,他会顺便游览,也会被疾病耽搁,用了八十天才到达目的地。契诃夫在萨哈林岛待了三个月,几乎走遍了岛上有人烟的地方,岛上的人要么是苦役犯,要么是强制移民,他专门制作了一种卡片表格,每家每户都进行调查。
契诃夫写了一本书叫《萨哈林旅行记》,这是一部控诉沙皇政府刑罚体系的作品,也是一部游记,他在书里描述了西伯利亚的风光,记述了萨哈林岛上的生活状况。他也写下了那里的异域之感,当他顺着阿穆尔河经过一个个小村庄时,他说,这里不再是俄国,而是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地区或者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某个地方,俄国人的生活方式对阿穆尔流域的居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里的人们不理解普希金和果戈理。他说,萨哈林岛上的犯人也有异域感,他们总想着回到故乡。
俄罗斯地域辽阔,很多地方都是扩张侵略而来,托尔斯泰曾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中亚地区当过兵,俄罗斯的文人,对沙皇的侵略政策基本上都是认同的。19世纪,随着俄罗斯版图扩张到亚洲草原,俄罗斯人开始把亚洲文化看作俄罗斯文化的一部分。西方人排斥俄罗斯,俄罗斯人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对西方价值观表达带有怨恨的蔑视,强调自己野蛮的一面。西方人歧视俄罗斯人,可俄罗斯人觉得自己在中亚和远东地区有优越感。
俄罗斯知识分子也对民间文化中的亚洲渊源产生兴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画家康定斯基的一次探索旅程。
康定斯基在投身艺术之前,本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人类学家。他在莫斯科大学念的是法律,毕业前一年,他跑到离莫斯科800公里远的科米地区考察学习。科米地区是基督教和萨满教的交汇之处,萨满教是古代蒙古人的信仰。历史上,科米地区的人们一直信奉萨满教,14世纪,这里变成了俄罗斯殖民者的定居点,当地人被迫改信基督教。
康定斯基到了科米地区,仿佛穿越了时间隧道,他发现,当地人虽然表面上不否认自己是东正教徒,私底下却信奉蒙古部落的萨满教。他还发现了,科米人与亚洲文化的渊源。科米人的祖先是芬兰的乌戈尔部落,几百年来,这个部落不断和来自北亚、中亚的突厥人融合。科米地区有大量蒙古纹饰的出土文物,也有蒙古风格的教堂。康定斯基在这个地区看到了很多民间绘画,对它们夸张、非写实的表现手法很感兴趣,他说,科米改变了他看待艺术的方式。
康定斯基的这次探索也是一次寻根之旅,他的家族来自蒙古阿穆尔河附近的一个部落。18世纪,这个部落的人向西北迁移,开始和芬兰人、科米人做生意,开始和科米人通婚。康定斯基有没有科米人的血统,这不好确定,但他长的就是蒙古人的外貌。很多俄罗斯家庭都有蒙古血统,这个族群中的文化名人除了康定斯基,还有屠格涅夫、阿赫玛托娃等等。
离开科米地区后,康定斯基做了一场讲座,讲述他的旅途见闻,掀起了一股风潮,学者们开始研究俄罗斯民间文化中的亚洲渊源。考古学家发现,石器时代鞑靼文化就对俄罗斯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俄罗斯民间信仰中都有亚洲渊源,等等。包括康定斯基在内的很多艺术家,都把亚洲当作俄罗斯文化身份的一部分,就像画家舍甫琴科所说:“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无法区分我们的民族特色在哪里终了,东方的影响从哪里开始……是的,我们是亚洲人,我们以此为荣。”
《娜塔莎之舞》的精华内容已经为你解读完了。
我们知道,1812年的卫国战争,让俄罗斯摆脱了法国的文化殖民。普希金奠定了俄语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基础,谢尔盖这样的贵族军官,接受了西方平等自由的理念,希望把俄罗斯建成一个欧式的现代化国家。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俄罗斯的知识精英都由此认识到自己的文化使命。
俄罗斯知识分子相信,农民中有纯洁的灵魂,如果农民地位提升,俄罗斯就可以变成一个先进的国家,他们开始走向农民。像列宾这样的艺术家会走向农民,描绘“俄罗斯人民的性格”,像托尔斯泰这样的贵族,会把土地无偿给农民,会给农民子弟办学校,但他们难以跨越艺术家、贵族与农民之间那条鸿沟。后世的革命者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俄罗斯有辽阔的国土,有多种民族混居,蒙古人、突厥人、鞑靼人都在俄罗斯留下了文化痕迹。俄罗斯是一个东西方之间的国家,面对西方的排斥和蔑视,他们会强调自己野蛮的一面,面对亚洲的扩张,则更野蛮。
这本书以贵族与农民的互动为主题讲述了俄罗斯文化史,如果你对俄罗斯的文学和音乐感兴趣,可以在得到电子书中找到电子版。
撰稿:苗炜工作室 转述:杰克糖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划重点
1.彼得大帝推行的欧化改革,把俄罗斯社会分化成“文明”俄罗斯和“本土”俄罗斯,这两个世界的复杂互动,造就了独特的俄罗斯文化。
2.1812年的卫国战争,让俄罗斯摆脱了法国的文化殖民,俄罗斯的知识精英都由此认识到自己的文化使命。
3.俄罗斯知识分子为了走向人民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他们很难跨越艺术家、贵族与农民之间那条鸿沟。